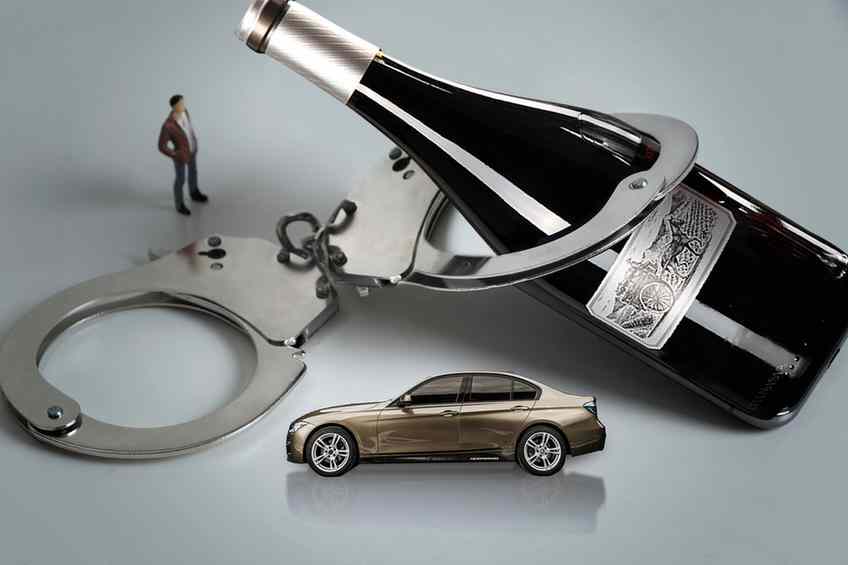合同欺詐行為與保同詐騙罪的區(qū)分和界定
 陳明月律師2021.12.24706人閱讀
陳明月律師2021.12.24706人閱讀
導(dǎo)讀:
而合同詐騙行為的含義,根據(jù)我國(guó)《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guò)程中,騙取對(duì)方當(dāng)事人財(cái)物的行為。但是,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欺詐行為畢竟是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行為。因?yàn)楹贤p騙罪作為一種目的型犯罪,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cái)物的目的。可見(jiàn),合同欺詐行為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構(gòu)成也可以由間接故意構(gòu)成;而合同詐騙罪則只能由直接故意構(gòu)成。那么合同欺詐行為與保同詐騙罪的區(qū)分和界定。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guān)知識(shí),希望能幫助大家。
而合同詐騙行為的含義,根據(jù)我國(guó)《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guò)程中,騙取對(duì)方當(dāng)事人財(cái)物的行為。但是,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欺詐行為畢竟是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行為。因?yàn)楹贤p騙罪作為一種目的型犯罪,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cái)物的目的。可見(jiàn),合同欺詐行為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構(gòu)成也可以由間接故意構(gòu)成;而合同詐騙罪則只能由直接故意構(gòu)成。關(guān)于合同欺詐行為與保同詐騙罪的區(qū)分和界定的法律問(wèn)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shí),希望能幫助大家。
一、合同欺詐與合同詐騙罪在理論上的界限
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法通則)若干問(wèn)題的意見(jiàn)》第六十八條對(duì)欺詐行為的解釋?zhuān)?ldquo;合同欺詐”是指簽訂合同的一方當(dāng)事人故意告知對(duì)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shí)情況,意圖誘使對(duì)方當(dāng)事人在做出錯(cuò)誤意思表示的情況下簽訂并履行合同的行為。而合同詐騙行為的含義,根據(jù)我國(guó)《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guò)程中,騙取對(duì)方當(dāng)事人財(cái)物的行為。很顯然,從法條字面的表述上來(lái)看,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欺詐行為在構(gòu)成特征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如二者都是利用合同的形式;都發(fā)生在合同的簽訂或履行過(guò)程中;主觀心態(tài)上都存在故意等等。但是,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欺詐行為畢竟是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行為。
(一)主觀方面不同:
雖然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欺詐行為在主觀方面均為故意,但是兩者的“故意”又不完全相同:
合同欺詐行為的主觀方面,既可以表現(xiàn)為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現(xiàn)為間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欺詐行為會(huì)導(dǎo)致相對(duì)人陷于錯(cuò)誤意思表示,卻希望這種結(jié)果發(fā)生;間接故意主要表現(xiàn)為行為人對(duì)某一重要事實(shí)輕率地做出陳述或根本不作表示,以致相對(duì)人錯(cuò)誤理解有關(guān)事實(shí),并據(jù)此做出意思表示。此種欺詐的特征在于,行為人并不考慮其陳述或態(tài)度可能給相對(duì)人造成的影響,行為人對(duì)其行為在主觀上采取了一種放任自流或無(wú)所謂的態(tài)度。
而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則只能表現(xiàn)為直接故意。因?yàn)楹贤p騙罪作為一種目的型犯罪,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cái)物的目的。為實(shí)現(xiàn)此目的,行為人對(duì)損害他人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這一犯罪結(jié)果必然持積極追求的態(tài)度,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必然導(dǎo)致對(duì)方當(dāng)事人財(cái)物上的損失,而仍然希望這一結(jié)果的發(fā)生,其心理態(tài)度始終是一種直接故意,而不可能對(duì)欺騙的結(jié)果持放任的態(tài)度。可見(jiàn),合同欺詐行為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構(gòu)成也可以由間接故意構(gòu)成;而合同詐騙罪則只能由直接故意構(gòu)成。
(二)客觀方面不同:
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的目的在于無(wú)償取得他人財(cái)物,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誠(chéng)意,因此其采取欺騙手段簽訂的合同通常根本無(wú)法履行,或者即使能夠履行,行為人也不會(huì)去履行;而在合同欺詐行為中,行為人并無(wú)不履行合同的故意,而只是用虛構(gòu)的事實(shí)或不履行告知義務(wù)致使合同違反公平交易規(guī)則,為自己謀取高于合同義務(wù)的利益。
從欺詐行為的方式上看,合同詐騙罪由于在主觀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所以行為人的欺騙行為只能是積極的作為方式,不存在不作為方式;而合同欺詐行為由于具有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形態(tài),所以行為人的欺騙行為可以是積極的作為,也可以是消極的不作為,甚至是沉默的方式。在間接故意的情形下,行為人的行為方式多表現(xiàn)為不作為,如不履行告知義務(wù)即可構(gòu)成合同欺詐行為。
從欺詐行為結(jié)果上看,合同詐騙犯罪“非法占有”的財(cái)物必須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guī)定的“數(shù)額較大”的條件;而合同欺詐行為并不以受害人有財(cái)產(chǎn)損失為必要條件,即使在要求有行為結(jié)果的間接故意的情形下,也沒(méi)有“數(shù)額較大”的構(gòu)成要件,行為人不法獲利數(shù)額的大小,不影響合同欺詐行為的成立。
(三)侵犯的權(quán)利屬性不同:
合同詐騙罪所侵犯的權(quán)利是受害人對(duì)財(cái)物的所有權(quán),而合同欺詐行為所侵犯的是對(duì)方當(dāng)事人的為真實(shí)意思表示的請(qǐng)求權(quán),侵犯的是一種債權(quán)。

(四)合同的真實(shí)性不同:
合同詐騙中的合同是不真實(shí)的、虛假的,行為人只是借助合同的形式來(lái)實(shí)施犯罪;而合同欺詐中所簽訂的合同是真實(shí)的,行為人追求非法利益的目的只能通過(guò)合同的履行來(lái)實(shí)現(xiàn),欺詐行為中必然有合同行為的存在。
(五)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欺詐行為最本質(zhì)的區(qū)別:
如前所述,單從法律規(guī)定的文字表述來(lái)看,合同詐騙罪與合同欺詐行為之間沒(méi)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但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構(gòu)成要件被立法明確限定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這才是問(wèn)題的關(guān)鍵。那么合同欺詐行為的主觀方面是否有這種目的內(nèi)容的要求呢?這個(gè)問(wèn)題的提出,主要是因?yàn)橛幸环N觀點(diǎn)認(rèn)為,合同欺詐與合同詐騙的根本區(qū)別僅在于情節(jié)輕重程度的不同,即行為人騙取對(duì)方當(dāng)事人的財(cái)物達(dá)到數(shù)額較大,就構(gòu)成合同詐騙犯罪,進(jìn)入刑法調(diào)整的領(lǐng)域,否則僅是一般合同欺詐行為,由民法規(guī)范調(diào)整,除此之外,二者并無(wú)其它本質(zhì)區(qū)別。這種觀點(diǎn)實(shí)質(zhì)上就是認(rèn)為合同欺詐行為也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內(nèi)容,或者說(shuō)即使沒(méi)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只要欺詐的財(cái)物數(shù)額較大,也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這是違背立法精神和法律規(guī)定的,也混淆了一般詐騙行為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會(huì)導(dǎo)致罪與非罪的認(rèn)定錯(cuò)誤。筆者認(rèn)為,欺詐行為與詐騙行為的主觀故意內(nèi)容雖然相似,但在目的內(nèi)容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行為人實(shí)施合同欺詐行為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使合同得以簽訂,并以合同的履行為其終極目的,欺詐方可以借此獲取不正當(dāng)?shù)睦妫布疵袷律系牟划?dāng)?shù)美6贤p騙行為則只是將合同的簽訂與履行作為其達(dá)到非法占有對(duì)方財(cái)物目的的手段,至于是否“數(shù)額較大”,只是區(qū)分一般合同詐騙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之間的罪與非罪的標(biāo)準(zhǔn)。因此,合同欺詐與合同詐騙的根本區(qū)別只能是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司法實(shí)踐中如何區(qū)分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
1、是否具備真實(shí)的合同主體資格。真實(shí)的合同主體資格,是簽訂和履行合同的前提條件。按照《合同法》關(guān)于合同主體的規(guī)定,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都是簽訂和履行合同的合格主體。但這些主體都必須是實(shí)際存在、并依其真實(shí)意思簽訂和履行合同,如果“以虛構(gòu)的單位或者假冒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不僅不具有簽訂合同的合法主體資格,且在造成合同對(duì)方當(dāng)事人損失時(shí),將使對(duì)方當(dāng)事人不可能依據(jù)其虛構(gòu)的單位或假冒的名義得到補(bǔ)償,無(wú)法實(shí)現(xiàn)其要求賠償?shù)臋?quán)利。在實(shí)踐中表現(xiàn)為:偽造合同主體身份證明文件,如營(yíng)業(yè)執(zhí)照、公章、合同專(zhuān)用章、業(yè)務(wù)介紹信等;盜用單位公章或加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shū)簽訂合同;被解除委托的行為人利用保留的公章、空白合同書(shū)等簽訂合同;借用其他單位的業(yè)務(wù)介紹信、合同專(zhuān)用章或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shū),以出借單位的名義簽訂合同。
2、有無(wú)真實(shí)有效的擔(dān)保。真實(shí)有效的擔(dān)保,是指在借貸、買(mǎi)賣(mài)、貨物運(yùn)輸、加工承攬等合同中,為保障債權(quán)的實(shí)現(xiàn),合同債務(wù)人或者第三人采用合法形式,以保證、抵押、質(zhì)押、留置或定金方式向債權(quán)人提供的擔(dān)保。以偽造、變?cè)臁⒆鲝U的票據(jù)或者其他虛假的產(chǎn)權(quán)證明作擔(dān)保的,不僅對(duì)合同債權(quán)人權(quán)利的實(shí)現(xiàn)不能起到有效擔(dān)保的作用,而且證明行為人主觀上確有非法占有對(duì)方當(dāng)事人財(cái)物的故意。根據(jù)我國(guó)《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guān)規(guī)定,“以偽造、變?cè)臁⒆鲝U的票據(jù)或者其他虛假的產(chǎn)權(quán)證明作擔(dān)保”及“隱瞞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擔(dān)保條件的抵押物、債權(quán)文書(shū)等作為合同履行的擔(dān)保”的,均應(yīng)認(rèn)定沒(méi)有真實(shí)有效的擔(dān)保。
3、有無(wú)履行合同的能力。有無(wú)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判斷行為人有無(wú)非法占有目的的一個(gè)重要方面。按照通常的理解,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指合同當(dāng)事人按照法律或者合同規(guī)定,在約定的時(shí)間、地點(diǎn),以約定的方式交付符合約定數(shù)量、質(zhì)量的合同標(biāo)的,完成合同約定義務(wù)的能力。考察履行合同的能力,一般側(cè)重于行為人簽訂合同時(shí)所擁有的資金、貨物和技術(shù)狀況。但是,市場(chǎng)條件下的合同交易,已不再是簡(jiǎn)單的現(xiàn)貨交易,市場(chǎng)交易主體所擁有的資金、貨物和技術(shù)也隨時(shí)處于變動(dòng)之中,不能要求所有的合同當(dāng)事人都在有了足以保證合同履行的資金、貨物或技術(shù)之后,再選擇合適的對(duì)方當(dāng)事人簽訂合同。因此,除了考察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shí)有無(wú)履行合同的現(xiàn)實(shí)性外,還應(yīng)當(dāng)考慮有無(wú)履行合同的可能性。所謂履行合同的可能性,應(yīng)當(dāng)是指簽訂合同時(shí),行為人雖然不具有足以保障合同履行的資金、貨物或技術(shù),但有充分依據(jù)證實(shí),在簽訂合同之后至履行合同之前,有可能籌集到足夠的資金、貨物或配備齊相應(yīng)的技術(shù)條件以保障合同的按約履行,如即將實(shí)現(xiàn)的到期債權(quán)、與他人簽訂的貨物買(mǎi)賣(mài)合同、技術(shù)服務(wù)合同等。對(duì)于不僅在簽訂合同時(shí)不具備履行合同的能力,甚至在簽訂合同后直至履行合同之前,也不可能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行為人,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4、有無(wú)履行合同的誠(chéng)意和行為。履行合同的誠(chéng)意和履行合同的行為往往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具備履行合同的誠(chéng)意,往往就會(huì)有履行合同的積極行為。有無(wú)履行合同的行為,是區(qū)別合同詐騙與合同欺詐的一個(gè)重要方面。一般說(shuō)來(lái),凡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cái)產(chǎn)目的的行為人,在依據(jù)合同取得對(duì)方當(dāng)事人的資金或貨物后,總是想方設(shè)法地拖賬、賴(lài)賬,逃避履行合同約定義務(wù)。因此,有無(wú)履行合同的行為,也是認(rèn)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cái)物目的的依據(jù)之一。有無(wú)履行合同的行為,主要根據(jù)行為人收取對(duì)方資金或貨物后,是否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nèi),實(shí)施了履行約定義務(wù)的行為或者為履行約定義務(wù)作了積極的努力。如果在合同約定期限內(nèi),雖然沒(méi)有實(shí)施履行約定義務(wù)的行為,但確為履行約定義務(wù)作了積極的努力,并采取了必要的補(bǔ)救措施,也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有履行合同的行為。但必要的補(bǔ)救措施必須是真實(shí)有效的,否則應(yīng)認(rèn)定為逃避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wù)。
5、行為人取得財(cái)物后的處置行為。合同當(dāng)事人在取得對(duì)方款物后,應(yīng)當(dāng)用于符合合同目的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如果行為人攜帶對(duì)方支付的貨款、貨物、預(yù)付款、定金、保證金等財(cái)產(chǎn)逃跑或者大肆揮霍、浪費(fèi),或者將財(cái)產(chǎn)隱匿、轉(zhuǎn)移,用于投機(jī)和違法犯罪活動(dòng)等,且拒不返還或無(wú)法返還,也可以認(rèn)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是司法實(shí)踐中較容易混淆、不易區(qū)分的一對(duì)范疇,如果國(guó)家公權(quán)力對(duì)合同詐騙這一類(lèi)觸犯刑律的犯罪不予干涉,那么很容易導(dǎo)致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秩序的混亂乃至崩潰,也會(huì)使公眾對(duì)國(guó)家的法制失去信心,而去遵循所謂“潛規(guī)則”行事。但如果國(guó)家公權(quán)力過(guò)分介入經(jīng)濟(jì)糾紛,又容易扭曲市場(chǎng)機(jī)制,窒息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主體的活力。因此,對(duì)合同欺詐行為和合同詐騙犯罪區(qū)分的意義就在于把國(guó)家權(quán)力介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程度限定在一個(gè)適度的標(biāo)準(zhǔn)上。通過(guò)界定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行為,來(lái)達(dá)到保證整個(g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既充滿活力又秩序井然的目的。
天津市高級(jí)人民法院:董志勇
 點(diǎn)贊
點(diǎn)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