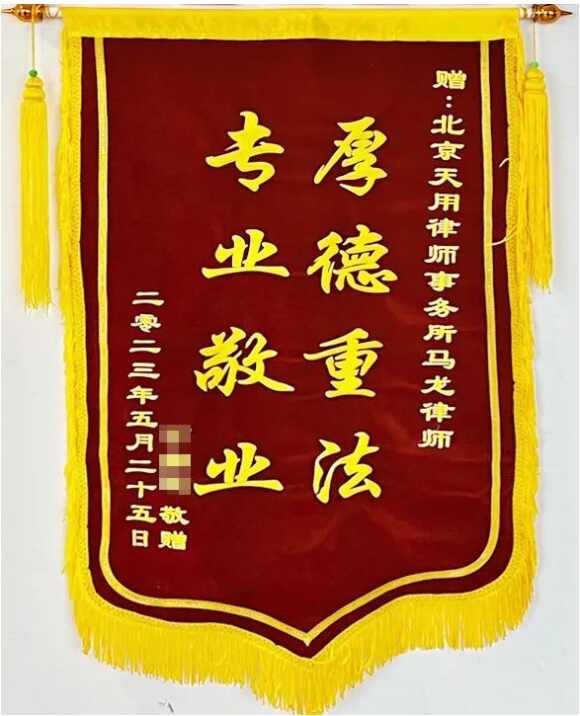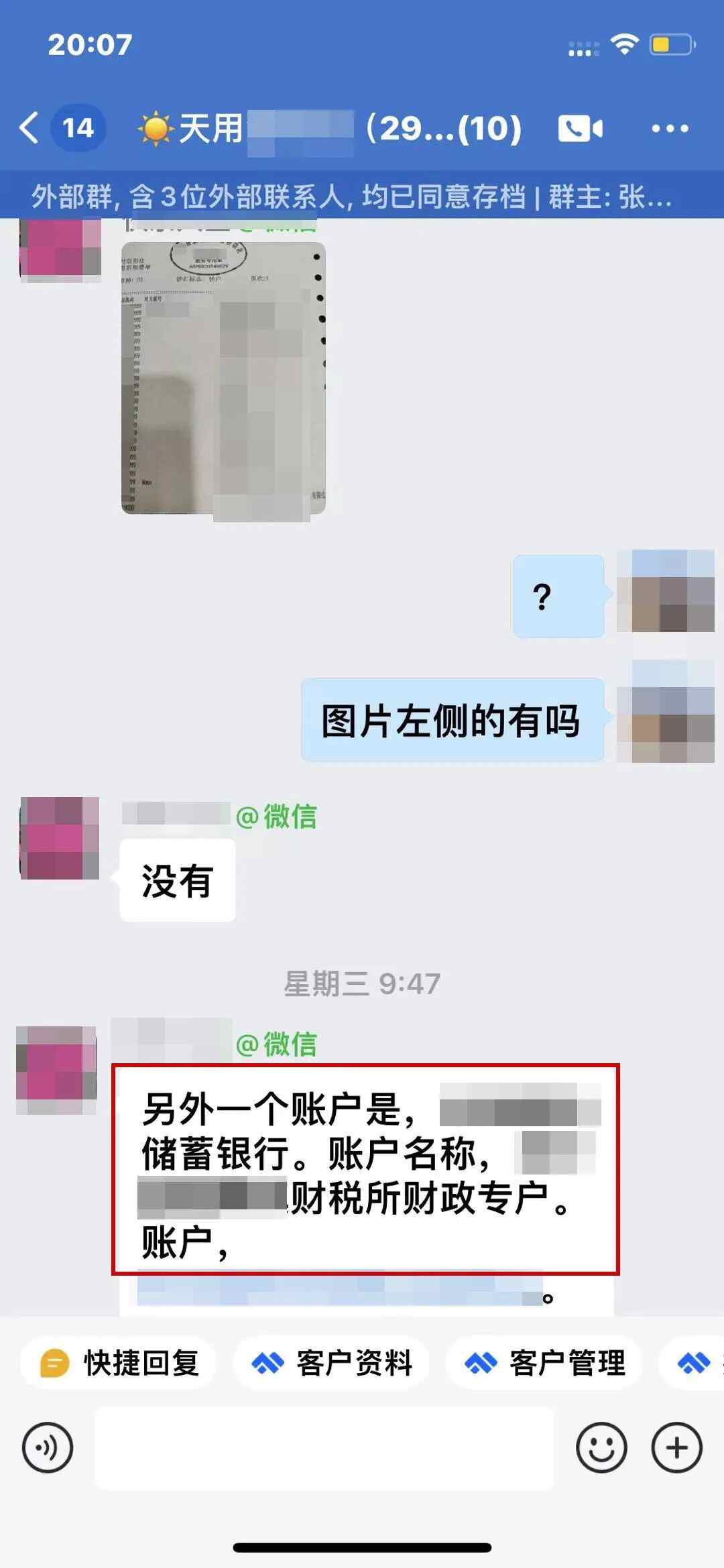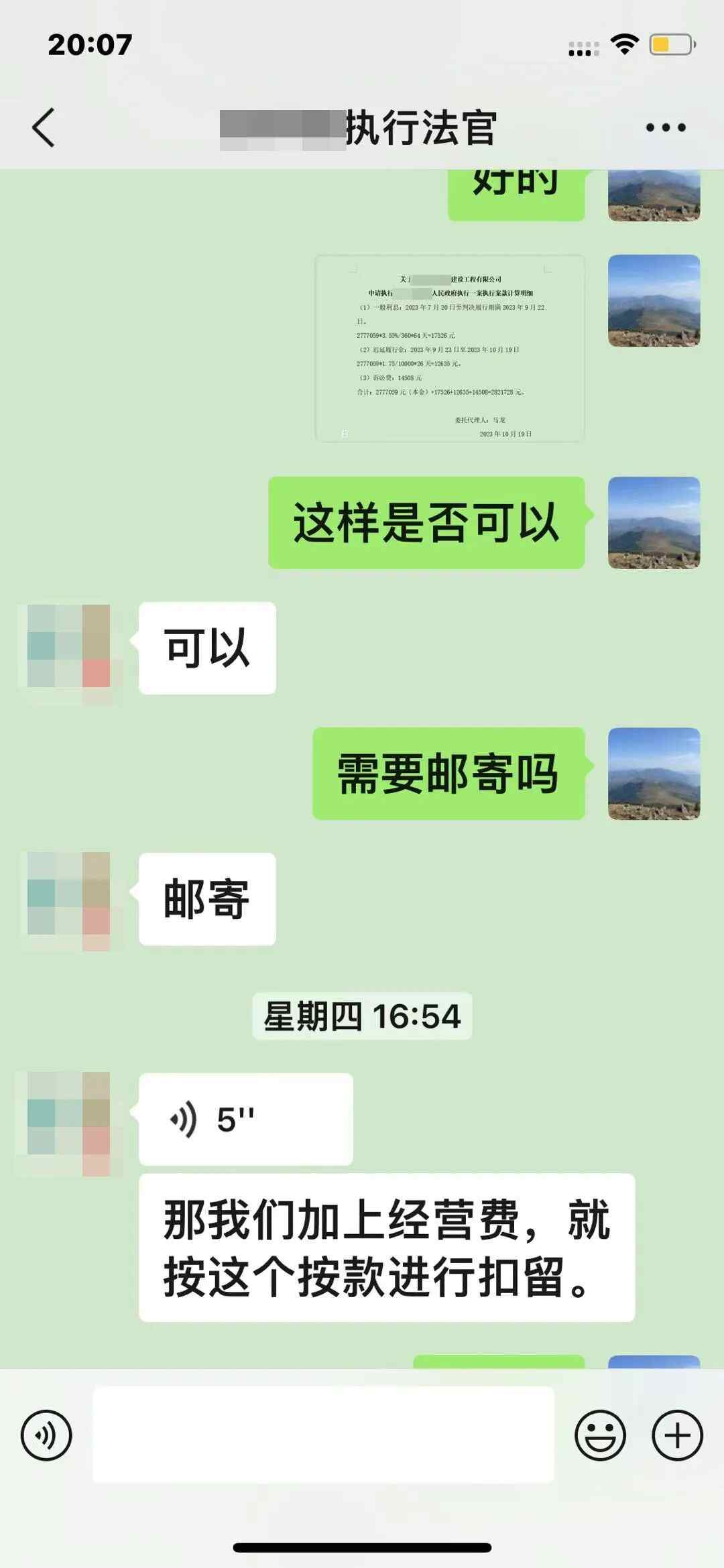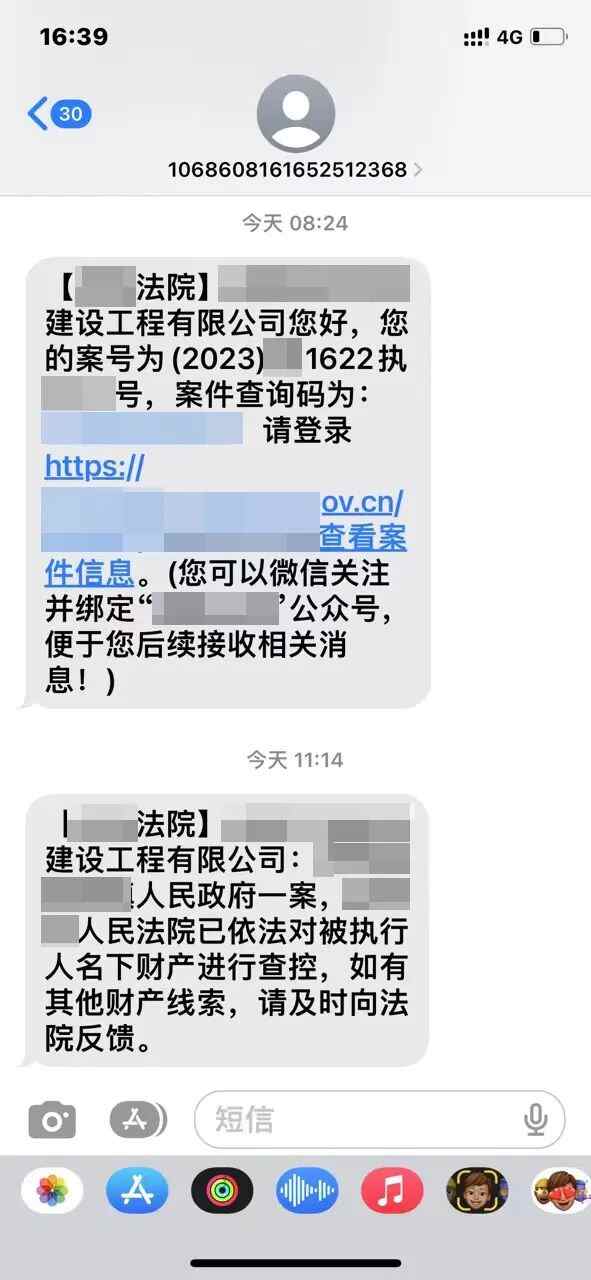怎么分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
 邢穎律師2021.12.241033人閱讀
邢穎律師2021.12.241033人閱讀
導(dǎo)讀:
但是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則因其本質(zhì)的差異而被列入了違法與犯罪這兩個既相互關(guān)聯(lián),又相互區(qū)分的法律范疇。研究合同欺詐行為,必然要聯(lián)系傳統(tǒng)民法學(xué)理論中“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這樣一來,合同欺詐行為作為違反意思自治基本原則的行為,便不同于嚴(yán)格意義的違法行為。這就意味著,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欺詐行為只能成為合同可變更或撤消的理由。那么怎么分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guān)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但是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則因其本質(zhì)的差異而被列入了違法與犯罪這兩個既相互關(guān)聯(lián),又相互區(qū)分的法律范疇。研究合同欺詐行為,必然要聯(lián)系傳統(tǒng)民法學(xué)理論中“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這樣一來,合同欺詐行為作為違反意思自治基本原則的行為,便不同于嚴(yán)格意義的違法行為。這就意味著,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欺詐行為只能成為合同可變更或撤消的理由。關(guān)于怎么分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的法律問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欺詐”與“詐騙”,單就兩個概念本身而言,應(yīng)該說沒有太大的區(qū)別,二者都包含著虛構(gòu)事實、隱瞞真相,以違背當(dāng)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的基本法律內(nèi)涵。但是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則因其本質(zhì)的差異而被列入了違法與犯罪這兩個既相互關(guān)聯(lián),又相互區(qū)分的法律范疇。筆者試就其不同的法律內(nèi)涵,淺談其構(gòu)成要件及其區(qū)分與界定,以期對司法實踐有所裨益。
一
我國民事法律所定義的合同欺詐行為,是指簽訂合同的一方當(dāng)事人故意告之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dāng)事人在違背其真實意思的情況下,簽訂和履行合同的行為。
構(gòu)成要件如下:
第一、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欺詐的故意,并以誘使對方當(dāng)事人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為目的。合同欺詐的主觀故意同時包含了兩層意思,即故意地為不真實之表示行為和故意地使相對人因此而陷入錯誤而為意思表示。合同欺詐的成立,兩層意思缺一不可。實踐中,行為人已有以不真實情況而為表示的行為,且已引起對方當(dāng)事人陷入錯誤而為意思表示,但行為人卻并不知道自己的表示行為是不真實的;或者行為人雖然明知自己所表示之事項為不真實或夸大,但僅為引起對方的興趣和注意,而并無使其陷入錯誤而為意思的目的,均不屬于欺詐。
第二、在客觀上,行為人實施了欺詐行為。行為人具有告之對方虛假情況,或隱瞞真實情況的客觀表現(xiàn)。行為人既可表現(xiàn)為作為的方式,也可表現(xiàn)為本應(yīng)作為而不作為的方式。
第三、相對人因受欺詐而陷入錯誤。對合同內(nèi)容及其它重要情況產(chǎn)生認(rèn)識缺陷。而這種錯誤認(rèn)識是因行為人的欺詐行為所致,即相對人的錯誤與行為人的欺詐行為之間有因果關(guān)系。
第四、相對人因錯誤認(rèn)識而為意思表示,與行為人簽訂合同或履行合同。錯誤的意思表示是以錯誤的認(rèn)識為直接動因。
研究合同欺詐行為,必然要聯(lián)系傳統(tǒng)民法學(xué)理論中“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意思自治,也就是我國《民法通則》上所稱的“自愿”,即指民事主體意志自由;它是民事行為的自主性對于法律規(guī)范的內(nèi)在要求。作為傳統(tǒng)民法學(xué)理論的核心內(nèi)容,意思自治原則也是當(dāng)今各國民事行為的通行準(zhǔn)則;它要求保障當(dāng)事人從事民事活動時的意志自由,不受國家權(quán)力和其他當(dāng)事人的非法干預(yù)。那么,民事行為中一旦存在一方當(dāng)事人對另一方當(dāng)事人的欺詐,則是對“意思自治”基本原則的違反。因而,從廣義上講,合同欺詐行為是一種民事違法行為,它是對民法基本原則的違反。
另一方面,因為意思自治作為民法基本原則,它并不具有作為民法規(guī)范所要求的明確的行為模式和確定的保證手段的構(gòu)成成份;其本身并非法律規(guī)范,而屬于非規(guī)范性規(guī)定中的原則性規(guī)定;它并非產(chǎn)生法律關(guān)系的獨立依據(jù),而只有補充的性質(zhì),必須與其他民法規(guī)范結(jié)合起來才能發(fā)揮法律調(diào)整的作用。這樣一來,合同欺詐行為作為違反意思自治基本原則的行為,便不同于嚴(yán)格意義的違法行為。這也就是我國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將違法行為與欺詐等違反當(dāng)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的行為并列為導(dǎo)致民事行為無效的兩個不同事由的原因所在。
1999年我國合同法的頒布,更進(jìn)一步反映了我國民事立法對于“意思自治”基本精神的深入理解和民事法律規(guī)范在“意思自治”基本原則下的進(jìn)步和完善。根據(jù)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四條之規(guī)定,對于欺詐行為,我們已經(jīng)不能簡單地將之歸入必然導(dǎo)致合同無效的情形之列。一方以欺詐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其合同無效;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quán)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jī)構(gòu)變更或者撤消。這就意味著,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欺詐行為只能成為合同可變更或撤消的理由。合同并不當(dāng)然無效,還有成為有效的可能性,使因為種種原因而不打算推翻已成立的合同的受欺詐一方當(dāng)事人可以保持因該合同所獲得的利益。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合同欺詐行為其效力的界定,日益偏重于被欺詐人意志自由的選擇,否定了其行為的必然無效性,從而進(jìn)一步弱化了合同欺詐行為的違法性。
二
合同詐騙犯罪,作為一種犯罪現(xiàn)象,它與不同形態(tài)的社會生產(chǎn)方式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并隨著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和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變化而變化。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一書中指出:“犯罪-孤立的個人反對統(tǒng)治關(guān)系的斗爭,和法一樣,也不是隨心所欲地產(chǎn)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現(xiàn)行的統(tǒng)治都產(chǎn)生于相同的條件。”因此,任何一種犯罪都有其滋生的特定溫床與背景-即特定的社會形態(tài)。
近年來,我國經(jīng)濟(jì)體制處于新舊轉(zhuǎn)換時期,市場主體多元化,經(jīng)濟(jì)運行的機(jī)制尚不規(guī)則,資源配置逐漸市場化,新舊體制同時起著重要作用,市場關(guān)系和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的錯綜復(fù)雜給行騙者投機(jī)鉆營提供了可乘之機(jī)。由于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合同成為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不可缺少的行為契約。合同行騙與合同欺詐因其競合性、重合性、隱蔽性而難以區(qū)分,滋生了不法分子的犯意,助長了不法分子的犯罪氣焰。

我國1997年刑法在第224條增設(shè)了利用合同進(jìn)行詐騙的犯罪。根據(jù)刑法的規(guī)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dāng)事人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
作為一種新類型的犯罪,合同詐騙罪必然具備犯罪的三個基本屬性:嚴(yán)重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應(yīng)受刑法懲罰性。就犯罪構(gòu)成而言,它具有以下構(gòu)成要件:
第一、該罪侵犯的客體是合同管理秩序和公私財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為實現(xiàn)一定目的而簽訂的具有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的協(xié)議。犯罪行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產(chǎn)為目的,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他人錢財,不僅侵害了合同的管理秩序,擾亂了市場經(jīng)濟(jì)秩序,也侵害了他人財產(chǎn)權(quán)益,具有嚴(yán)重的社會危害性。
第二、在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了欺騙的手段。所謂欺騙,就是虛構(gòu)事實或隱瞞真相。即行為人捏造客觀上不存在的事實,騙取受害人的信任,使其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而與之訂立或履行合同;或者根據(jù)法律、合同和交易慣例有義務(wù)告知對方當(dāng)事人真實的情況而故意不予告知。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guī)定了五種行為,明確了合同詐騙罪在客觀方面的具體表現(xiàn)。
第三、主觀方面,合同詐騙罪行為人表現(xiàn)為直接故意,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既包括意圖本人對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圖為單位或者第三人對非法所得的占有。[page]
第四、行為人利用合同騙取的財物必須數(shù)額較大。利用合同騙取的財物數(shù)額的大小,是衡量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的主要根據(jù)。只有當(dāng)數(shù)額達(dá)到一定程度,才能認(rèn)定其行為構(gòu)成犯罪。
市場經(jīng)濟(jì)條件下,合同糾紛日趨增多,利用合同進(jìn)行犯罪的現(xiàn)象也十分突出。由于這類犯罪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現(xiàn)的,具有相當(dāng)?shù)膹?fù)雜性、隱蔽性和欺騙性,往往與合同糾紛交織在一起,相互間容易糾纏不清。這就給司法活動增添了相當(dāng)?shù)碾y度,必須在理論上對于兩者的界限有明確的認(rèn)識和區(qū)分。
三
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在行為方式上都表現(xiàn)為虛構(gòu)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特征。籠統(tǒng)而言,我們可以認(rèn)為合同欺詐是均可構(gòu)成合同詐騙的前提案件,合同詐騙則是合同欺詐的“量”達(dá)到一定程度的“質(zhì)”的飛躍,具有量變到質(zhì)變的關(guān)系。但是,作為犯罪行為的合同詐騙,與民事關(guān)系中的合同欺詐行為,必然存在本質(zhì)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就是罪與非罪的區(qū)別。
我國《刑法》第三條明確規(guī)定“法律明文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就是《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nèi)容。它要求對一切行為人的定罪量刑,必須以法律明文規(guī)定為界限。這種界限往往取決于定罪的法律標(biāo)準(zhǔn),也就是犯罪行為構(gòu)成要件的法律規(guī)定性。因此,合同詐騙犯罪與合同欺詐行為的區(qū)別就在于其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法律規(guī)定性,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是否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是區(qū)分合同詐騙犯罪與合同欺詐行為的主要依據(jù)。
目的是指行為人通過實施具體的行為,所期望達(dá)到的結(jié)果。這是行為人主觀上所具有的一種心理狀態(tài),它體現(xiàn)了行為人的主觀愿望。合同詐騙犯罪表現(xiàn)為行為人通過實施虛構(gòu)事實或隱瞞真相的行為以達(dá)到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主觀上沒有履行合同的意圖。而合同欺詐行為往往只是違反“意思自治”的民事原則,使對方當(dāng)事人作出了錯誤意思表示,其目的是獲取不當(dāng)或不法利益,合同欺詐行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意圖。
2、獲得財物的數(shù)額的大小是區(qū)分合同詐騙犯罪與合同欺詐行為的重要依據(jù)。
經(jīng)濟(jì)活動中一般所涉及的對象都是有形的,具有財產(chǎn)價值的,可以測量具體數(shù)額大小的。合同欺詐與合同詐騙所指向的對象,所造成的直接結(jié)果,所獲得的非法利益等等,大都能夠以數(shù)額予以衡量。因此,衡量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之大小,數(shù)額成了重要的標(biāo)志。我國刑事立法對于合同詐騙犯罪的認(rèn)定,明確規(guī)定了數(shù)額較大的構(gòu)成要件,要求騙取財物達(dá)到“數(shù)額較大”的程度的行為才能構(gòu)成犯罪。而合同欺詐行為的成立,不以數(shù)額大小為標(biāo)準(zhǔn)。
3、有無基本履約行為是區(qū)分合同詐騙犯罪與合同欺詐行為的關(guān)鍵依據(jù)。
合同詐騙犯罪的目的決定了行為人沒有履行合同的意圖,客觀上沒有基本的履行合同的行為。有時也可能有少量履約,但實質(zhì)上是一種假象。而合同欺詐行為人正是要通過合同的履行來獲得非法利益,客觀上,必然會有履約的行為。
4、是否應(yīng)受懲罰是合同詐騙犯罪與合同欺詐行為在性質(zhì)上的區(qū)別。
合同訂立和履行中的欺詐行為是一種民事侵權(quán)行為,在民事法律制度將“意思自治”原則貫徹到合同、契約領(lǐng)域時,法律對于行為雙方當(dāng)事人意志自由的尊重已達(dá)到“至高無上”的程度。因此合同欺詐作為合同可變更或撤消的法定事由并非必然導(dǎo)致契約行為的無效,合同欺詐行為人并非必然導(dǎo)致民事責(zé)任的承擔(dān)。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被欺詐一方當(dāng)事人的意志自由:他可以選擇要求依法確認(rèn)合同無效,并由欺詐行為人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民事責(zé)任;也可以選擇承認(rèn)合同的效力,對于欺詐行為人不追究任何責(zé)任。然而,合同詐騙犯罪則不同,它作為一種犯罪行為,必然具有應(yīng)受刑罰處罰這一基本特征。一旦行為人的行為符合刑法分則關(guān)于合同詐騙犯罪構(gòu)成的基本特征,則行為人不可避免地應(yīng)該受到刑罰處罰,這是國家強制力的體現(xiàn),并非任何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
四
主觀動機(jī)和目的是意識領(lǐng)域的產(chǎn)物,最終通過客觀行為表現(xiàn)出來。在正確區(qū)分了合同詐騙犯罪與合同欺詐行為的前提下,如何確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即成為劃清兩者的關(guān)鍵之所在。根據(jù)現(xiàn)行法律及司法解釋規(guī)定,實踐中應(yīng)以如下幾個方面來加以掌握:
(一)考察行為人的主體資格是否真實。
在經(jīng)濟(jì)活動中,簽約是為了履約。即使是合同欺詐,也只有通過履約才能實現(xiàn)其經(jīng)濟(jì)目的,也就決定了在主體資格上不會弄虛作假。反之,一旦行為人在簽約時是以虛假的面目出現(xiàn),以虛構(gòu)的單位或假冒他人簽訂合同,即可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二)考察行為人有無履約能力。
行為人客觀上有無實際履約能力,是判斷其主觀目的的重要方面。凡客觀上不具有履約能力,不難判定行為人主觀上無履約意圖和目的,從而也證明其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履約能力包括現(xiàn)實性和可能性兩種情況。現(xiàn)實性即為行為人簽約時就有了履約能力,可能性是指行為人在簽約時還不具備履約能力,而在履約期限屆滿前,將可能變?yōu)楝F(xiàn)實。履約能力的現(xiàn)實可能性不同于虛假的可能性。是現(xiàn)實履約能力的強有力的補充。
(三)查明行為人有無實際履約行為。
履約能力不能作為衡量行為性質(zhì)的唯一決定依據(jù)和基本出發(fā)點。即使行為人客觀上有實際履約能力,也還必須進(jìn)一步查明其是否有實際履約行為。在合同詐騙犯罪中,由于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是通過合同這種表面的合法形式來非法占有對方當(dāng)事人的財物。因而,一旦詐騙成功,合同款項或財物到手,行為人就不會向?qū)Ψ铰男辛x務(wù)了。或者僅履行小額合同而逃避更大的義務(wù),表面上在實施履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段。從整體上看不影響行為的非履約性和詐騙性。
(四)分析行為人不履約的原因。
合同詐騙行為人沒有實際履約行為,但并非未履約便一定是詐騙,要分析其未履約的原因,標(biāo)準(zhǔn)是行為人是否為履約而進(jìn)行了努力。行為人在簽合同時本有履約能力,但簽約后卻不積極為履約創(chuàng)造條件,不愿實現(xiàn)其履約行為,亦說明其主觀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之目的。
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是兩個既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區(qū)別的概念。在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中對于“合同欺詐行為與合同詐騙犯罪的區(qū)分與界定 ”這一命題的研究,對于我們理論水平的提高和實踐能力的增強都有重要的意義。[page]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