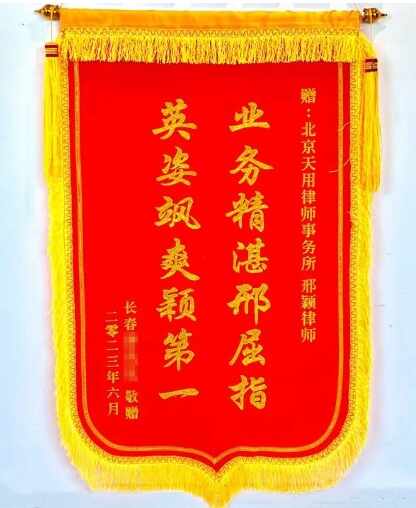單位是主犯自然人是從犯的刑事責任確定問題
 李楠楠律師2022.01.17421人閱讀
李楠楠律師2022.01.17421人閱讀
導讀:
如何解決這一兩難問題筆者以為可從單位犯罪的主體身份入手以身份犯與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有關理論解決單位主犯與自然人從犯之間刑事責任的分配問題,關于單位實行犯罪自然人提供幫助情形中如何分別確定單位主犯與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問題,而對單位主犯和自然人從犯分別按照各自的刑法條款確定刑事責任大小在適用法律上遵循了自然人犯罪和單位犯罪分別定罪處罰的刑法立法格局但是有可能出現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重于單位主犯的刑事責任的不合理結果。
單位實施犯罪自然人提供幫助依照共同犯罪的原理單位是主犯自然人是從犯這當無疑問。解決了單位的身份犯問題在單位是主犯自然人是從犯的共同犯罪場合如何確定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就涉及到非身份犯與身份犯的共同犯罪認定問題。單位與自然人共同犯罪相當于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犯罪確定無身份者的刑事責任可適用區別對待的原則即單位與自然人同為實行犯的情況下一般應當依照單位的犯罪性質定罪但也有可能出現分別定罪的情況。關于單位是主犯自然人是從犯的刑事責任確定問題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刑事辯護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關于單位實行犯罪自然人提供幫助情形中如何分別確定單位主犯與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問題。單位實施犯罪自然人提供幫助依照共同犯罪的原理單位是主犯自然人是從犯這當無疑問。但是如何分別確定單位主犯與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從罪刑相適應的角度對自然人和單位均按照單位犯罪的量刑幅度來定罪處罰比較符合案件的實際情況。比如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中對個人按個人走私來處理很可能造成對從犯的處罰比對主犯的處罰還重。另一種觀點認為對這種情況仍然應當分別適用單位犯罪和個人犯罪的條款處罰。理由是從立法原意角度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為例單位犯罪因為有責任分擔問題有為團體謀取利益的因素對其定罪處刑較輕。但是個人參與走私與其參與其他共同犯罪沒有本質區別。對單位與個人分別適用相關條款處罰與各自社會危害性相適應。而且刑法修改后對從犯從輕、減輕處罰也是對與其犯罪相適應的法定刑從輕、減輕不存在比照主犯從輕、減輕的問題。因此應當分別適用個人犯罪和單位犯罪的法律規定進行處罰。
筆者認為一味依照單位犯罪的量刑幅度來確定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或者簡單地分別依照自然人和單位犯罪的條款確定刑事責任都有不足之處。依據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規定自然人犯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根據走私偷逃應繳稅額的大小可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不等刑罰。而單位犯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最重僅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兩者刑罰量不可謂不懸殊。依照單位主犯的刑事責任確定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確實能夠避免出現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重于單位主犯刑事責任的尷尬局面。但是自然人從犯畢竟不是單位犯罪理應依照自然人犯罪的有關規定定罪量刑用單位犯罪刑事責任代以自然人犯罪刑事責任在理論上有不通之處。而對單位主犯和自然人從犯分別按照各自的刑法條款確定刑事責任大小在適用法律上遵循了自然人犯罪和單位犯罪分別定罪處罰的刑法立法格局但是有可能出現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重于單位主犯的刑事責任的不合理結果。如何解決這一兩難問題筆者以為可從單位犯罪的主體身份入手以身份犯與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有關理論解決單位主犯與自然人從犯之間刑事責任的分配問題。
關于單位是不是刑法意義上的身份犯問題。理論界對單位是不是刑法意義上的身份存在爭議。筆者認為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一樣也存在身份犯即特殊的單位才能構成的犯罪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的違規制造、銷售槍支罪該罪的主體是特殊單位即依法被指定、確定的槍支制造企業、銷售企業其他一般單位不能構成此罪。除此之外單位本身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身份。解決了單位的身份犯問題在單位是主犯自然人是從犯的共同犯罪場合如何確定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就涉及到非身份犯與身份犯的共同犯罪認定問題。刑法理論界對此有不同的觀點(1)主張以主要實行犯的定罪處罰標準為基點。在單位為主實行犯罪個人起次要或幫助作用的情形下定罪量刑均應適用單位犯罪的相關規定。(2)主張按主犯的犯罪性質來定罪。
單位與自然人共同犯罪相當于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犯罪確定無身份者的刑事責任可適用區別對待的原則即單位與自然人同為實行犯的情況下一般應當依照單位的犯罪性質定罪但也有可能出現分別定罪的情況。(1)單位與自然人只是各自利用本人的身份或職務便利并沒有利用對方的身份或者職務便利也應認定構成共同犯罪但應分別定罪處罰。單位與自然人不僅利用了本人的身份或職務便利而且還相互利用了對方的身份或職務便利宜按其中刑法重點保護的身份客體即重點打擊的職務犯罪來確定共同犯罪的性質對各行為人按統一的罪名定罪處罰。具體而言在共同犯罪中當單位是主犯自然人是從犯時定罪量刑均應適用單位犯罪的相關規定。理由在于依照單位犯罪的相關規定確定自然人的刑事責任不會造成自然人從犯的刑事責任大于單位主犯的量刑失衡的后果。在經濟犯罪中單位犯罪的起刑點一般遠高于自然人犯罪的起刑點如果采取單位主體與自然人主體分別量刑的方法就很有可能出現單位不構成犯罪或者構成輕罪而自然人構成犯罪或者構成重罪主、從犯之間量刑失衡甚至是倒置顯然不利于懲治犯罪。
此外當單位與自然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當時也就是都是主犯時對犯罪單位與犯罪自然人應分別按照各自的量刑標準確定刑事責任不必對自然人再適用單位犯罪的相關條款。當然由于刑法對單位和自然人設置的量刑幅度存在一定差別在某些犯罪中可能懸殊還較大因此在分別對單位與自然人確定刑事責任時要充分注意兩者間刑罰的均衡避免差距過大。例如在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中往往會出現單位不構成刑事責任而自然人構罪的情況這時如果對單位和自然人分別定罪單位不構罪自然人構罪。考慮到單位與自然人是共同實施走私犯罪即使不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也要有相關主管單位對其施以必要的行政處罰而在對自然人定罪的前提下對其可從輕量刑符合法定條件時可考慮免予刑事處罰。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