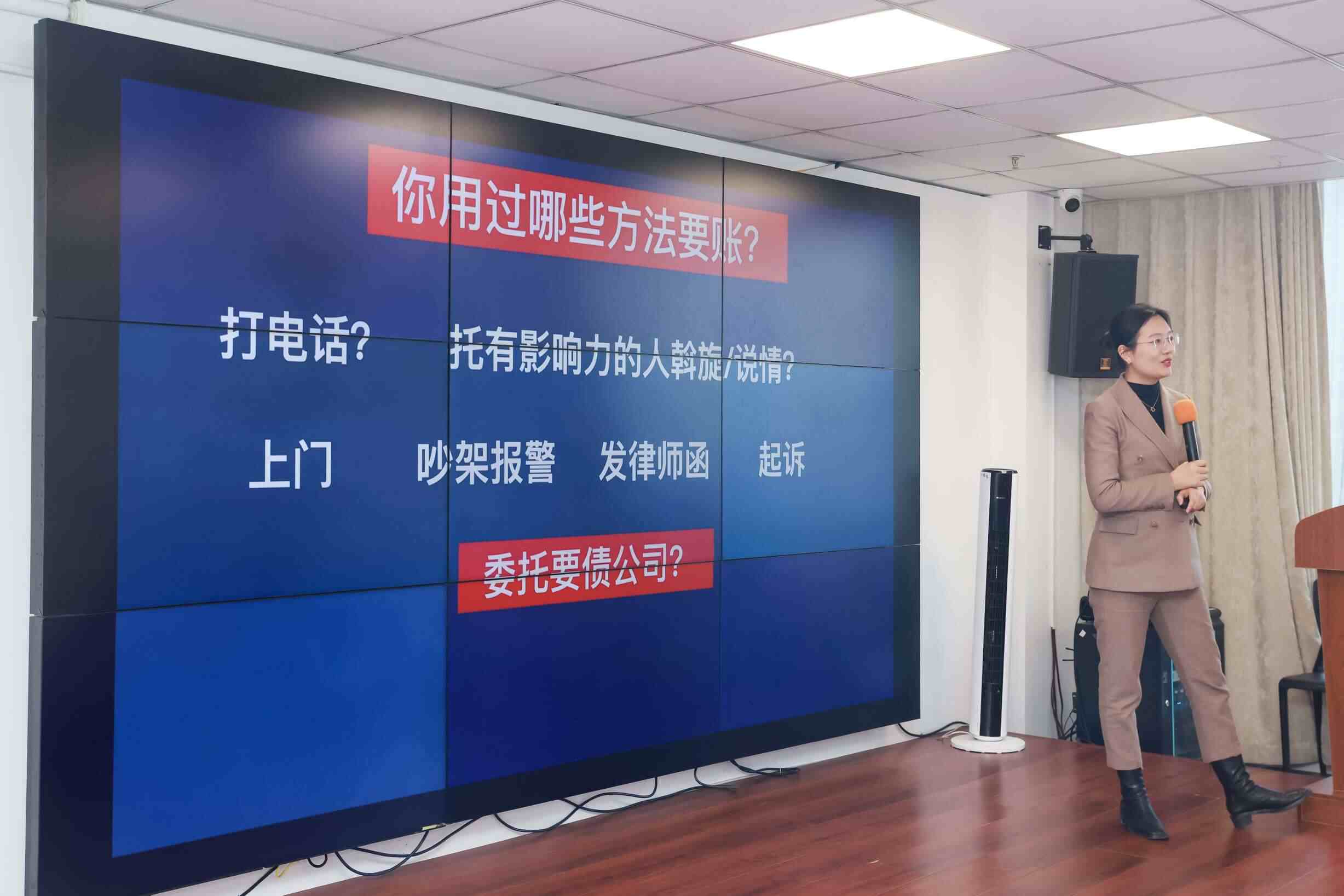處理瀆職罪共犯的三大問題
 元甲交通律師律師2022.01.17937人閱讀
元甲交通律師律師2022.01.17937人閱讀
導(dǎo)讀:
刑法總則在解決共同犯罪問題上并未涉及身份犯共犯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少數(shù)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時刑法采用立法條文個別化設(shè)置或司法解釋來解決上述不足,刑法總則在解決共同犯罪問題上并未涉及身份犯共犯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少數(shù)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時刑法采用立法條文個別化設(shè)置或司法解釋來解決上述不足,從瀆職犯罪構(gòu)成要件看瀆職犯罪的實行行為即刑法分則所規(guī)定的由行為人所實施的反映瀆職犯罪違背職責(zé)義務(wù)這種本質(zhì)特征的作為或不作為其內(nèi)在要素之一就是職務(wù)行為因而即使是有身份者和無身份者共同實施了事實上的行為并非兩者都是共同實行犯只有前者才是實行犯后者只能是教唆犯或幫助犯。
刑法總則在解決共同犯罪問題上并未涉及身份犯共犯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少數(shù)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時刑法采用立法條文個別化設(shè)置或司法解釋來解決上述不足。本文試對瀆職犯罪中有關(guān)共犯的幾個主要問題展開討論以探求其規(guī)律。筆者認為就瀆職犯罪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除外而言在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犯罪場合無身份者不能成立共同實行犯。關(guān)于處理瀆職罪共犯的三大問題的法律問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刑事辯護律師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刑法總則在解決共同犯罪問題上并未涉及身份犯共犯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少數(shù)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犯罪行為時刑法采用立法條文個別化設(shè)置或司法解釋來解決上述不足。如對瀆職犯罪的共犯之認定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在2003年4月16日關(guān)于非司法工作人員是否可以構(gòu)成徇私枉法共犯問題的答復(fù)中規(guī)定非司法工作人員與司法工作人員勾結(jié)共同實施徇私枉法行為構(gòu)成犯罪的應(yīng)當以徇私枉法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zé)任。可見雖然刑法分則及相關(guān)司法解釋對身份犯共犯問題有所涉及但并未形成一般性規(guī)范并指導(dǎo)司法實踐。因而對身份犯共犯的有關(guān)問題有必要進行探討。本文試對瀆職犯罪中有關(guān)共犯的幾個主要問題展開討論以探求其規(guī)律。
一、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能否構(gòu)成身份犯之共同實行犯
無身份者可以構(gòu)成有身份者的教唆犯和幫助犯歷來被公認我國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對此也予以認可。但是對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能否構(gòu)成有身份者實施犯罪的共同實行犯理論界看法并不一致。主要包括三種觀點即肯定說、否定說與折中說。肯定說之論者對此予以認可否定說論者則拒絕承認而折中說則認為應(yīng)當根據(jù)具體情況區(qū)別對待在有些場合應(yīng)當承認無身份者可以構(gòu)成有身份者的共同實行犯。
筆者認為就瀆職犯罪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除外而言在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犯罪場合無身份者不能成立共同實行犯。這是因為瀆職犯罪的主體均是特定主體即必須具備特定身份而這種身份是由法律賦予的法律在賦予這種身份的同時也加諸一定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這些法定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在行為上就表現(xiàn)為職務(wù)上特定的要求即行為時是以職務(wù)為條件的所有的瀆職犯罪都與行為人所擔(dān)任的職務(wù)密切相關(guān)并且都發(fā)生在行為人執(zhí)行職務(wù)活動中。從瀆職犯罪構(gòu)成要件看瀆職犯罪的實行行為即刑法分則所規(guī)定的由行為人所實施的反映瀆職犯罪違背職責(zé)義務(wù)這種本質(zhì)特征的作為或不作為其內(nèi)在要素之一就是職務(wù)行為因而即使是有身份者和無身份者共同實施了事實上的行為并非兩者都是共同實行犯只有前者才是實行犯后者只能是教唆犯或幫助犯。比如私放在押人員罪中司法工作人員利用押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職務(wù)便利將其放走職務(wù)行為就是其實行行為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而無此身份者即不具有此種職務(wù)便利。若要成為共犯只能是教唆或幫助。再如徇私舞弊減刑、假釋、暫予監(jiān)外執(zhí)行罪也是具有報請、裁定、決定或者批準減刑、假釋、暫予監(jiān)外執(zhí)行權(quán)的司法工作人員才可以實施。在這些犯罪中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的身份是作為犯罪主體要件中的特別要素而存在的法律將這種特定身份設(shè)定于犯罪構(gòu)成要件中一般就表明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行為的性質(zhì)。該種犯罪之所以成為真正身份犯也是由這種身份決定的。因此在瀆職犯罪中由于其實行行為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性質(zhì)因而無身份者在與有身份者實施瀆職犯罪時不能成為共同實行犯。
二、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共同實施犯罪如何定性
在刑法理論界關(guān)于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犯罪如何定性爭議較大。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為分別定罪說。即有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無身份者按普通犯定罪。
第二種為有身份者的實行行為決定犯罪性質(zhì)說。即依有身份者所實施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行為來定罪即使無身份者是主犯也不影響上述定罪原則。
第三種為主犯行為性質(zhì)決定說。主張根據(jù)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來定罪如果主犯是有身份的按身份犯來定罪主犯無身份的則以無身份者所犯之罪定罪。這一學(xué)說一直為司法實務(wù)界所支持。
第四種為依有身份者之行為性質(zhì)定罪說。該觀點認為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共同實施要求特定身份者才能單獨構(gòu)成之罪不管有身份者是否為主犯、是否為實行犯無身份者均利用了有身份者之身份分別定罪或按主犯身份定罪均不符合犯罪之實際危害和特點而依有身份者之行為性質(zhì)定罪才比較妥當。
筆者認為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構(gòu)成共犯如何定性關(guān)鍵在于確定無身份者的定罪問題。在瀆職犯罪的司法實踐中針對這種情況需要分別討論
第一無身份者與有身份者共同實施瀆職犯罪刑法分則對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均規(guī)定罪名的應(yīng)依分別定罪說加以認定即對有身份者應(yīng)認定為瀆職罪對無身份者另定他罪。比如私放在押人員罪在有些情況下司法工作人員與在押人員相互配合實施犯罪此時因為刑法分則對有身份者和無身份者分別規(guī)定罪名對于司法工作人員一般不能認定為脫逃罪的共犯。如果將其定為脫逃罪的共犯私放在押人員罪就會形同虛設(shè)在實踐中不再有適用的可能。類似這種情況在瀆職犯罪中比比皆是例如放縱走私罪與走私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與偷稅罪、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罪與生產(chǎn)銷售偽劣商品罪、辦理偷越國邊境人員出入境證件罪與偷越國邊境罪等對于這類犯罪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主觀上共謀但各自實施不同行為即使成立共犯但刑法明確規(guī)定不同罪名的依照法律定罪。因為共同犯罪并不意味著必須以同一罪名加以認定在某些情況下共同犯罪也不排除罪名的不一致。
第二無身份者的行為在刑法分則中沒有對應(yīng)罪名的如甲為一般主體乙為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二人合謀實施瀆職犯罪的甲的行為在刑法分則中難以找到對應(yīng)的犯罪在此情況下應(yīng)依有身份者之行為性質(zhì)定罪說加以認定因為此時整個犯罪行為都被打上了身份的烙印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的行為實際上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故應(yīng)當進行綜合評價。比如非法批準征用、占用土地罪招收公務(wù)員、學(xué)生徇私舞弊罪濫用管理公司、證券職權(quán)罪等。在這些場合無身份者的行為在刑法分則中沒有對應(yīng)罪名然其行為畢竟具備了相當程度的社會危害性而且符合共犯的幫助犯之特征如果僅僅追究有身份者的刑事責(zé)任勢必造成司法不公。因此應(yīng)當以有身份者所成立的身份犯之共犯進行定罪處罰。
此外有身份者與無身份者構(gòu)成共犯情況下對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以相應(yīng)瀆職犯罪進行定罪量刑明顯較輕如何處理對此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有人認為只能認定瀆職罪另有人主張如果對其以瀆職罪以外的其他罪名的共犯處罰更重的可以認定為該罪名的共犯。例如放縱制售偽劣商品犯罪行為罪原則上對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以本罪認定但如果以生產(chǎn)、銷售偽劣商品罪的共犯定罪處罰更重則將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作為生產(chǎn)、銷售偽劣商品罪的共犯定罪處罰這屬于刑法中的想象競合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放縱行為實際上兼有瀆職罪構(gòu)成要件與其他個罪共犯構(gòu)成要件的雙重性質(zhì)即一行為同時觸犯數(shù)罪名應(yīng)當依照想象競合犯的處罰原則對行為人擇一重罪處斷。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