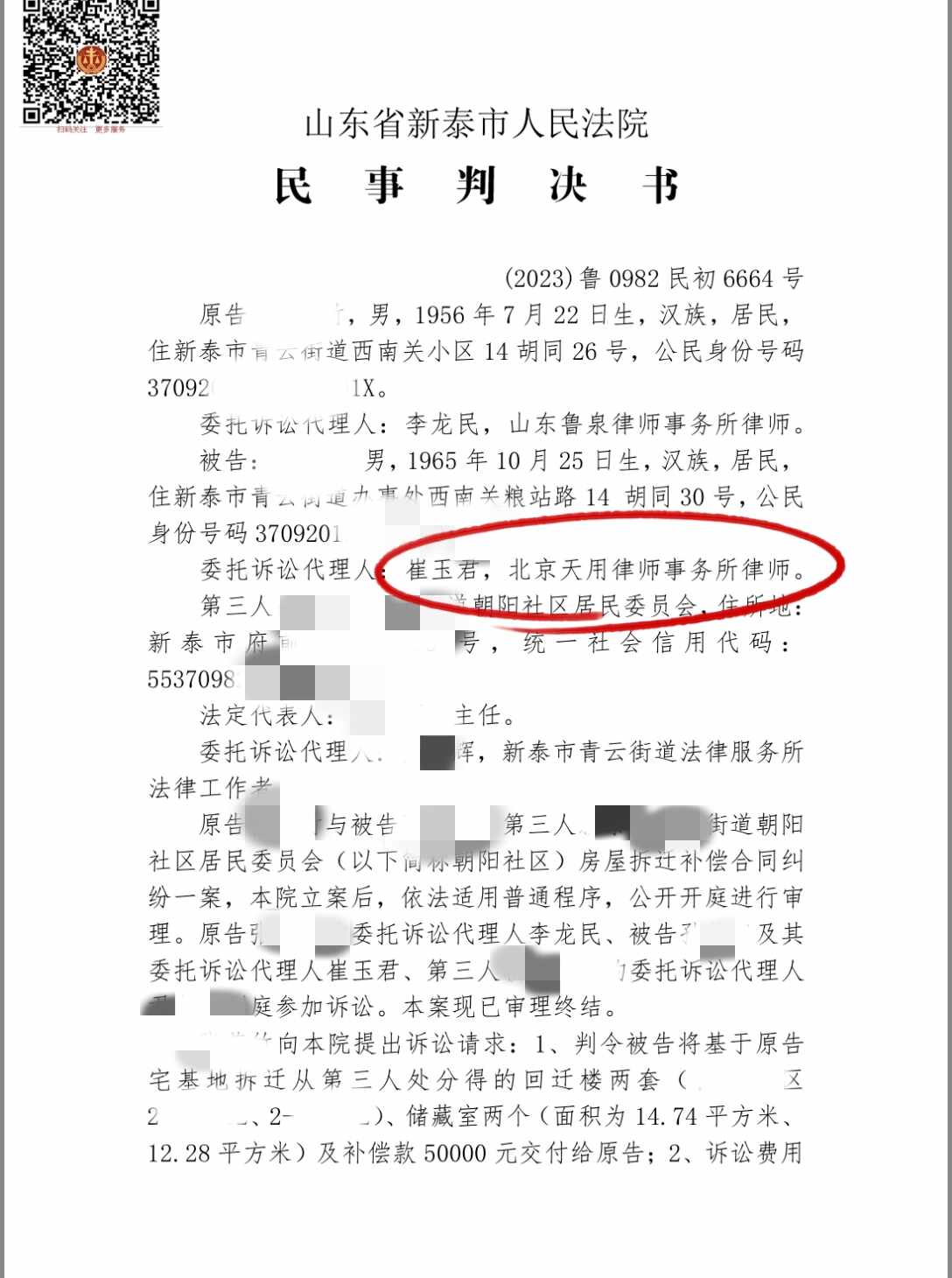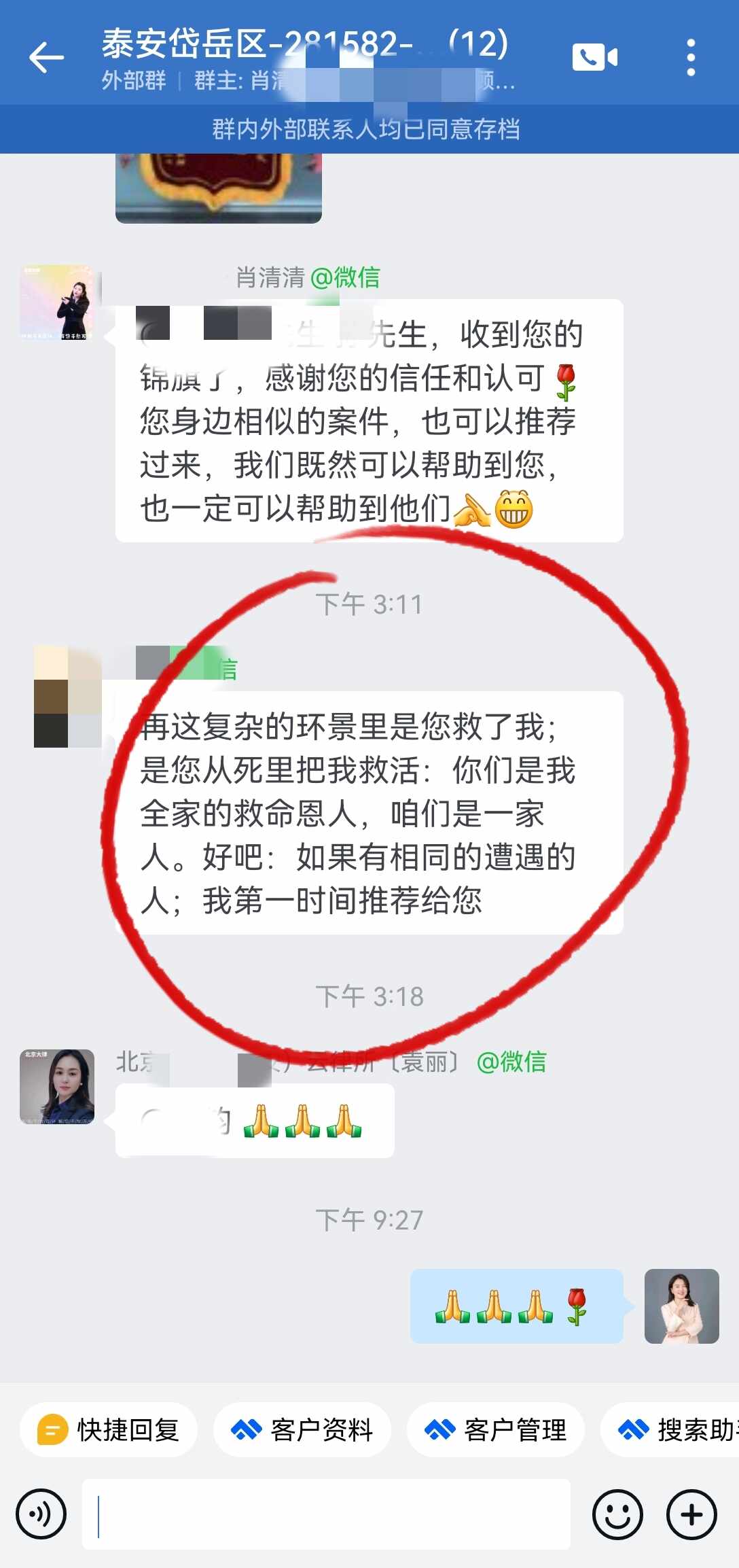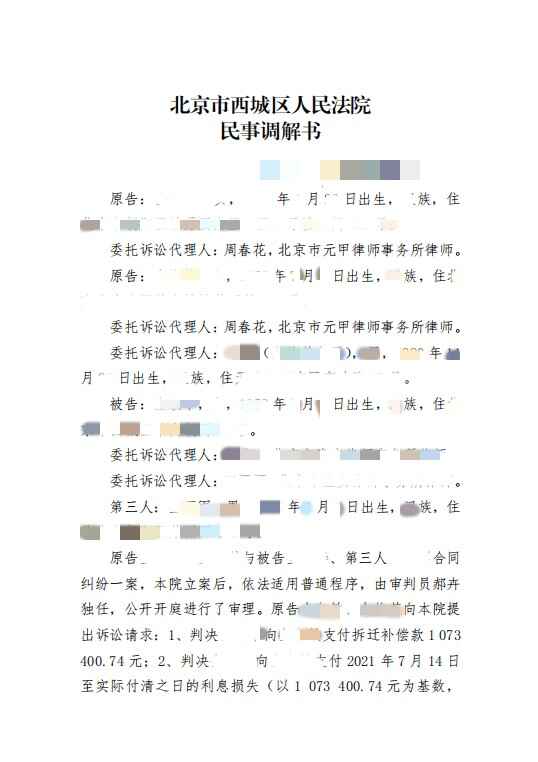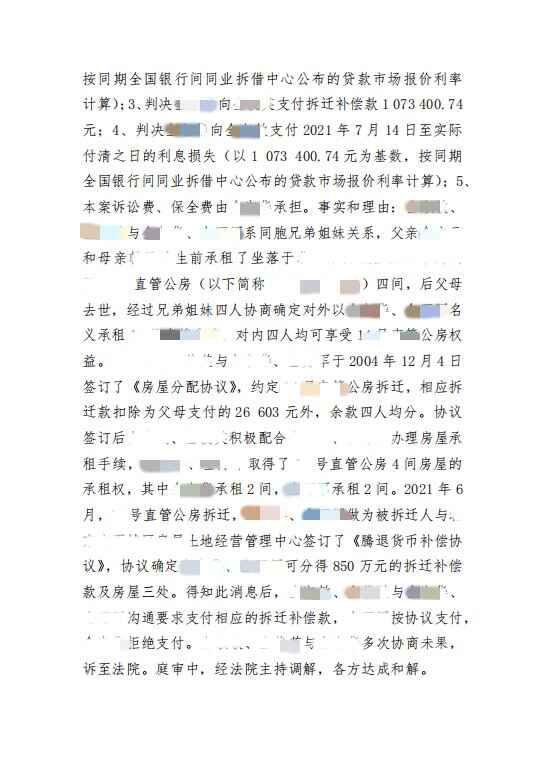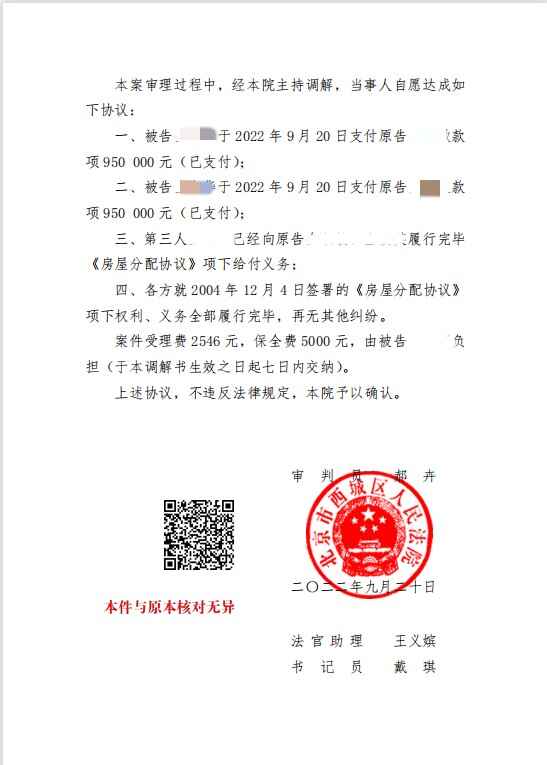對(duì)《城市房屋拆遷管理?xiàng)l例》的合憲、合法性的質(zhì)疑
 李維律師2022.01.02180人閱讀
李維律師2022.01.02180人閱讀
導(dǎo)讀:
城市房屋拆遷近十年來(lái),演化成最易產(chǎn)生劇烈沖突的一個(gè)領(lǐng)域。拆遷的強(qiáng)制性正是誘發(fā)過(guò)激沖突的根源。2001年國(guó)務(wù)院出臺(tái)《城市房屋拆遷管理?xiàng)l例》,兩年來(lái)各地都據(jù)此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行政立法。何謂“拆遷”,引用條例的管轄定義,“在城市規(guī)劃區(qū)內(nèi)國(guó)有土地上實(shí)施房屋拆遷,并需要對(duì)被拆遷人補(bǔ)償、安置的,適用本條例”。房屋拆遷的本質(zhì),是賣(mài)方處分自己土地使用權(quán)和房屋所有權(quán)的私人行為,或買(mǎi)方基于契約而產(chǎn)生的合同權(quán)利。憑什么強(qiáng)制除財(cái)產(chǎn)權(quán)外,強(qiáng)制拆遷所侵犯的還有兩種同等重要的對(duì)象。拆遷管理?xiàng)l例以“房屋拆遷”這一行政指令性概念,掩蓋和代替了房地產(chǎn)轉(zhuǎn)讓中的契約概念。那么對(duì)《城市房屋拆遷管理?xiàng)l例》的合憲、合法性的質(zhì)疑。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guān)知識(shí),希望能幫助大家。
城市房屋拆遷近十年來(lái),演化成最易產(chǎn)生劇烈沖突的一個(gè)領(lǐng)域。拆遷的強(qiáng)制性正是誘發(fā)過(guò)激沖突的根源。2001年國(guó)務(wù)院出臺(tái)《城市房屋拆遷管理?xiàng)l例》,兩年來(lái)各地都據(jù)此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行政立法。何謂“拆遷”,引用條例的管轄定義,“在城市規(guī)劃區(qū)內(nèi)國(guó)有土地上實(shí)施房屋拆遷,并需要對(duì)被拆遷人補(bǔ)償、安置的,適用本條例”。房屋拆遷的本質(zhì),是賣(mài)方處分自己土地使用權(quán)和房屋所有權(quán)的私人行為,或買(mǎi)方基于契約而產(chǎn)生的合同權(quán)利。憑什么強(qiáng)制除財(cái)產(chǎn)權(quán)外,強(qiáng)制拆遷所侵犯的還有兩種同等重要的對(duì)象。拆遷管理?xiàng)l例以“房屋拆遷”這一行政指令性概念,掩蓋和代替了房地產(chǎn)轉(zhuǎn)讓中的契約概念。關(guān)于對(duì)《城市房屋拆遷管理?xiàng)l例》的合憲、合法性的質(zhì)疑的法律問(wèn)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房產(chǎn)糾紛律師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shí),希望能幫助大家。
城市房屋拆遷近十年來(lái),演化成最易產(chǎn)生劇烈沖突的一個(gè)領(lǐng)域。拆遷的強(qiáng)制性正是誘發(fā)過(guò)激沖突的根源。數(shù)年前央視曾報(bào)道東北某市一拆遷戶手持菜刀,誓不離開(kāi)自己的家,并砍傷爬窗強(qiáng)行入戶的消防干警。但這一事件背后的悲涼與絕望,卻在知法普法的法制宣傳主題下被遮蔽了。直到南京自焚事件,把拆遷戶的絕望以極端方式爆發(fā)了出來(lái)。同時(shí)近年來(lái),人們也漸漸懂得了“法治”的要義并不在于簡(jiǎn)單的知法守法,而在于讓法律成為個(gè)人權(quán)利的保護(hù)神。“惡法非法”這一體現(xiàn)憲政和法治精神的原則,通過(guò)由孫志剛案件帶來(lái)收容遣送制度被廢止的個(gè)案,也開(kāi)始被更多人了解和接受。
何謂“拆遷”?
2001年國(guó)務(wù)院出臺(tái)《城市房屋拆遷管理?xiàng)l例》,兩年來(lái)各地都據(jù)此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行政立法。但筆者認(rèn)為條例任意擴(kuò)大“強(qiáng)制拆遷”范圍,是近年來(lái)拆遷糾紛走向尖銳化的根源。何謂“拆遷”,引用條例的管轄定義,“在城市規(guī)劃區(qū)內(nèi)國(guó)有土地上實(shí)施房屋拆遷,并需要對(duì)被拆遷人補(bǔ)償、安置的,適用本條例”。這一定義僅排除了自行拆遷的情形,而將一切因土地使用權(quán)轉(zhuǎn)讓帶來(lái)的拆遷都囊括在“強(qiáng)制拆遷”之內(nèi)。不像以前只有被納入城市改造或政府工程的項(xiàng)目才搞強(qiáng)制拆遷。這一規(guī)定的法理依據(jù)是非常糊涂的,它強(qiáng)調(diào)拆遷發(fā)生在“國(guó)有土地”上,似乎為政府強(qiáng)制力量介入提供了一個(gè)氣壯的理由。但它忽略和抹煞了另一個(gè)更重要的事實(shí),即這些“國(guó)有土地”是政府已經(jīng)向私人有償出讓了土地使用權(quán)的土地。政府的身份有兩種解釋,一是土地所有權(quán)人的名義,一是社會(huì)管理者的名義。但政府既然拿地?fù)Q了錢(qián),就不能再以土地所有權(quán)人的身份強(qiáng)制性介入。政府擁有土地所有權(quán)并不構(gòu)成強(qiáng)制的理由,相反,政府不擁有土地使用權(quán)構(gòu)成了不能強(qiáng)制的理由。因?yàn)閺?qiáng)制拆遷的本質(zhì)就是政府單方面收回土地使用權(quán)。 “土地使用權(quán)”是一種物權(quán),土地使用權(quán)及其附著的房屋所有權(quán)是老百姓用一生積蓄換來(lái)的、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拆遷問(wèn)題首先不關(guān)乎補(bǔ)償,而關(guān)乎對(duì)私人產(chǎn)權(quán)的剝奪。
無(wú)論《城市房地產(chǎn)管理法》還是《土地管理法》,都未提及“房屋拆遷”這一概念。因?yàn)榉课莶疬w的基礎(chǔ)是房地產(chǎn)交易,無(wú)交易即無(wú)拆遷。只要國(guó)家不收回私有房屋的土地使用權(quán),拆遷的實(shí)質(zhì)就是一種私法意義上的履約行為,而非行政法上的概念。即便拆遷行為因?yàn)橛绊懙匠鞘信涮捉ㄔO(shè)而需要進(jìn)行規(guī)范和管理,這種作為社會(huì)管理者角色的管理權(quán)限,也不可能包括違背產(chǎn)權(quán)人意志的強(qiáng)制拆遷在內(nèi)。政府的強(qiáng)制拆遷只能發(fā)生在一種前提下,即政府強(qiáng)制性的收回了某幅地的土地使用權(quán)。只有土地使用權(quán)被政府合法的強(qiáng)制性收回,才會(huì)產(chǎn)生出強(qiáng)制拆遷的行政權(quán)力。而征用有著嚴(yán)格的程序和要求,只發(fā)生于政府自身因公益而用地的情形。
房屋拆遷的本質(zhì),是賣(mài)方處分自己土地使用權(quán)和房屋所有權(quán)的私人行為,或買(mǎi)方基于契約而產(chǎn)生的合同權(quán)利。兩方面都和政府無(wú)關(guān)。但《條例》借口“國(guó)有土地上的拆遷”這一混淆的概念,通過(guò)強(qiáng)制禠奪了拆遷戶的土地使用權(quán)。為什么說(shuō)私有財(cái)產(chǎn)權(quán)是憲政制度的基石,就因?yàn)楣珯?quán)力對(duì)它的侵犯是無(wú)所不在的。強(qiáng)制性退耕,強(qiáng)制性拆遷,強(qiáng)制性安裝或不安裝防護(hù)欄,強(qiáng)制性使用統(tǒng)一的店鋪招牌,禁止在陽(yáng)臺(tái)上晾內(nèi)衣,禁止在家門(mén)口放泡菜壇子,以及亂罰款亂收費(fèi)等。只有當(dāng)這些政府行為的背后,存在一個(gè)財(cái)產(chǎn)權(quán)先于國(guó)家權(quán)力的憲政原則,法律才可能在個(gè)人財(cái)產(chǎn)權(quán)和政府權(quán)力之間劃出具體的邊界。
憑什么強(qiáng)制
除財(cái)產(chǎn)權(quán)外,強(qiáng)制拆遷所侵犯的還有兩種同等重要的對(duì)象。一是私法領(lǐng)域內(nèi)的“契約自由”,一是公法領(lǐng)域內(nèi)的司法權(quán)力。
拆遷管理?xiàng)l例以“房屋拆遷”這一行政指令性概念,掩蓋和代替了房地產(chǎn)轉(zhuǎn)讓中的契約概念。強(qiáng)制力的在場(chǎng),使一切商業(yè)性用地的締約和談判過(guò)程被扭曲,事實(shí)上侵犯和取消了拆遷戶的契約自由。無(wú)論各地政府對(duì)于補(bǔ)償問(wèn)題和估價(jià)問(wèn)題進(jìn)行怎樣的立法,有的城市合理些,有些城市不盡合理,但都無(wú)法改變一個(gè)事實(shí),即拆遷戶與開(kāi)發(fā)商簽訂的合同是在推土機(jī)之下締結(jié)的“城下之盟”。

一個(gè)尋常百姓都知道的簡(jiǎn)單法律常識(shí),任何一筆合同如果一方當(dāng)事人違約,我們是不能自己去強(qiáng)制的,也不可能找任何政府部門(mén)出面強(qiáng)制。我們只能去打官司。只有法院通過(guò)訴訟才能產(chǎn)生出強(qiáng)制執(zhí)行合同的權(quán)力。這就是司法權(quán)獨(dú)立的一個(gè)基本內(nèi)容,即只有法院才有權(quán)對(duì)具有司法性質(zhì)的糾紛進(jìn)行裁決,并有權(quán)對(duì)什么是屬于司法性質(zhì)的糾紛作出判斷。但《條例》以行政法上的“拆遷期限”魚(yú)目混珠,替代了合同中的履約期限。這就一方面剝奪契約自由,自我授權(quán)擁有了強(qiáng)制執(zhí)行合同的行政權(quán)力,另一方面也僭取了法院的司法裁判權(quán)和強(qiáng)制執(zhí)行權(quán)。這使房產(chǎn)開(kāi)發(fā)商與房產(chǎn)權(quán)利人之間的合同成為一種準(zhǔn)行政合同,成為一切合同中的一個(gè)例外,即政府直接擁有強(qiáng)制執(zhí)行一份私人契約的特權(quán)。這一特權(quán)的存在,使開(kāi)發(fā)商帶著刀子走進(jìn)每一筆合同的談判現(xiàn)場(chǎng)。《條例》從制度上營(yíng)造了一個(gè)在法理上導(dǎo)致合同無(wú)效的“脅迫”條件。而當(dāng)強(qiáng)制力直接掌握在政府部門(mén)(政府的另一個(gè)身份是土地使用權(quán)一級(jí)市場(chǎng)上的壟斷者)手中時(shí),開(kāi)發(fā)商利用和勾結(jié)這種強(qiáng)制力的機(jī)會(huì)更高,成本極小。如周正毅一案中我們所見(jiàn)的那樣。[page]
有人以為政府擁有強(qiáng)制拆遷權(quán)力會(huì)更好的提高效率,而訴諸司法的成本可能太高,萬(wàn)一拆遷戶漫天要價(jià)怎么辦呢。此起彼伏的拆遷紛爭(zhēng)和慘絕人寰的自焚事件已使這一觀點(diǎn)不攻自破。但我還要指出一點(diǎn)是人們通常對(duì)法律的強(qiáng)制力存在一種誤解。套用斯密的一句名言,“用得最少的強(qiáng)制才是最好的強(qiáng)制”,強(qiáng)制力的最大效用是構(gòu)成一種“法律陰影”,一種法律所預(yù)設(shè)的潛在的懲罰結(jié)果,會(huì)對(duì)當(dāng)事人雙方構(gòu)成一種必須達(dá)成妥協(xié)的成本衡量的壓力。潛在的而非現(xiàn)實(shí)的強(qiáng)制,才會(huì)最有效率的迫使雙方找到雙贏的解決之道。打個(gè)比方,強(qiáng)制力絕不是某一方當(dāng)事人可以帶進(jìn)場(chǎng)去的刀子,而是談判現(xiàn)場(chǎng)被供起來(lái)的“關(guān)二爺”。請(qǐng)出這種強(qiáng)制力的成本、風(fēng)險(xiǎn)和結(jié)果,促使開(kāi)發(fā)商和拆遷戶進(jìn)行理性的妥協(xié)。
這也是為什么契約的強(qiáng)制必須交給司法權(quán)力的原因之一。除了公正和獨(dú)立的程序正義外,恰恰是司法的高成本有效的催化和保障了契約自由之下的私法自治。一個(gè)看似矛盾的現(xiàn)實(shí)是,“不出場(chǎng)的司法強(qiáng)制”使百分之九十九的契約都不需要強(qiáng)制。而在房屋拆遷中“出場(chǎng)的政府強(qiáng)制”卻導(dǎo)致層出不窮的抗?fàn)幒屠习傩兆顟K烈的過(guò)激反彈。正是因?yàn)閺?qiáng)制拆遷的立等可取,才使交易雙方徹底失去平等的妥協(xié)動(dòng)機(jī)和博弈能力。
邏輯上講,如果政府有權(quán)在私人擁有使用權(quán)的土地上強(qiáng)制執(zhí)行私人契約進(jìn)行拆遷,那政府也就有權(quán)在私人擁有使用權(quán)的土地上強(qiáng)制執(zhí)行建筑合同,非要修房子不可。這是極其荒唐的。法治的進(jìn)步方向之一,是將一個(gè)“行政的國(guó)家”(警察國(guó)家)轉(zhuǎn)變?yōu)橐粋€(gè)“司法的國(guó)家”,以潛在的司法懲罰之下的私法自治,逐步置換政府的行政強(qiáng)制力。《城市房屋拆遷管理?xiàng)l例》顯然與這一方向存在抵牾,并因財(cái)產(chǎn)權(quán)原則的缺席無(wú)法定出政府權(quán)力的邊界。根據(jù)憲法和立法法對(duì)該條例的“合憲性”進(jìn)行審查,把“強(qiáng)制拆遷”限制在政府因公益收回土地使用權(quán)的情形下。這將是防止類似南京自焚悲劇繼續(xù)出現(xiàn)的根本途徑。
 點(diǎn)贊
點(diǎn)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