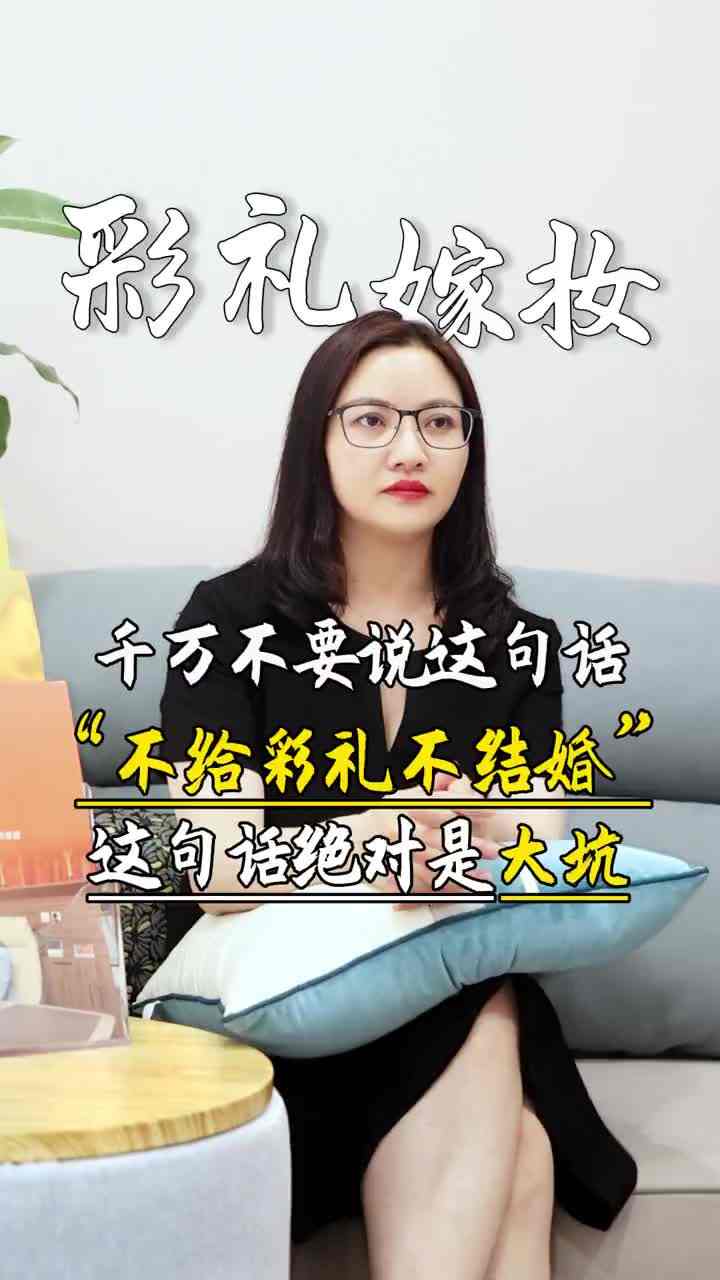彩禮返還制度研究(二)
 郭銘芝律師2021.12.24345人閱讀
郭銘芝律師2021.12.24345人閱讀
導讀:
獲得該項財物也是以“索取”而不是對方“主動”或“自愿”給予為前提的。“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獲得者應是女方本人。1951年《聘金或聘禮處理的指示》第1條將“以索取對方一定的財物為結婚條件”認定為“變相的買賣婚姻”。“純正的聘娶婚所異于現代志愿婚者,不過屬于兩族或兩家之契約,非盡以男女兩方之意志為主已耳。由于從后果上看,國家對前者的責難程度要遠高于對后者的,因此“大量”要比“許多”高。那么彩禮返還制度研究(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獲得該項財物也是以“索取”而不是對方“主動”或“自愿”給予為前提的。“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獲得者應是女方本人。1951年《聘金或聘禮處理的指示》第1條將“以索取對方一定的財物為結婚條件”認定為“變相的買賣婚姻”。“純正的聘娶婚所異于現代志愿婚者,不過屬于兩族或兩家之契約,非盡以男女兩方之意志為主已耳。由于從后果上看,國家對前者的責難程度要遠高于對后者的,因此“大量”要比“許多”高。關于彩禮返還制度研究(二)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婚姻家庭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三)“彩禮”與“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間的關系
1.“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解釋
依據文意解釋和歷史解釋的方法,“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應做出以下解釋:(1)“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也是以立法者或準立法者將“聘娶婚之性質”確定為“買賣婚”為前提的。如果不將聘娶婚在性質上認定為買賣婚姻,“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也就無從談起。
(2)獲得該項財物也是以“索取”而不是對方“主動”或“自愿”給予為前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1950年4月13日)第2條規定,“……禁止任何人借婚姻關系問題索取財物。”最高法院《關于軍人婚約和聘禮問題的復函》(1951年6月1日)明確指出,“如聘禮系由訂婚人父母或男女雙方基于自愿幫助或贈與”,則不屬于“變相的買賣婚姻”;反之,如系“索取的財物”則屬之。依據1979年《民事意見》之有關規定,“……男女主動互相贈與和贈送對方父母的財物……”與“女方向男方要了許多財物,或父母從中要了一部分財物”具有根本區別。
(3)“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獲得者應是女方本人。1951年《聘金或聘禮處理的指示》第1條將“以索取對方一定的財物為結婚條件”認定為“變相的買賣婚姻”。它比較明確地暗示著“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獲得者是女方本人。而1979年《民事意見》認為,“女方”的“父母”也可以是獲得者。這一規定不妥。其理由是:①它不符合“聘娶婚”的特征。“純正的聘娶婚所異于現代志愿婚者,不過屬于兩族或兩家之契約,非盡以男女兩方之意志為主已耳。”[1]換言之,雙方結婚是為當事人雙方本人或其家長所不反對的。由于“納采”(依據現代民法,在性質上應屬附卜得吉兆為條件的同意)“問名”、“納吉”(依據現代民法,在此時“婚約”已經成立)在先,而納征(即交付聘財)在后,還由于“納征”只不過起是否“許嫁”,即婚約是否成立的“證明”作用,因此聘財的交付其實是建立在合意基礎之上的。只不過由于在聘娶婚中女家向男家“索取”了聘財,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將其定性為“買賣婚姻”;由于在聘娶婚中存在“父母之命”,[2]所以又將其定性為“包辦強迫婚姻”。而1979年《民事意見》卻認為,只有“買賣婚姻”(即1951年《聘金或聘禮處理的指示》所稱的“公開的買賣婚姻”)才是“第三者(包括父母)以索取大量財物為目的”的,才是“包辦強迫”婚姻,而“借婚姻索取財物”(即1951年《聘金或聘禮處理的指示》所稱的“變相的買賣婚姻”)是建立在“婚姻基本上自主自愿”基礎之上的,顯然違反了立法本意;②以“財物數額”為準劃分“公開的買賣婚姻”和“變相的買賣婚姻”也不科學。1979年《民事意見》認為,如果財物數額是“大量”的,則構成“公開的買賣婚姻”;如果是“許多”的,則構成“變相的買賣婚姻”。由于從后果上看,國家對前者的責難程度要遠高于對后者的,因此“大量”要比“許多”高。而在實踐中,收買被拐賣的婦女成婚支出的費用要遠遠低于男家在正常訂婚過程中支出的。[3]③由于婚約在民事上沒有法律效力,由于違反婦女意志的性行為構成強jian罪等原因,男方一般不會盲目地、冒險地向女方家給付大量錢財。因此,女方父母先“包辦”[4]訂婚、然后收取彩禮,如女孩不從則進行強迫恐怕也不多見。
2.“彩禮”與“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間的關系
由于“彩禮”與“聘金”或“聘禮”只不過具有名稱上的差別,因此女方獲得的彩禮也就是女方獲得的聘金或聘禮。由于女方獲得的聘禮依據1951年《聘金或聘禮處理的指示》被認定為“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因此,“女方獲得的彩禮”之法律性質也就是“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1984年《民事意見》第18條將“女方獲得的彩禮”在內的財物統稱為“借婚姻關系索取的財物”。
3.法律漏洞的補充
在離婚時“女方獲得的彩禮”之返還問題上,1984年《民事意見》第18條和1993年《離婚時財產分割的意見》第19條第1款與《婚姻法解釋(二)》第10條盡管總體上一致,但還是具有以下細微的區別:(1)返還的條件不同。前者是:①“結婚時間不長”;②“因索要財物造成對方生活困難”;后者是:①“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②“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2)返還的范圍不同。前者只需“酌情返還”,后者沒有這一限制。由于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女方獲得的彩禮”和“借婚姻索取財物”系平面交叉關系,因此不能按照“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處理,從而構成了法律漏洞。
在此情況下,原則上應該適用《婚姻法解釋(二)》第10條之規定。其理由是:(1)“結婚時間”長和不長忽視了“金錢式的彩禮”在財產形態上的轉化。在古代,女方獲得的聘財具有“每一代人日用器具更新費的特質”,是用于購買“室內的日用器具、鋪蓋、盛裝使用的衣服等等”的,在“并不富裕的普通家庭”中,“大部分一生只有一次機會來籌辦”。[5]今天依然如故。“彩禮所包含的項目:家用電器屬于耐用消費品,可以長期消費;日常生活用品和大批量購進的服裝也是為留待日后慢慢使用,亦屬長期消費,等等。從本質上說,彩禮本身,即是為將來消費所進行的‘儲蓄’”。[6]一般而言,當事人應該只有臨近“成婚”,才會以“金錢式的彩禮”購置。換言之,只有在“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情況下,“金錢式的彩禮”才沒有轉化為雙方共同生活用的或女方專用的財物,才可能返還。而一旦共同生活,無論長短,其大部甚或全部就已經轉化為財物;(2)以“給付人”而不是“對方”生活困難為條件更為科學。因為“彩禮”一般而言,是從“男子”的“家產”[7]——應該主要是男方父母的共同財產——支付的,因此不能以“對方”作為判斷標準。不過,在返還時,法院確實應該考慮“金錢式的彩禮”是否消耗、消耗的比例等具體情況。
4.“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條款的廢除
盡管1979年《民事意見》、1980年《婚姻法》、現行《婚姻法》不再像1951年《聘金或聘禮處理的指示》那樣,將“女方獲得的彩禮”定性為“變相的買賣婚姻性質的”聘金或聘禮而予以沒收,但是“變相的買賣婚姻”仍然為1980年《婚姻法》和現行《婚姻法》以“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這種形式保留下來。它應該得到廢除。其理由是:(1)它違反了農村的生活實際。1950年《婚姻法起草報告》明確指出,“人民自己”將“結婚”“重視為終身大事”。因此,在結婚之際,購置新生活用品乃是順理成章的。新生活用品固然可以由夫妻雙方購置、日后購置,然而“在農村,未來收入不確定的風險太大,女性經濟上對男性的依附性,決定了她出于日后生活保障這一動因而向男方索要彩禮的行為。”[8]而且,“金錢式的彩禮”購置的財物多“留置”在男家,因此他們一般不會遭受不可預測的損害。(2)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護。由于支付巨額彩禮的人多為男方父母,因此他們如何安度晚年的確令人擔憂。不過,依據《合同法》第192條第1款第2項“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之規定,老年人可以撤銷贈與。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11條第3款規定,“贍養人的配偶應當協助贍養人履行贍養義務”,該規定可以適用于兒媳和公婆之間;(3)由于“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與“禁止買賣婚姻”一樣,屬強制性法律規范,因此它也同樣為當事人“帶來隱患”。 [page]
(四)“彩禮”與“贈與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間的關系
1.“贈與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解釋
按照文義解釋和歷史解釋的方法,“贈與性質的”聘金或聘禮可以作出以下解釋:(1)依據1979年《民事意見》之有關規定,獲得“贈與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主體既包括雙方當事人,也包括“對方父母”。
(2)受贈人獲得贈與物是建立在贈與人“主動”贈送的基礎之上的。
(3)依據1951年《聘金或聘禮處理的指示》第4條之規定,它既不是附條件,也不是附義務的,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仍然應該返還的。而且,該條件不同于《合同法》,第192條第1款規定的可以撤銷贈與的條件。
2.“彩禮”與“贈與性質的”聘金或聘禮之間的關系
由于“給付彩禮方在主觀上是非自愿的”,而不可能是“主動的”,因此,兩者之間沒有任何關系。
3.“贈與性質的”聘金或聘禮制度的法律漏洞
“贈與性質的”聘金或聘禮制度的法律漏洞是:(1)在法律效力方面,附條件的贈與應該排除而未排除。依據《民法通則》第62條的規定,民事行為可以附條件。因此,贈與合同可以附停止條件或解除條件。而1951年《聘金或聘禮處理的指示》第4條規定,“贈與性質的”聘金或聘禮“原則上均不許請求返還”。很顯然,附停止條件或解除條件的贈與應該排除而沒有排除;(2)它與《合同法》之有關規定相互矛盾。依據《合同法》第185條的規定,無附款的贈與合同一經履行,贈與人便“無償”取得了“財產”;依據《合同法》第192條第1款第1項、第2項的規定,在受贈人“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的近親屬”和“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的情況下,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依據《合同法》第194條之規定,撤銷贈與之后,贈與人可以請求返還。而1951年《聘金或聘禮處理的指示》第4條規定的返還要件是“給付之一方在經濟上特別困難而收受之一方又有返還能力”者,返還的范圍是“在確保婚姻自由的前提下……判令收受之一方返還全部或一部”。
(五)聘金或聘禮制度的應然狀態
如果未來的立法放棄將“聘娶婚”定性為公開的或變相的“買賣婚姻”之立場,放棄將聘金或聘禮定性為公開的或變相的“買賣婚姻的代價”之立場,由于獲得聘禮的一方屬無償獲得,因此就應該依據《合同法》第185條之規定,將聘金或聘禮定性為“贈與物”。依據《民法通則》第62條“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附條件……”之規定,聘金或聘禮可以分為附條件的聘金或聘禮和不附條件的聘金或聘禮兩類。對于前者,在停止條件或解除成就時,獲得者就應該返還;對于后者,按照《合同法》撤銷贈與的有關規定返還。
三、返還彩禮的請求權基礎
(一)比較法的考察
所謂請求權基礎,是指“支持一方當事人得向他方當事人請求特定作為或不作為之法律規范。”[9],就返還彩禮的請求權基礎,羅馬、德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美國的立法可以分為“給付目的不達”之不當得利和“給付目的嗣后不存在之不當得利”兩類立法模式。前者建立在“彩禮”之法律性質被確定為附停止條件的贈與之上;后者建立在彩禮之法律性質被確定為附解除條件的贈與之上。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將給付彩禮定性為附條件的贈與有“推定”和“擬制”兩種途徑。“所謂條件,系使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系于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事實成否之附從的意思。條件本身亦為意思表示,而贈與又為契約,當事人必須合意,附條件之贈與始能成立。然而,交付聘金或禮物時,當事人明示約定附以解除條件者,其例絕少,因此此項附解除條件之意思表示,僅能依社會一般觀念,認為系屬默示意思表示。此種認定原屬擬制,未必盡符當事人原意。”[10]
1.“給付目的不達”之不當得利
羅馬法認為,彩禮屬于“預期結婚而贈與”。如果“其后目的不能實現……為給付之一方得向受領給付之一方請求返還所受之利益”。[11]依據德國民法典第1301條之規定,婚約不履行時,關于婚約當事人間之“贈與”或“以為婚約之信證所與之物”,任何一方“得依不當得利返還之規定”,向他方請求返還。[12]此種不當得利在性質上也應該是給付目的不達之不當得利。1928年5月21日,日本京都地方法院認為,聘禮屬于“以婚姻之成立為停止條件之贈與”。[13]而且,日本部分地方法院將“結婚”這一條件做了目的性擴張。首先,對于已經辦理了結婚申報但持續期間短暫的婚姻,仍然要求受領方返還。1952年8月13日,“鳥取”地方法院在“自結婚時起一方就沒有誠實地維持婚姻關系的意思,并應該認識到婚姻關系必定因此而終止”的案件中,認為“依據信義原則,參照婚姻關系不成立加以處理,受領方應負擔返還之義務”。1962年8月8日,“柳川”地方法院在“婚姻即使在形式上已經成立,但由于夫妻生活持續期間短暫,事實上的夫妻協同體沒有成立的”案件中,“參照婚約不履行加以處理,受領方應負擔返還義務。”[14]其次,對于短暫的事實婚姻,仍然要求受領人返還。1928年5月21日,日本京都法院率先做出判決指出,“事實上的夫妻共同生活既然已經開始,交付訂婚禮品的目的就已經完全實現。”1928年11月24日,最高法院支持了京都法院的立場,即原則上只要事實婚姻成立,給付方就不得請求返還。[15]1935年10月15日,最高法院修改了自己的立場。它指出,“事實婚姻雖然已經成立,但由于持續期間比較短暫,且雙方感情不和,訂婚禮品授受之增進雙方情誼之目的沒有實現,”因此,受領方應該像婚約解除時一樣加以返還。[16]“神戶”法院在1957年4月23日于事實婚姻只持續一個多月,“弘前”法院在1957年8月13日于事實婚姻只持續一個月的案件中,均支持了返還的請求。在美國,“在聘禮(engagementgift)系期待結婚而給予受贈人的情況下,大多數法院認為,盡管在形式上看是絕對的,但實質上是附條件的。婚約一旦違反,贈與人有資格請求返還。”[17]所附的條件屬于停止條件。即“結婚是獲得戒指的所有權的前提要件。只有交換結婚誓言,受贈人才能獲得它的所有權。”[18]在條件的形式問題上,美國各州分為兩類:其一是可以是“默示的條件”(impliedcondition)。“大多數法院承認以后結婚這一條件在性質上可以是默示的,”[19]“只要有優勢證據證明禮物是基于期待結婚而給予的,就足以證明禮物是附條件的。”而且,法院還認為,“要求戒指的贈與人將‘如不結婚即不贈與’的愿望表達出來是過分苛刻的,也是不必要的。”[20]其二是必須是“明示的條件”(expresscondition)。“有少數法院拒絕將聘禮定性為以結婚為默示條件的聘禮。它們要求請求返還聘禮的贈與人證明聘禮曾經明確地附加結婚這一條件。”當然,依據判例,“明示的條件可以通過雙方當事人的行為來表達,而不是非通過明確的協議表達不可。”[21] [page]
2.“給付目的嗣后不存在”之不當得利

日本“神戶”、“大阪”法院認為,訂婚禮品屬于或類似于以婚姻不成立為解除條件的贈與。[22]我國臺灣地區1958年臺上字第917號判例指出,“凡訂立婚約而授受聘金禮物,固為一種贈與。惟此種贈與并非單純以無償移轉財物為目的,實系預想他日婚約之履行,而以婚約解除或違反為解除條件之贈與,嗣后婚約經解除或違反時,當然失其效力;受贈人依第179條,自應將其所受利益返還于贈與人。”[23]我國臺灣地區1958年臺上字第1469號判例指出,“婚約之聘金系附有負擔之贈與,上訴人既不愿履行婚約,則依第412條第1項、419條第1項,被上訴人自得撤銷贈與,請求返還贈與物,縱解除婚約之過失系在被上訴人,亦僅生賠償之問題,不能為拒絕之論據。”就附條件的贈與和附負擔的贈與之間的關系,1966年3月28日,民刑庭總會決議認為,“為訂立婚約所付之聘金,究系附有負擔之贈與,抑解附有解除條件之贈與,本院1958年臺上字第1469號與同年臺上字第917號判例見解不同,應否刪除,議決:兩判例并存”。[24]由于“婚約則依民法第975條規定不得請求強迫履行,故惟有撤銷贈與之一途”。[25]因此,附負擔之贈與的返還最終同樣應該依據“給付目的嗣后不存在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而且,我國臺灣地區對于“結婚”這一條件或負擔未做目的性擴張。1954年臺上字第158號判例認為,“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惡意遺棄,經第一審判決離婚確定在案,其所收之聘金、飾物及支付之酒水費200元,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被上訴人應負返還之義務。按因離婚而消滅之婚姻關系,并無溯及既往之效力,在離婚前之婚姻關系既已成立,自不發生不當得利問題,上訴人所為不當得利之主張,殊難謂為有據。”1961年臺上字第351號判例再次認為,“聘金乃一種贈與,除有解除條件之贈與于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贈與人得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受贈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不得以此為因判決離婚所受之損害,而依同法第1056條第1項請求賠償。”[26]
(二)我國的請求權基礎
1.彩禮的性質
最高法院認為,彩禮在性質上是屬于“附解除條件的贈與”。即“在廣大的農村地區,老百姓操勞多年,傾其所有給付彩禮,是迫于地方習慣做法,為了最終締結婚姻關系,不得已而為之的。這種目的性、現實性、無奈性,都不容否認和忽視。作為給付彩禮的代價中,本身就蘊涵著以對方答應結婚為前提。如果沒有結成婚,其目的落空,此時彩禮如仍歸對方所有,與其當初給付時的本意明顯背離。”[27]而且,依據“作為給付彩禮的代價中,本身就蘊涵著以對方答應結婚為前提”這一內容,“條件”在解釋上應該包括“默示的條件”。而且,“結婚”這一解除條件也做了目的性擴張。依據《婚姻法解釋(二)》第10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如果“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離婚時也應該返還。立法理由是:“如果一直沒有共同生活的話,也就沒有夫妻之間相互協助、共同生活的經歷。所以,對雙方當事人而言,法律意義上的婚姻關系雖已成立,但實質意義上真正的共同生活還遠沒有開始。由于各地方的習慣不一樣,農村及一些地方,往往更注重的是舉辦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婚禮,更注重的是兩個人真正走到一個家庭中,開始共同生活。而且許多時候,舉辦這些儀式與登記結婚要隔很長時間,如果雙方尚未共同生活的,也沒有過多把雙方共同聯系在一起的紐帶。”[28]依據《婚姻法解釋(二)》第10條第1款第3項的規定,如果“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離婚時也應該返還。立法理由是:“給付彩禮、辦理結婚登記并共同生活在一起后,由于雙方性格不合等原因,加之生活困難等因素,結婚時間不長,雙方就離婚了的,實踐中也大有人在。而且由于給付彩禮,全家已經債臺高筑,生活陷于困境,此時這些人也大多要求返還彩禮,處理不好的話,很容易激化矛盾。”[29]
2.請求權基礎
由于彩禮的法律性質被確定為“附解除條件的贈與”,因此“當事人一方依照附解除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向另一方為給付后,因為附解除條件成就,另一方因受領給付所獲得之利益,失去法律上的依據,構成不當得利,應予返還。”[30]依據比較法的解釋,此種不當得利當屬“給付目的嗣后不存在”之不當得利。[31]不過,“由于我國民法不承認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因此,對于彩禮中的“貴重物品”來說,“不當得利”屬獲得占有的不當得利,贈與人可以請求返還所有權。[32]對于彩禮中的金錢來說,“貨幣的所有權因為交付而發生當然移轉(貨幣的持有人視為貨幣之所有人),此為公理性的原則,給付貨幣的一方沒有請求所有權返還的基礎。”[33]不當得利屬獲得所有權的不當得利,贈與人不能請求返還所有權。[34]
四、返還彩禮與過錯
(一)比較法的考察
就返還財禮與過錯的關系,即無正當理由解除婚約的一方或由于自己的過錯致使對方解除婚約者如系贈與人,能否向無過錯的另一方請求返還,羅馬、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美國的立法可以分為返還彩禮不受過錯的影響和返還彩禮受過錯的影響兩類立法模式。
1.返還彩禮不受過錯的影響
羅馬“帝政”以前,婚約解除時,“對訂婚時收受他方的禮物,應行歸還”。[35]1967年7月31日,日本大阪法院判決認為,“只要將訂婚禮品認定為有目的的贈與,在目的不達到的情況下,就不應該考慮責任的有無,而應認可返還的請求。”[36]依據我國臺灣地區1958年臺上字第1469號判例,返還彩禮也不受過錯的影響。當然,受害人可以依據民法第978、第979條的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在美國,盡管大多數法院在解決聘禮糾紛時繼續采用過錯主義,但是“有少數法院追隨無過錯離婚主義,在解決訂婚戒指的糾紛時,也采用無過錯主義。”[37]1971年,紐約州在格登訴格登(Gadenv.Gaden)[38]案中率先確立了無過錯主義。[39]此后,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堪薩斯州最高法院也采用了無過錯主義,[40]賓西法尼亞州也采用了無過錯主義。[41]美國少數法院采用無過錯主義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男女平等。“過錯主義是建立在男女不平等基礎上的、過時的。它應該讓位于無過錯離婚法體現出來的中立主義”;其二是“它可以給負擔已經過重的法院提供明確的原則,防止當事人陷入激烈的婚約解除訴訟之中”。[42]
2.返還彩禮受過錯的影響
羅馬“帝政”以后,“聘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發生強制履行的效力,法律視不履行婚約有無正當理由而作不同的規定:男方無正當理由而毀約的,要喪失聘禮,同時應歸還女方的全部贈與;如女方無正當理由而毀約,則不得收回贈與,除返還男方的聘禮外,還要另付四倍于聘禮金額的罰金,以后改為與聘禮相等的數額。”“男女一方因正當理由”“而解除婚約,則由雙方互退聘禮和贈與”。[43]在婚約因給付方之過錯而終止的情況下,日本下級法院的一般立場是對有責方之返還請求持否定態度。所持的理由主要有:首先,過錯方請求構成“非禮”。“神戶”法院在1952年5月26日判決認為,訂婚禮品在性質上屬結親的標志,如果一方面給付方因自己的過錯導致婚約終止,另一方面又提出返還訂婚禮品之請求,屬于“非禮”;其次,過錯方請求“違反信義原則”。“奈良”法院在1954年4月13日、“小倉”法院在1973年2月26日、“大阪”法院在1968年1月29日判決認為,有責方的返還請求違反信義原則;再次,“過錯方應受制裁”。“大阪”法院在1966年1月1日判決認為,有責方應該受到制裁,因此駁回其訴訟請求。在高級法院中,東京高等法院在1982年4月27日率先判決認為,如果準許有責方的返還請求,則違反了信義原則。[44]在美國,“無過錯離婚法確立之前,在贈與方違反婚約(breakengagement)的情況下,大多數法院(amajorityofurisdiction)均主張或承認受贈人有權保有訂婚戒指或請求返還它的價值,”[45]“很多法院(courts)認為,在受贈方違反婚約的情況下,對未婚妻贈與價值不菲且能長期保存的禮物之贈與方可以請求返還禮物。”[46]“目前,在解決戒指的所有權糾紛時,大多數法院仍然堅持過錯主義。”[47] [page]
(二)我國采用了無過錯主義
依據《婚姻法解釋(二)》第10條第1款的規定,返還彩禮不受過錯的影響。因為“本解釋在決定彩禮是否返還時,是以當事人是否締結婚姻關系為主要判斷依據的。給付彩禮后未締結婚姻關系的,原則上收受彩禮一方應當返還彩禮。給付彩禮后如果已經結婚的,原則上彩禮不予返還,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支持當事人的返還請求。”[48]此種立法是正確的。因為彩禮屬附解除條件的贈與,不問過錯的有無,均應該返還。當然,在婚姻解除損害賠償制度(《婚姻法》第46條)的基礎上,我國應該確立婚約乃至事實婚姻解除的損害賠償制度。[49]否則,就是不公平的。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