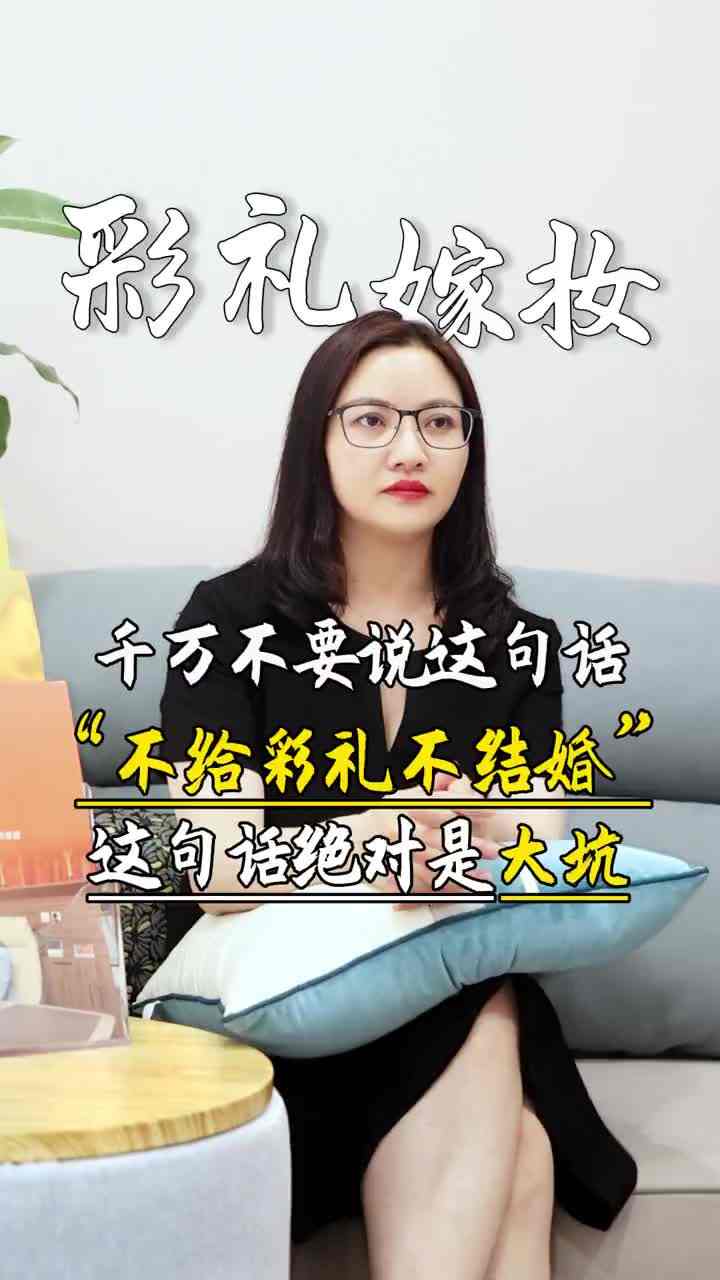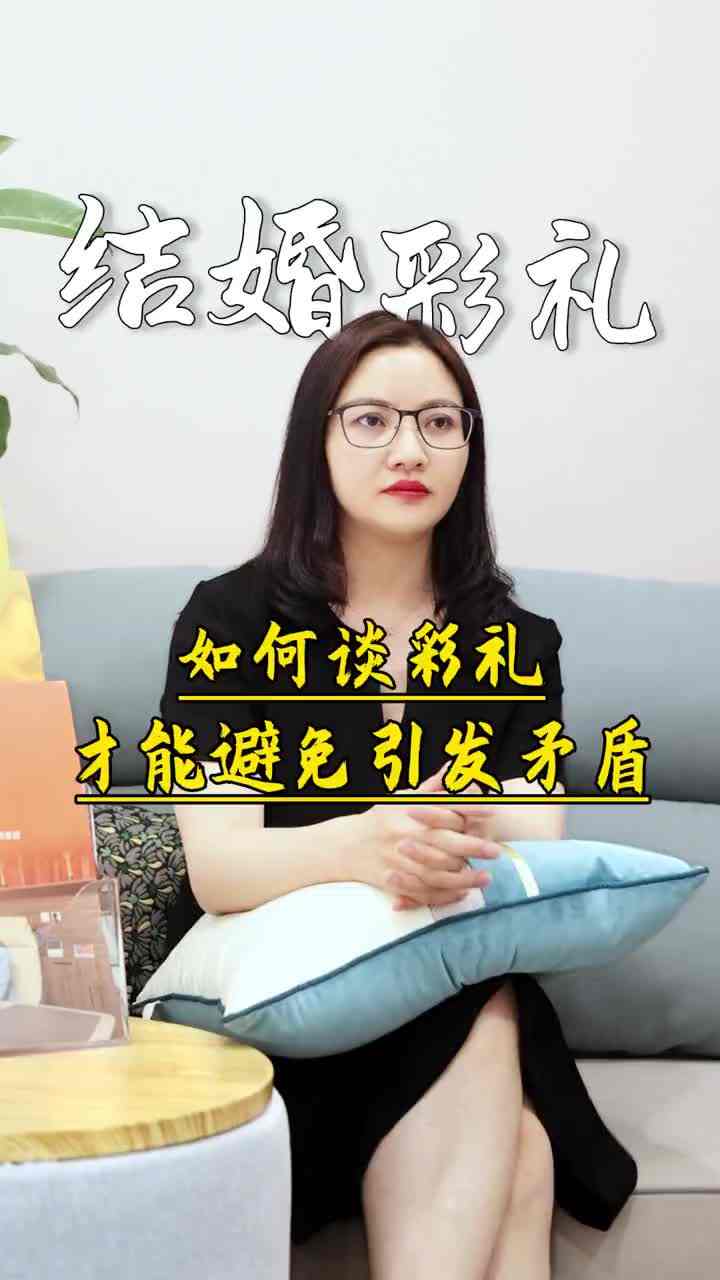本案應由誰來返還彩禮?
 龍珊律師2022.01.30196人閱讀
龍珊律師2022.01.30196人閱讀
導讀:
嗣后,原告一家對被告阿某某表示滿意,并初步同意阿某某提出要給其家人5.6萬元安家費的要求。原告經尋找未果,遂以償還借款為由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被告李某、楚某給付5.6萬元,并承擔案件訴訟費用。被告拉某某同阿某某出走后,被告李某一家尋找未果,曾于2010年12月20日向派出所報案稱被拉某某騙取彩禮5.4萬元。案情經公安漢臺分局研究后認為拉某某與李某甲登記結婚并共同生活,所使用身份信息真實有效,認定婚姻詐騙要件不足,故未予立案偵查。另派出所未接到原告袁某報警記錄。故該5.6萬元應為《婚姻法》所規定的彩禮性質,本案案由宜為婚約財產糾紛。那么本案應由誰來返還彩禮?。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嗣后,原告一家對被告阿某某表示滿意,并初步同意阿某某提出要給其家人5.6萬元安家費的要求。原告經尋找未果,遂以償還借款為由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被告李某、楚某給付5.6萬元,并承擔案件訴訟費用。被告拉某某同阿某某出走后,被告李某一家尋找未果,曾于2010年12月20日向派出所報案稱被拉某某騙取彩禮5.4萬元。案情經公安漢臺分局研究后認為拉某某與李某甲登記結婚并共同生活,所使用身份信息真實有效,認定婚姻詐騙要件不足,故未予立案偵查。另派出所未接到原告袁某報警記錄。故該5.6萬元應為《婚姻法》所規定的彩禮性質,本案案由宜為婚約財產糾紛。關于本案應由誰來返還彩禮?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婚姻家庭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案情簡介】
原告袁某訴稱,2010年11月8日,被告李某、楚某向其借款5.6萬元,并親手執筆出具借條一張,后經其多次向被告索要,二被告以各種理由拒絕償還,無奈之下只好持借條提起民間借貸之訴,請求人民法院判令二被告歸還借款5.6萬元,并承擔案件訴訟費用。
被告李某辯稱,借條是其本人所寫,但事情并非單純借貸關系。2010年底,原告妻子到被告家托被告給其兒子介紹對象,后幾經周折被告通過鄰村一人給原告兒子介紹一四川籍女子阿某某。原告一家看到該女子后都滿意,也都同意該女子要求給她5.6萬元彩禮。原告于2010年11月8日將5萬余元彩禮帶到被告家,并叫被告擔保此事。被告本不同意,但因被告當天喝了酒,又在原告妻子再三催促下糊里糊涂地按原告夫妻的要求寫了該借條,誰也沒料到這個川籍女子是騙婚的,拿了錢就跑了。被告兒子也被騙走近5萬元。被告確實沒用這筆錢,沒有理由償還原告所訴請的5.6萬元。
被告楚某辯稱,我同丈夫好心給原告兒子介紹對象,現如今自己兒子也被騙了近5萬元彩禮,自己一家也是受害人。都是騙婚的把錢拿走了,希望能將騙婚的抓到,這樣錢也能歸還原告一家。被告夫婦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給原告還5.6萬元。
經審理查明,原告袁某(男)與被告李某(男)、楚某(女)系漢臺區同鎮農民,因故相熟。2010年10月一天,原告家人與被告楚某偶遇時談及給原告兒子介紹對象事宜。被告楚某將此事告知其新過門的兒媳拉某某(四川喜德縣彝族農民)后,拉某某提出自己表妹阿某某(四川冕寧縣彝族農民)尚未婚嫁。被告李某、楚某遂告知原告家人,并安排原告一家與被告阿某某見面。嗣后,原告一家對被告阿某某表示滿意,并初步同意阿某某提出要給其家人5.6萬元安家費的要求。2010年11月8日在被告李某家中,原告因未見過阿某某家人,便提出讓被告李某書寫5.6萬元的借條來擔保此事。被告李某在清點完5.6萬元后出具借條一張。借條載明:借到袁某現金5.6萬元,伍萬陸仟元整,具借人:李某、楚某。并在借條兩處加蓋李某私人印章,借款人簽名均為李某所簽。被告楚某在場未提出異議。次日上午10時許,被告楚某、拉某某、阿某某及楚某之子李某甲一同在鎮郵政儲蓄銀行以拉某某名義將5萬元匯至四川省喜德縣其胞兄拉某某甲名下賬戶,其余6000元被告李某、楚某自行留存。被告阿某某隨后在原告家生活約一周時間左右,以同被告拉某某一起到鎮上給老家郵寄物品為由外出后下落不明。原告經尋找未果,遂以償還借款為由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被告李某、楚某給付5.6萬元,并承擔案件訴訟費用。訴訟中為查清事實,法院依職權公告通知拉某某、拉某某甲、阿某某參與訴訟。
另查明,匯入被告拉某某甲名下5萬元由拉某某甲隨后在四川省喜德縣郵政銀行ATM機分12次提現。
再查明,被告李某、楚某之子李某甲經人介紹認識被告拉某某談婚,后兩家人在四川省喜德縣城一飯店見面訂婚,并于2010年10月28日辦理了結婚登記。被告拉某某同阿某某出走后,被告李某一家尋找未果,曾于2010年12月20日向派出所報案稱被拉某某騙取彩禮5.4萬元。案情經公安漢臺分局研究后認為拉某某與李某甲登記結婚并共同生活,所使用身份信息真實有效,認定婚姻詐騙要件不足,故未予立案偵查。另派出所未接到原告袁某報警記錄。
【審判】
漢臺區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在于5.6萬元現金是否為借款以及四被告在原告5.6萬元給付過程中的行為性質及應否承擔民事責任。
關于5.6萬元現金問題。通過業已查明的事實,原告在為其子物色對象過程中,被告李某、楚某及其兒媳拉某某介紹的談婚對象阿某某提出需要5.6萬元安家費,原告為促成兒子婚事而同意給付。故該5.6萬元應為《婚姻法》所規定的彩禮性質,本案案由宜為婚約財產糾紛。原告持有李某出具的5.6萬元借條要求返還借款,僅有形式要件,無借款之實,故對其返還借款的請求依法不予支持。

關于被告行為性質及應否承擔民事責任問題。本案所涉5.6萬元作為原告商談其子婚事過程中所給付的彩禮,因被告阿某某最終并未與原告之子登記結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解釋(二)第十條之規定,其應該在收取的5萬元范圍內向原告返還。被告拉某某以阿某某親屬身份作為談婚過程的介紹人之一,且鑒于彩禮款項匯至其兄被告拉某某甲賬戶,并由拉某某甲取現這一事實,故應由被告拉某某、拉某某甲承擔連帶返還責任。被告李某、楚某作為介紹人為實現通過促成婚事獲取介紹費6000元的目的,在未對阿某某家庭真實情況有足夠了解情況下,便以自己給付兒媳拉某某父母5.4萬元后雙方登記結婚的陳述以及書寫借據的方式增進原告信任。在基于原告信任管控5.6萬元后,又草率將其中5萬元轉移由阿某某占有致使原告人財兩空,未盡到因其先行行為而負有的善意管理人注意義務,故應對原告的財產損失根據過錯程度承擔連帶返還責任。其通過介紹對象借機獲利亦屬不當,所占有6000元應予返還。另根據婚姻自由的法律精神,婚姻應建立在感情基礎上。而原告袁某為促成其子婚事,在對阿某某個人及家庭情況未充分了解下,便急于以給付大額彩禮為代價敲定結婚事宜,疏于注意,應對自身彩禮損失承擔相應風險。遂判決如下:一、被告阿某某、拉某某、拉某某甲返還原告袁某彩禮5萬元。二、被告李某、楚某對上述5萬元按30%比例即在1.5萬元范圍內承擔連帶返還責任(被告李某、楚某給付后有權向被告阿某某、拉某某、拉某某甲追償)。三、被告李某、楚某返還占有原告的6000元。以上金錢給付項目限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付清。四、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
【分析】
一、本案是否為民間借貸糾紛?
民間借貸糾紛是公民之間、公民與非金融機構企業之間的借款行為引發的糾紛。根據我國《合同法》第210條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之規定,公民之間的民間借貸是實踐性合同,不僅需要雙方達成借貸合意,還要求有貸款人實際提供借款的行為。本案原告袁某持借條起訴被告李某、楚某夫婦歸還借款5.6萬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法[2011]42號)中的相關規定:民事案件案由應當根據當事人主張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確定。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結案時應當根據法庭查明的當事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的性質相應變更案件的案由。故本案案由在立案時應定為民間借貸糾紛。通過庭審查明,經原告家人囑托,二被告與其兒媳被告拉某某為原告之子介紹婚戀對象被告阿某某,雙方見面后,原告一家人同意被告阿某某要求給其家人5.6萬元安家費而將5.6萬元給付給婚介人之一被告李某,被告李某應原告要求出具借條并署名李某、楚某,因原告與被告李某、楚某并未達成借貸合意、產生借貸行為,故原告訴請被告李某、楚某返還借款5.6萬元的請求依法不予支持。雖然我國《婚姻法》第3條明文規定禁止包辦、買賣婚姻、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但受我國傳統封建社會舊禮制中聘娶婚制度的影響,民間談婚論嫁習俗中普遍存在男方向女方給付一定數額的財物即彩禮,作為締結婚約、登記結婚的前提條件,故該5.6萬元屬于我國《婚姻法》司法解釋(二)[下簡稱司解(二)]第10條所規定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我國《婚姻法》未規定婚約,婚約當事人可自行解除婚約,無須征得對方同意,對方對解除婚約有異議而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根據該第10條規定,如存在(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二)雙方辦理結婚登記但確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情形之一的,給付彩禮方請求返還彩禮的,依法應當予以支持。本案原告起訴婚介人李某、楚某夫婦名為要求返還借款5.6萬元,實際則是要求返還彩禮5.6萬元,故本案案由應當根據庭審查明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變更為婚約財產糾紛。因阿某某系婚約當事人,拉某某系婚介人之一,彩禮5萬元是以拉某某名義匯至其兄拉某某甲銀行賬戶名下,且由其兄實際提取,故為查明案件事實應依法追加三人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
二、各被告的行為性質及法律責任
被告阿某某經被告李某、楚某、拉某某介紹與原告之子談婚,其在雙方見面時提出給其家人5.6萬元安家費,原告將5.6萬元現金交給婚介人之一被告李某,次日上午,其與被告拉某某及楚氏母子一同在銀行以拉某某名義將5萬元匯至拉某某之兄拉某某甲賬戶上,因原告與被告李某、楚某均信任被告拉某某稱其與被告阿某某系表姐妹關系,故該匯款行為證實被告阿某某已收取彩禮5萬元。但其僅在原告家生活約一周時間后即與被告拉某某借故外出下落不明,顯然是單方解除婚約行為,因其并未與原告之子辦理結婚登記,故依據司解(二)第10條之第1項規定,其負有返還彩禮5萬元之義務。因被告拉某某并非婚約當事人,其將原告袁某給付給被告阿某某的彩禮5萬元以其名義匯至其兄拉某某甲名下,并由其兄實際提取,事后又與被告阿某某一同借故外出下落不明,這一系列不當行為沒有合法根據,其取得的不當利益給原告袁某帶來經濟損失,依據《民法通則》第92條之規定,已構成不當得利,依法應當由被告拉某某、阿某某、拉某某甲連帶將該不當利益5萬元返還給受損失人原告袁某。
被告李某、楚某夫婦受原告家人囑托,如其所言好心為原告之子介紹對象,其自行從彩禮中留存6000元的行為是否恰當、合法呢?其在聽信新過門兒媳被告拉某某之言,將被告阿某某介紹給原告之子相識談婚,不料之后二被告一同借故外出下落不明,最終致兩家人財兩空的事件中是否有法律責任呢?俗話說:天上無云不下雨,地上無媒不成姻。雖然民間有謝媒禮風俗,況且答謝婚姻介紹人也是人之常情,但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之規定,說媒行為也要符合日常情理標準,否則應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本案原告袁某與被告李某、楚某并未約定謝媒紅包數額,且二被告未經原告袁某同意即自行從彩禮中留存6000元,違背了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原則,顯然不當。二被告之子李某甲與被告拉某某經人介紹相識談婚中,兩家相隔跨省千里且素未謀面,因民族、成長環境不同必然會產生生活習慣、性格差異,但其與被告拉某某兩家人僅在四川省喜德縣一飯店見面、給付拉某某娘家彩禮5.4萬元后便登記結婚,可以說這本是一樁草率婚姻,二被告及其子李某甲本身對被告拉某某及其家庭的了解都不夠充分,但二被告卻將給原告之子介紹婚戀對象的信息告知被告拉某某,僅聽憑拉某某之言,在未對被告阿某某及其家庭充分了解的情況下便將其介紹給原告之子談婚,并以自家娶兒媳婦拉某某給付其娘家彩禮5.4萬元及應原告袁某要求,在其并未向原告借款5.6萬元的情況下,違背事實、不計后果地書寫借條,被告楚某在場亦未提出異議或阻攔的行為來增進原告袁某的信任,進而使原告在內心確信下將彩禮5.6萬元交由被告李某掌管。其于次日上午又草率將其中5萬元轉移給被告阿某某占有,最終導致兩家均人財兩空,其荒唐行為明顯違背了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民法通則》第106條第1款規定,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二被告應當返還原告袁某6000元,否則即構成不當得利;并且因其荒唐說媒言行,未妥善盡到最起碼的善良注意義務的先行行為而導致原告袁某彩禮5萬元的損失承擔一定范圍內的連帶賠償責任。其給付后有權依法向被告拉某某、阿某某、拉某某甲追償。根據《民法通則》第131條之規定,受害人對于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應當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本案原告袁某作為成年人,應深知婚姻大事非兒戲,其家人委托二被告為其子介紹婚戀對象,在一般人看來二被告之子與被告拉某某的婚姻本就是草率行事,何況新中國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質的法律《婚姻法》頒行于1950年,自那時起男女婚姻自由、禁止包辦、買賣婚姻、禁止借婚姻關系問題索取財物的觀念便深入人心,而原告袁某卻盲目聽信二被告的荒唐言行,在其家人僅與被告阿某某一面之緣的情況下便同樣草率給付大額彩禮來敲定其子結婚事宜,并未考慮兩人是否真心相愛、性格是否相合、女方是否身體健康等因素,完全照搬舊時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婚啞嫁陋習,其應當因自身草率、大意、盲從的過錯行為而自行承擔人財兩空后果的風險,故應減輕被告李某、楚某對彩禮5萬元在一定范圍內的連帶返還責任。生效民事裁判文書判處由被告李某、楚某對5萬元按30%比例范圍內承擔連帶返還責任是適當的。至于被告拉某某在與李某甲閃婚后便借故外出下落不明,其情形符合《解釋(二)》第10條規定的雙方辦理結婚登記但確未共同生活的,李某甲或被告李某、楚某可持給付彩禮5.4萬元的相關證據起訴請求被告拉某某返還彩禮。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