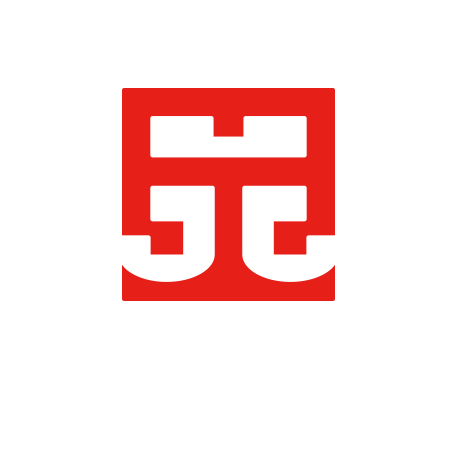合同詐騙罪犯罪數額在量刑中的認定
 劉曉紅律師2021.12.24798人閱讀
劉曉紅律師2021.12.24798人閱讀
導讀:
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數額是指與合同詐騙罪的詐騙行為相關聯的、對合同詐騙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刑法意義的以一定標準計算的財產的數目,也就是貨幣或具有一定經濟價值的物品的數目,包括定罪數額與量刑數額。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合同詐騙罪會呈現不同的形態,而不同的犯罪形態中存在著不同的犯罪數額。③筆者試圖從合同詐騙罪的既遂、未遂、連續犯、共犯等犯罪形態的基礎上,對合同詐騙罪犯罪數額在量刑中的認定作一簡略探討。對合同詐騙罪進行量刑的依據應當表現為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所指向的數額,而不是實際的犯罪數額。那么合同詐騙罪犯罪數額在量刑中的認定。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數額是指與合同詐騙罪的詐騙行為相關聯的、對合同詐騙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刑法意義的以一定標準計算的財產的數目,也就是貨幣或具有一定經濟價值的物品的數目,包括定罪數額與量刑數額。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合同詐騙罪會呈現不同的形態,而不同的犯罪形態中存在著不同的犯罪數額。③筆者試圖從合同詐騙罪的既遂、未遂、連續犯、共犯等犯罪形態的基礎上,對合同詐騙罪犯罪數額在量刑中的認定作一簡略探討。對合同詐騙罪進行量刑的依據應當表現為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所指向的數額,而不是實際的犯罪數額。關于合同詐騙罪犯罪數額在量刑中的認定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數額是指與合同詐騙罪的詐騙行為相關聯的、對合同詐騙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刑法意義的以一定標準計算的財產的數目,也就是貨幣或具有一定經濟價值的物品的數目,包括定罪數額與量刑數額。合同詐騙罪的定罪數額是指合同詐騙罪普通構成數額,而量刑數額是指影響合同詐騙行為并對行為的刑罰裁量有影響的犯罪數額,大體可以合同標的額、犯罪所得數額與犯罪造成的損失數額三種類型。合同標的額,是指合同詐騙行為所指向的合同標的總額,它客觀地反映了行為人意圖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多少以及犯罪行為的規摸、社會危害性的程度和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大小。犯罪所得數額,是指行為人通過詐騙行為實際得到的財物數額,其實質是表現行為人所實現的財產利益或經濟利益。犯罪造成的損失數額,是指對方當事人因為行為人的合同詐騙行為而減少或喪失的財產數額。它包括直接損失數額和間接損失數額。②這三類犯罪數額都與合同詐騙行為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對合同詐騙罪的定罪數額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在實踐中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問題,但在對合同詐騙罪進行刑罰裁量時究竟應該以哪一種數額作為依據呢?
犯罪數額的認定不能脫離具體犯罪的具體形態,只有在具體犯罪形態的基礎上,才能科學認定具有刑法意義上的犯罪數額,并進而作出正確的刑罰裁量。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合同詐騙罪會呈現不同的形態,而不同的犯罪形態中存在著不同的犯罪數額。③筆者試圖從合同詐騙罪的既遂、未遂、連續犯、共犯等犯罪形態的基礎上,對合同詐騙罪犯罪數額在量刑中的認定作一簡略探討。
一、在合同詐騙罪的既遂形態下,宜以受害方的直接損失數額作為量刑依據
這是因為,合同詐騙罪造成的直接損失數額,在受騙方交付給行為人時,體現了合同詐騙行為的非法占有性,以其作為此種情形下的合同詐騙罪的量刑依據,可以全面體現行為人對被害人財產的侵害程度,準確反映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保證正確適用刑罰,實現保護被害者合法利益的目的;在交付過程中,由于受害人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損失,均是由行為人的欺騙行為造成的,完全也應當歸責于行為人。如果以合同標的額作為犯罪數額,在合同標的額并未全部損失掉,被害人因受騙只損失了部分財物的情況下,若使犯罪分子對全部合同標的額承擔刑事責任,則會造成輕罪重罰的后果;如果以犯罪造成的損失數額作為犯罪數額,在受騙人實際交出財物后、犯罪分子實際騙到財物前財物因被害人以外的原因而減少的場合,這部分損失數額就會因無人承擔刑事責任而使犯罪分子得不到應有懲罰。同時應當注意的是,受害人的間接損失數額只是在正常情形下其可能會獲得的利益,并不必然獲得,不能體現非法占有性,因此不應歸責于行為人。
二、在合同詐騙罪的預備、中止和未遂形態下,宜以合同標的額作為作為量刑依據
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基本原則,未完成形態的犯罪數額應當表現為犯罪行為所指向,行為人主觀上所追求的數額,并非犯罪的實際數額。在合同詐騙罪的預備、中止和未遂形態下,行為人沒有取得任何財物,被害人也沒有交付任何財物,不會有任何經濟損失。所以,被害人損失額和行為人實際所得額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合同的標的額。對合同詐騙罪進行量刑的依據應當表現為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所指向的數額,而不是實際的犯罪數額。此時,合同標的額最能反映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所指向的數額,因此,宜把它作為合同詐騙罪未完成形態的量刑依據。但是,同時我們也應當考慮到,合同標的額有時并非是行為人所希望詐騙的對象(比如行為人只想詐騙合同的定金、預付款等),有時對該合同標的的詐騙事實上也不可能實現既遂狀態,故在司法實踐中,應當以合同標的額為量刑根據,依照刑法總則規定的關于犯罪預備、中止和未遂的處罰原則,對行為人予以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三、在合同詐騙犯罪呈連環狀態時,宜以受害各方的直接損失數額之和作為量刑根據
實踐中存在著“拆東墻補西墻”的連環合同詐騙行為,即行為人將后一次詐騙的財物償還上一次詐騙的財物,行為人始終占有他人一部分財產。連環詐騙中,行為人主觀上對是否歸還對方財物是不確定的,往往見機行事:如果對方緊盯不放,可再去騙另一家的財物來沖抵;如果對方催得不緊,就拖下去,以至不了了之。但是,在決意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確定之前,尚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詐騙犯罪的故意。在客觀方面,連環詐騙整個過程中的后一次詐騙是為了償還前一次詐騙欠下的債務,除最后一次受騙者外,其余受害人的財產損失有可能得到了全部或部分補償,詐騙人對財物的占有處于不穩定的暫時狀態,受騙人的財產損失也處于兩可的不確定狀態。這種形式的合同詐騙犯罪,行為人雖然在形式上實施數次詐騙行為,而且每次行為都可能構成了犯罪,但它事實上是一個整體的犯罪過程,在先的詐騙行為都是為后續的詐騙行為作鋪墊,行為人在實質上僅實施了一個合同詐騙行為。這種形式下的合同詐騙犯罪,從主觀上看,行為人并非意圖將全部詐騙所得據為己有,而是只想占有其中的一部分;從客觀上看,受騙人雖然財物被騙,但同時也有數個償還以前詐騙所得的行為;從行為結果來看,受騙人財物被騙,失去的并非是全部被騙財物,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對這種類型的合同詐騙犯罪,不宜以合同標的額作為量刑依據,同時,由于在數次合同詐騙行為的實施過程中給各個被害人造成的直接損失可能大于行為人的犯罪所得數額,故也不應以犯罪所得數額作為量刑依據。所以,對呈連環狀態的合同詐騙犯罪犯罪,其量刑依據應以受害各方的直接損失數額之和為準。受害各方的直接損失數額之和的計算方法,可以由行為人最后一次行騙給被害人造成的直接損失加上前幾次詐騙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直接損失而得到。
四、在合同詐騙罪呈共同犯罪的狀態下,量刑應依據各共同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同時兼顧各行為人的參與數額或分贓數額
這是由共同犯罪的本質和處罰原則所決定的。由于各個共同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故對影響其定罪量刑的犯罪數額的認定也應有所區分。首先,依據刑法總則的規定,合同詐騙犯罪的主犯應對其參與的或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的數額(在完成形態下即受害方的直接損失數額,在未完成形態下即合同標的額)承擔刑事責任,這也就是說,由于主犯的行為起決定作用,應對其參與的或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的數額承擔刑事責任。其次,對于在合同詐騙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從犯(實行犯) ,應以本人參與合同詐騙犯罪的數額為準承擔刑事責任;對于在合同詐騙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的從犯(幫助犯) ,應以其所幫助的實行犯在合同詐騙犯罪所參與的總額為準承擔刑事責任,再比照主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是由從犯自身特征所決定的。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刑法中的從犯有兩種。其一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即次要的實行犯。這一部分從犯,其特征為“參與”,所起作用不大。因此在合同詐騙犯罪中,能夠體現其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只能是其“參與額”,其不能對未參與的數額負責。否則就有可能與罪責自負原則相違背。其二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即幫助犯。其行為大多表現為共同犯罪的實施創造有利條件,輔助實施犯罪。這一部分從犯的特征主要為“輔助”,他們往往不直接參與犯罪的實施。換言之,在合同詐騙犯罪中,他們與犯罪數額之間沒有直接聯系。但是,鑒于合同詐騙犯罪的實行犯是在其幫助下完成犯罪的,故其應當對其所幫助的實行犯參與的犯罪總額承擔刑事責任。④當然,對這兩類從犯的處罰,應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從輕、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第三,脅從犯由于系被迫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較小,故宜以分贓數額作為承擔刑事責任的基礎,并且按照刑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根據其犯罪情節減輕或免除處罰。第四,在共同犯罪中,教唆犯的作用主要是由被教唆人的作用決定的,可能起主要作用,也可能起次要或輔助作用。如果被教唆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則教唆犯應相當于主犯承擔刑事責任,即應以犯罪總額(在完成形態下即受害方的直接損失數額,在未完成形態下即合同標的額)作為確定刑事責任的標準;如果被教唆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輔助作用,則教唆犯應相當于從犯承擔刑事責任,即應以被教唆人參與合同詐騙犯罪數額或被教唆人所幫助的實行犯參與的犯罪總額作為量刑依據。
五、同時有合同詐騙和其他詐騙行為情況下的量刑數額認定
在有的情況下,行為人連續實施的詐騙行為中,各種詐騙行為的性質不同,而且各種詐騙行為的數額分別計算都未達到起刑點,但是其總數額卻達到某種詐騙罪的起刑點。如行為人分別以合同手段騙、票據詐騙手段、貸款詐騙手段取了對方當事人財物,雖然其每一種詐騙行為都不構成相應性質的犯罪,但是其詐騙的總數額卻能構成其實施的任何一種詐騙犯罪如合同詐騙罪、票據詐騙罪或貸款詐騙罪。對這種情況,應當將行為人的這些行為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看,即把這些僅根據據各自特征無法認定為犯罪的行為的數額累計相加,按照普通詐騙罪定罪量刑。因為特殊詐騙罪是從普通詐騙罪分離出來的犯罪,特殊詐騙罪的犯罪構成為普通詐騙罪的犯罪構成所包容,特殊詐騙行為數額雖然不能構成特殊詐騙罪,但是其數額已經達到普通詐騙罪的起刑點,應以普通詐騙罪論處和量刑。還有一種情況是行為人實施了數種詐騙行為,其中一種或者幾種構成某一詐騙罪,而其他數種詐騙行為均未達構成犯罪的數額,如行為人分別以合同詐騙手段、票據詐騙手段、貸款詐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但只有以其中一種手段實施的行為在數額上構成了相應的犯罪,其他手段實施的行為在數額上均未構成相應犯罪。對這種情況,首先應當將沒有獨立構成犯罪的詐騙行為的數額累計起來按照普通詐騙罪定罪,然后將普通詐騙罪與已經構成的一個或者幾個特殊詐騙罪實行數罪并罰。如果已經構成的犯罪中有普通詐騙罪和其他特殊詐騙罪,那么應當將沒有獨立構成犯罪的詐騙行為的數額與普通詐騙罪的數額相加并以普通詐騙罪定罪后與其他特殊詐騙罪實行數罪并罰。

引文出處:
①趙炳春,向朝陽:《刑法若干理論問題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版,第302頁。
②田鵬輝:《合同詐騙罪的數額認定問題》,《學術交流》,2004年第1期,第44-45頁。
③張成法:《論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數額》,《法學》2005年第5期,第69頁。
④沈惠娣:《共同經濟犯罪中從犯數額的認定》,《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2年第4 期,第58-59頁。
作者:懷遠縣法院 楊光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