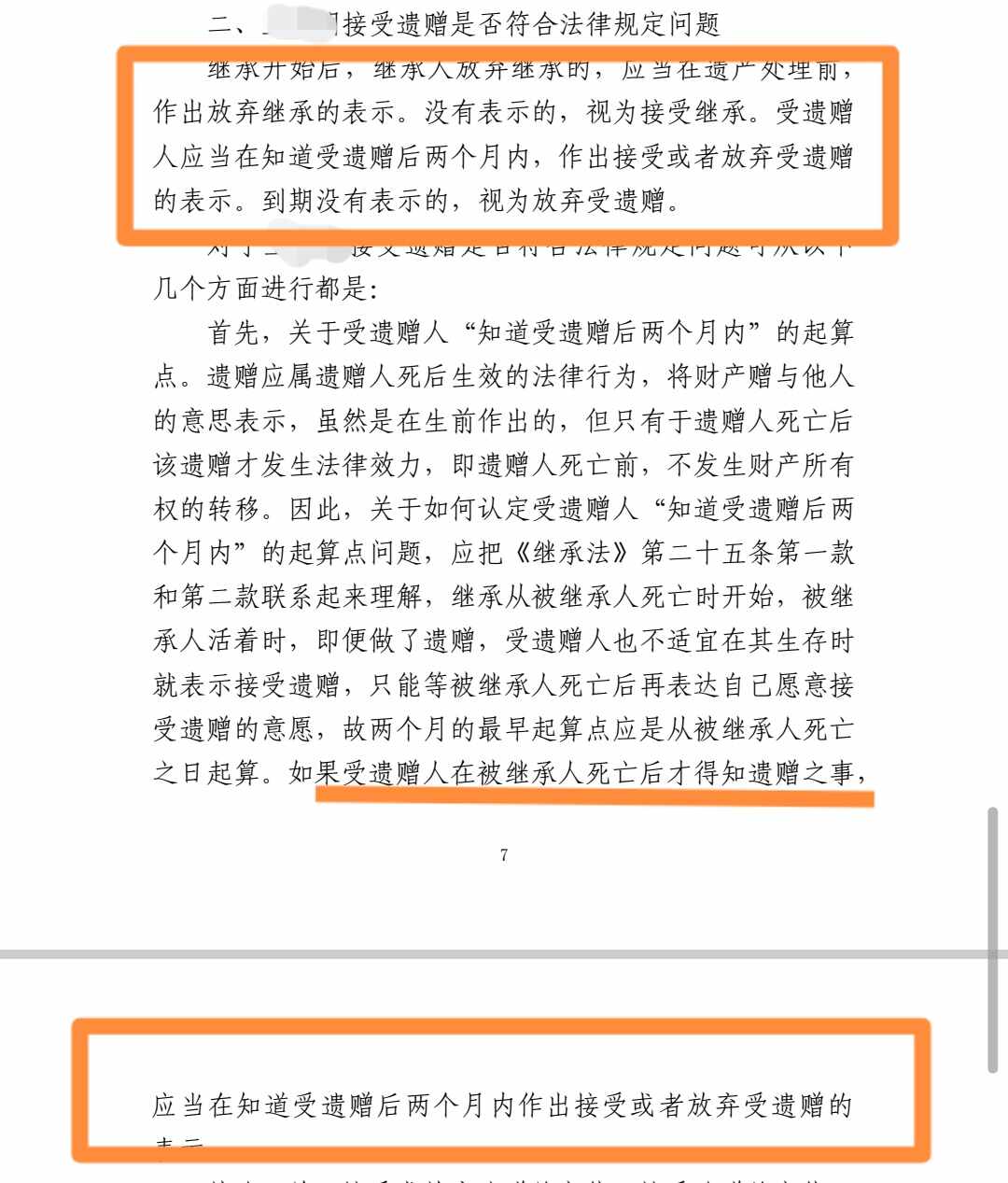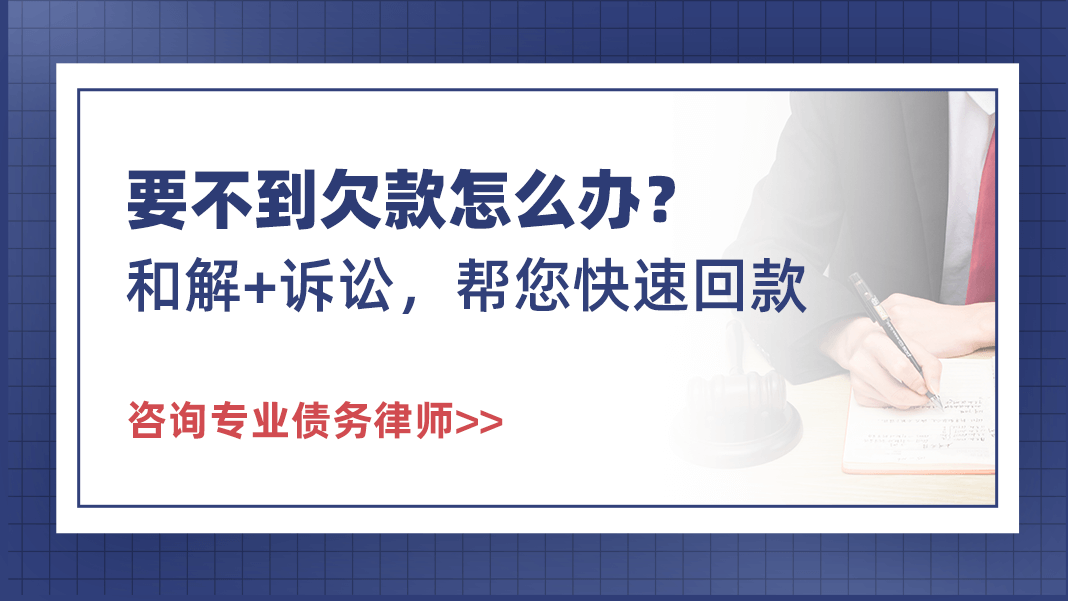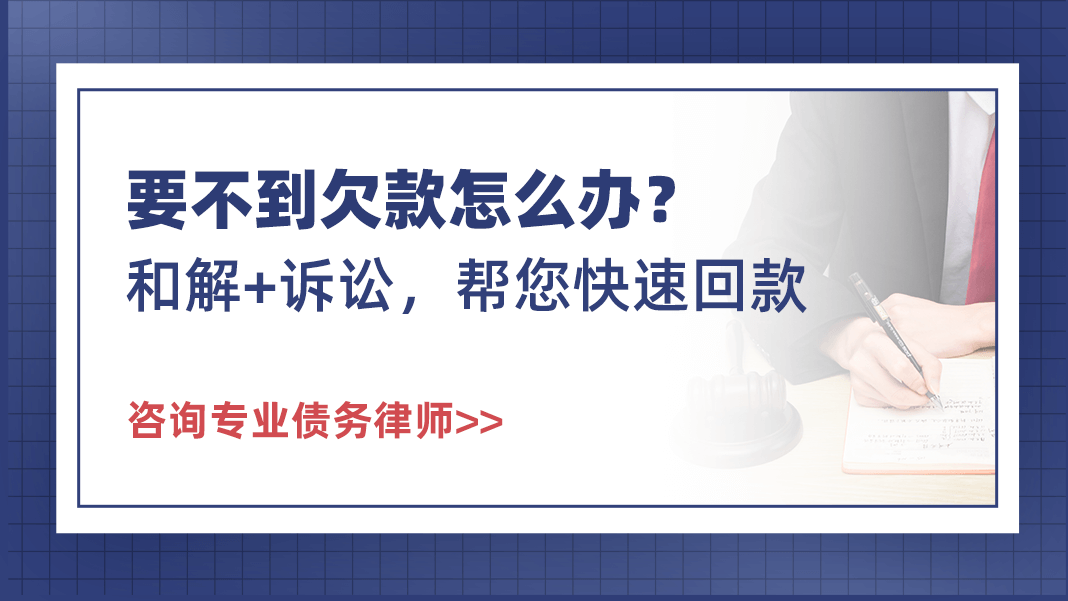不安抗辯權中止履行有幾種形式
 郭銘芝律師2021.09.17473人閱讀
郭銘芝律師2021.09.17473人閱讀
導讀:
眾所周知法律所管轄的范圍是非常廣闊的,同時法律處理的情況也是多種多樣。生活中,雙務合同履行過程中,存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先履行一方認真履行義務,而后履行一方不嚴守合同的情形。那么,對于法律規定當中,不安抗辯權中止合同履行的形式有哪幾種呢?但是什么情況下才能真正的拿起不安抗辯權這把利劍中止履行義務,拿起利劍后如何操作才能最大限度保護自身利益?
不安抗辯權中止履行有幾種形式
(一)經營狀況嚴重惡化;
(二)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
(三)喪失商業信譽;
(四)有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當事人中止履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對方提供適當擔保時,應當恢復履行。
不安抗辯權中止的效力
①先給付義務人中止履行
按民法典規定,先給付義務人有確切證據證明后給付義務人的履行能力明顯降低,有不能為對待給付的現實危險的,有權中止履行。所謂中止履行,就是暫停履行或者延期履行,履行義務仍然存在。在后給付義務人提供適當擔保時,應當恢復履行。此處所謂適當擔保,既指設定擔保的時間適當,更指設定的擔保能保障先給付義務人的債權得以實現。至于擔保的類型則在所不限,可以是保證,也可以是抵押、質押等。
②先給付義務人解除合同
按民法典規定,先給付義務人中止履行后,后給付義務人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先給付義務人可以解除合同。解除的方式,由先給付義務人通知后給付義務人,通知到達時發生合同解除效力;但后給付義務人有異議時,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與仲裁機構確認合同解除效力。
③后給付義務人的行為構成違約時,應負違約責任。
先履行方符合以上適用條件,即取得不安抗辯權。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辯權將對雙方當事人產生何種影響,這就是不安抗辯權的效力。根據后履行方在合理期限內是否提供擔保或恢復履行能力,可將不安抗辯權的效力劃分為兩個層次。
不安抗辯權的行使需要以下條件
第一,合同雙方當事人因同一雙務合同而互負債務。此條件為基礎,不安抗辯權的行使只能針對合同相對方,不能以案外人違約作為理由進行抗辯[2]。即,案外人的違約可能導致的合同后履行人存在違約情形不可直接主觀認為后履約人就存在違約情況;
第二,后履行方雖然存在喪失或者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情形,但并危及對方當事人債權的實現。具體表現在《合同法》第六十八條條中有列舉式說明。可以肯定的是,如顧老所言,“根本違約,而且要有確切證據,才能行使不安抗辯。”因此,除卻八十六條列舉的情況,想要行使不安抗辯權的前提是能有確切證據證明對方根本違約。如果僅僅只是違反了或者不能履行合同準備工作、次要合同給付義務、附隨義務等不影響主合同的根本履行的義務,則不能行使不安抗辯權。此時,合同的根本違約的另一層表示意思是難以完整的對待給付[3]。
第三,在形式上,抗辯一方需按照法律規定向另一方履行“通知”義務,這是影響不安抗辯能否有效成立的關鍵因素。究其本質,在于希望合同雙方能通過協商的方式將不安事由消除,以便能按約定履行合同[4]。因此,此處的“通知”,筆者認為書面的,列出中止理由的通知到達對方之后,才能更加全面的證實己方所履行的義務。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構成不安抗辯權適用的事由,在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時不能為雙方所預知,也不能是合同成立之前所發生的事由,否則當事人不得行使不安抗辯權。
第一、行使不安抗辯權,須在合同成立后對方發生財產狀況惡化,且有難為給付之可能。此種財產狀況的惡化在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時不能為雙方所預知。明知對方當事人財產狀況嚴重惡化而仍與其簽訂合同的,視為其自愿承擔不能得到對待給付的風險,不能取得不安抗辯權。應當得知而因過失沒有得知的,亦不能取得不安抗辯權。構成不安抗辯權適用的事由,必須是合同成立后所發生的事由,如果在合同訂立時即具有這些事由的,先為履行義務的一方如不知情,可以援引欺詐、錯誤等進行抗辯,尋求救濟;如明知這些情況而仍然簽訂合同,承擔風險是其預料之中的事,就沒有給予不安抗辯權保護的必要。
第二、同樣的,如果應先履行一方在簽訂合同時已知相對人不可能履行合同,也不得行使不安抗辯權[6]。因為不安抗辯權的行使,必須是在訂立合同時對相對人可能不履行合同處于不明知狀態,如已知相對人可能不履行合同而仍與之訂立合同,是甘愿冒險,先履行義務一方已無權行使抗辯權,應對由此產生的后果承擔責任。
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速的放緩和下行壓力的加大,企業經營困難的情況有所增加,交易過程中對對方履約能力的關注也變得更為重要。不安抗辯權作為一種合同履行抗辯權,意在保護合同先履行義務方的合法權益,越來越受到關注和重視。綜上所述,對于不安抗辯權中止合同履行的形式以及終止履行的條件,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