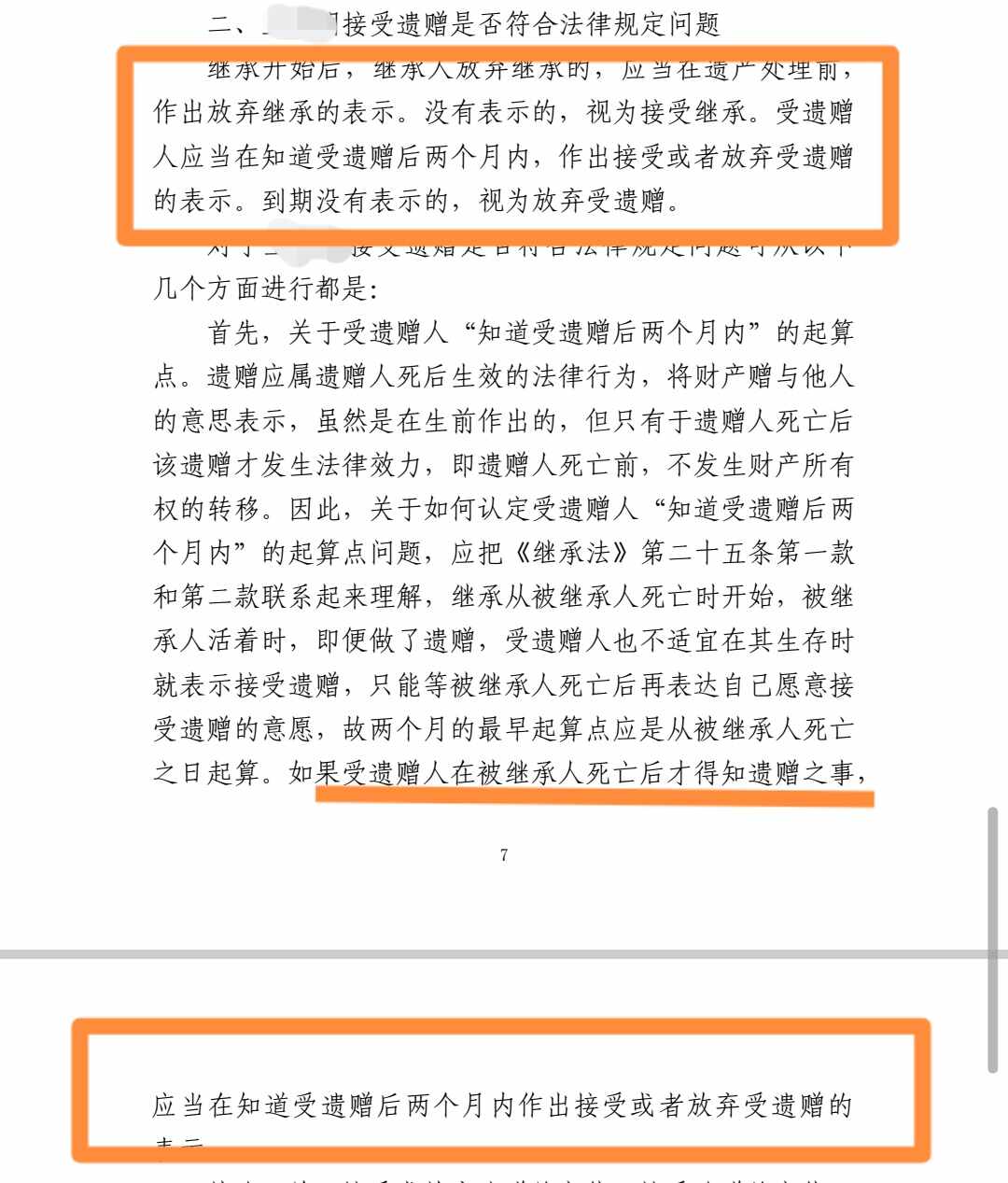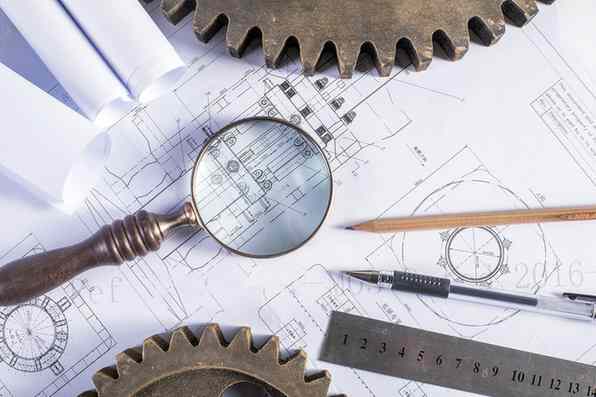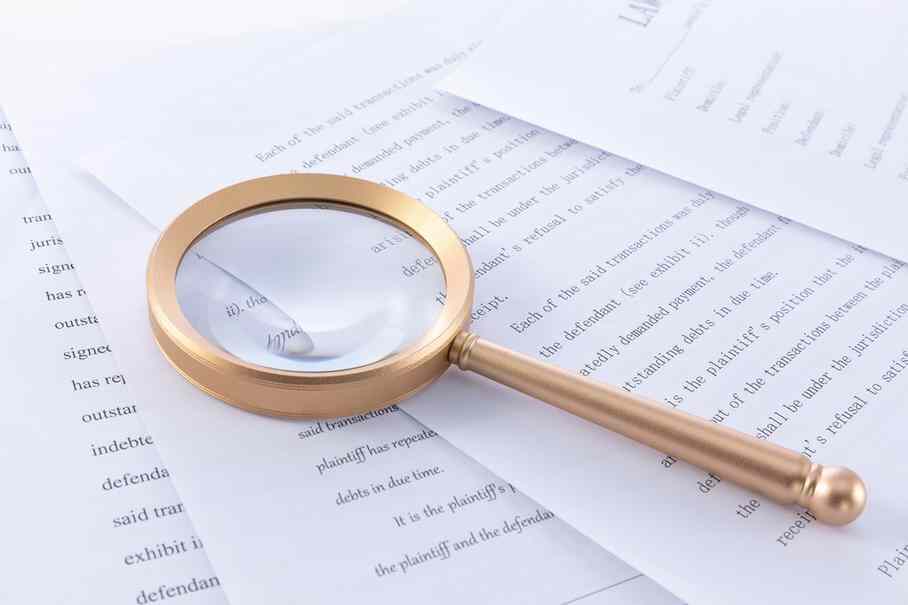建設工程承包人法定抵押權的效力
 毋磊穎律師2021.11.02892人閱讀
毋磊穎律師2021.11.02892人閱讀
導讀:
建設工程承包人法定抵押權的效力
建設工程承包人法定抵押權的效力
就其效力而言,法定抵押權優先于經登記的約定抵押權與發包人的其他債權,此點殆無疑義,司法解釋對此也予以明確。問題在于,在所建設商品房已進行預售或銷售的情況下,承包人與購房人之間的關系應如何處理。我國的物權制度雖未臻完善,但物權法定的原則已經基本確立,不動產物權的轉移以登記為條件,與此相配套的還有商品房買賣合同的登記制度。經登記的商品房買受人可對抗包括抵押權人在內的其他債權人,但經登記的商品房買受人是否可對抗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權則存有疑問。我們認為,經登記的商品房買受人對該商品房享有的權利是一種物權性質的權利,承包人法定抵押權雖可對抗抵押權及其他債權,但應不具備對抗經登記的買受人的效力。但未經登記的買受人對該商品房享有的是純粹的債權,因此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權優先于未經登記的買受人的債權。
令人關注的是,司法解釋規定法定抵押權不能對抗已支付全部或大部分購房款項的消費者,這應理解為基于利益衡量考慮對法條作出的限縮解釋。有學者指出,消費者利益屬生存利益,應優先于承包人的經營利益,因此應對消費者進行特殊保護。但是,對消費者與一般商品房購買人的區別存在認定上的問題。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可見立法是從合同簽訂的目的來判斷是否屬消費者,非為生活需要購買則不屬消費者。這一點也是眾多法院不支持知假買假并索賠的“王海現象”的法律依據。從現實來看,房地產作為一種重要的投資方式,有相當數量的購房人并不是為了生活需要而購房,其購房目的或是為了投資,或是為了經商需要,這種現象在大中城市大量存在。在此情形承包人是否可以購房人不是消費者為由進行對抗呢
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上述規定來看,承包人應可進行對抗,但在舉證方面將面臨極大困難,而且合同法第286條規定承包人行使法定抵押權時并不需要進行訴訟,因此當購房人與承包人就此產生爭議時,也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濟程序。我們認為,對消費者的認定應采取較為寬松的立場,購房者只需證明其與發包人存在購房合同且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購房款即可,如承包人有異議,應由承包人承擔舉證責任。但對消費者的認定應有如下標準:第一,消費者應為自然人,非自然人不能成為法律意義上的消費者,個體工商戶等特殊自然人也可成為消費者。第二,消費者所購房屋規劃用途應為住宅或住宅式公寓等用于居住的商品房,寫字樓、商鋪等商品房的購買者不能認定為消費者。需至少兩個條件同時滿足的商品房買受人才能對抗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權。但對經登記或已辦理產權過戶的商品房買受人,無論是否屬消費者,其均可對抗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權。
承包人法定抵押權既是一種優先受償權,在發包人破產時,其受償效力應位于員工工資、福利及稅款之后,抵押權及其他債權之前。如發包人宣告破產于工程竣工或合同約定的工程竣工之前,由于承包人法定抵押權的產生系基于建設工程合同的行為,而非工程竣工的事實,因此承包人自可主張破產財產的優先受償權。
合同法第286條并未規定承包人債權的范圍,只規定為“價款”。前述司法解釋將價款作了不同于擔保法關于抵押權受償范圍的狹義解釋,僅包括為承包人為建設工程應付的工作人員報酬、材料款等實際支出費用,包括其付墊資工程費用,但不得包括承包人因發包人違約所造成的損失。該司法解釋的出發點可能是出于對發包人其他債權人利益的保護,但其是否完全符合合同法的立法本意,則頗值商榷。本文在此無意就此深入討論,但該司法解釋在概念上至少不夠周延,在操作層面上不夠嚴謹。建設工程合同約定的價款除承包人實際支出的工作人員報酬及材料款外,還包括承包人應得利潤,而司法解釋并未明確承包人是否可就該部分主張優先受償。此外,由于合同法規定承包人行使法定抵押權不需經過訴訟程序,因此承包人的實際支出費用數額的認定也存在一定的困難,對其他債權人可能不利。我們認為,即便對價款作狹義解釋,也應包括承包人應得利潤。如因發包人未按時支付價款而致工程未能在合同約定的工期完工,則承包人只能就其實際支出費用主張優先受償權尚在情理之中,在建設工程已完工的情況下,還要求承包人只能就實際支出費用主張優先受償則似與合同法立法本意相悖,此時承包人理應可就建設工程合同約定的價款主張優先受償權。
工程建筑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