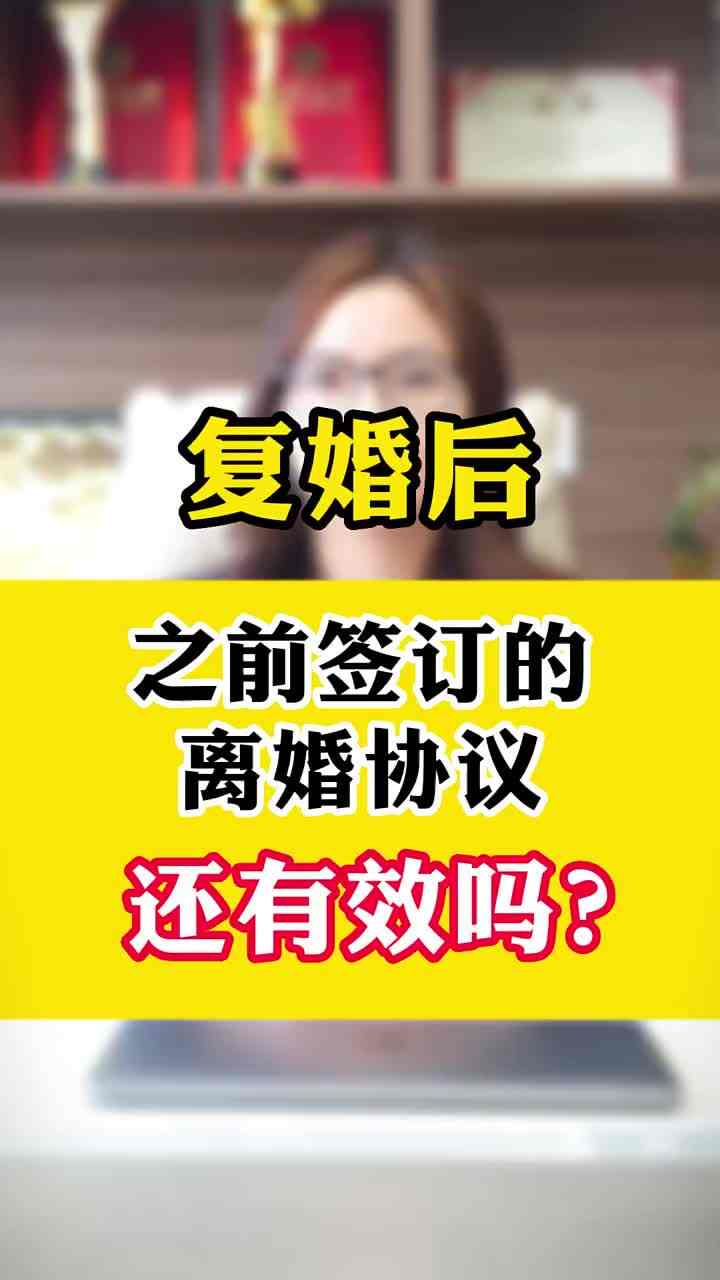私刻公章簽擔保協議有效嗎
 周春花律師2021.12.23732人閱讀
周春花律師2021.12.23732人閱讀
導讀:
同日,A公司使用私刻的B公司公章及仿冒的B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簽名,以B公司名義與甲銀行簽訂土地使用權抵押協議,約定B公司對上述借款承擔擔保責任。在訴訟過程中,法院對本案也產生了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A公司代B公司簽訂土地使用權抵押協議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B公司應當對借款承擔擔保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A公司代簽抵押協議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該抵押協議并非B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B公司不應對借款承擔擔保責任,甲銀行無權行使抵押權。那么私刻公章簽擔保協議有效嗎。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同日,A公司使用私刻的B公司公章及仿冒的B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簽名,以B公司名義與甲銀行簽訂土地使用權抵押協議,約定B公司對上述借款承擔擔保責任。在訴訟過程中,法院對本案也產生了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A公司代B公司簽訂土地使用權抵押協議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B公司應當對借款承擔擔保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A公司代簽抵押協議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該抵押協議并非B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B公司不應對借款承擔擔保責任,甲銀行無權行使抵押權。關于私刻公章簽擔保協議有效嗎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簡要案情
1997年12月1日,某集團公司與A公司簽訂企業承包協議,約定該集團公司將其全資子公司B公司承包給A公司經營,承包期限至2004年12月1日止。協議簽訂后,某集團公司向A公司移交了B公司的全套公章、營業執照及其他文件,包括一塊土地的土地使用權證書。后某集團公司因故于1999年8月收回了B公司的公章、營業執照等文件,但未收回土地使用權證書。
2000年10月1日,甲銀行與C公司簽訂借款合同,約定C公司向甲銀行借款若干,還款期至2001年10月1日止。同日,A公司使用私刻的B公司公章及仿冒的B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簽名,以B公司名義與甲銀行簽訂土地使用權抵押協議,約定B公司對上述借款承擔擔保責任。此后,A公司又使用私刻的B公司公章及偽造的B公司的《職代會決議》向當地土地管理部門提出申請,并辦理了土地使用權抵押登記,抵押權人為甲銀行。還款期限屆至,C公司無力償還借款,B公司亦未承擔擔保責任。2002年2月10日,甲銀行訴至法院,要求C公司償還借款,B公司以抵押的土地承擔擔保責任。
分歧意見
訴訟中,各方對C公司應履行還款義務均無爭議,其爭議焦點在于:B公司應否對借款承擔擔保責任,即甲銀行可否行使土地抵押權。在訴訟過程中,法院對本案也產生了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A公司代B公司簽訂土地使用權抵押協議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B公司應當對借款承擔擔保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A公司代簽抵押協議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該抵押協議并非B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B公司不應對借款承擔擔保責任,甲銀行無權行使抵押權。
本案解析
筆者認為,從以下幾個角度分析,甲銀行有權行使抵押權。
一、承包經營權的內容
在我國,較早的經營權及承包經營權的概念出現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民法通則及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中,主要是指對國家、集體所有的財產(例如全民所有制企業中的國家財產、集體所有的土地、國家所有的荒山、灘涂等)的經營或承包經營的權利。在初期,承包經營權主體的范圍非常狹窄,僅指從事農業生產的集體或個人,且權利的內容也很狹窄,有的僅有使用收益的權利,沒有處分權。隨著經濟的發展,把權利主體及內容限定在如此狹窄的范圍內已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承包經營,其權利內容也不僅僅限于使用收益,而與承包經營合同的具體內容聯系起來了。
理論上,有觀點認為,承包經營權是一種用益物權,是為收益圍繞著市場對財產進行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其四項權能齊全,但與所有者憑自己意志支配所擁有財產的四項權能是有區別的,它僅是經營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換而言之,承包經營權的權利人是否擁有全部四項權能及任何權能的行使方式與發包人所給予的授權有很大關系。

具體到本案,A公司對B公司的承包經營權是否齊備四項權能,可否將B公司的土地使用權用于抵押,要看某集團公司對A公司授權的具體內容。某集團公司將B公司交給A公司經營時,雖未出具授權委托書,但移交了公章、營業執照及其它經營所必備的文件,這種行為系某集團公司履行承包經營協議項下義務的行為,在客觀上也確實起到了公示代理的實際效果,使交易相對人相信A公司有權處理B公司的全部事務,故A公司基于承包經營合同對B公司的財產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因此,本案中A公司當然可將B公司的土地使用權用于抵押,其所產生的法律效果應歸于B公司。
二、某集團公司收回公章、營業執照是否意味著A公司代理權的消滅
筆者認為,某集團公司收回公章、營業執照的行為并不當然消滅了A公司基于承包經營權所擁有的代理權。理由如下:
首先,從承包經營合同的目的分析,承包經營合同本身包含了授權內容,只要合同未終止,承包人則一直擁有基于合同所產生的代理權,而無需另行授權。承包經營的目的與其他任何經營方式的目的一樣,均追求投資者(或稱為股東、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為此,投資者最終確定的承包人在經營方面應比投資者本人更有經驗或專長,且一般情況下,投資者更愿意承包人全權處理被承包企業的各項事務,以利于整個企業的整體發展。因此,在實踐中,很少發生簽訂承包經營合同后,作為發包人的投資者另行授權給承包人的情況。簡而言之,承包經營合同中的授權行為與基礎法律關系相伴而生,除非合同提前終止,否則承包人基于承包合同即可擁有代理權(即承包經營合同具有概括授權的性質和效果)。具體到本案,某集團公司雖收回了公章等,但并未終止承包經營合同,因此A公司在某集團公司收回公章等后仍擁有承包經營權,也擁有代理權,只不過該權利的行使受到了更為嚴格的限制,其方便性和行使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而已。
其次,從公示的角度分析,如某集團公司收回公章、營業執照意在收回概括授權,剝奪A公司的代理權,其應當采用與授權相同的公示方式,才能達到與授權相同的公示效果。就本案的具體情況分析,某集團公司因故收回公章、營業執照等文件并非意在收回已通過承包經營合同賦予A公司的權利,其采取的方式也不能產生令交易相對方知曉該事實的法律效果,而且該集團公司并未收回全部文件,對本案抵押協議及抵押登記有關鍵作用的土地使用權證書仍在A公司手中。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交易相對方的甲銀行完全有理由信任自承包合同簽訂之日起至簽訂抵押合同之日,A公司當然是B公司的代理人,其以B公司名義所為的一切行為的法律后果都應由B公司承擔。
三、A公司偽造公章、簽名等文件的行為不能否定由B公司應承擔A公司行為的法律后果
A公司偽造公章、職工代表大會決議等行為,所導致的后果應屬代理行為中意思表示瑕疵的問題。我國民法中的代理制度對有代理權的情況下,代理人向相對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瑕疵所產生的法律后果沒有明確的規定,但從代理制度本身的制度價值,及其在相對人無過失的情況下更傾向于保護交易安全的價值取向等方面分析,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德國法中對冒用他人姓名從事行為法律后果的處理原則,即其產生代理的效果。具體到本案,由B公司承擔A公司行為的法律后果,甲銀行可行使抵押權,至于該偽造行為所帶來的侵權問題,屬于A、B兩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可另案解決。[page]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王延玲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