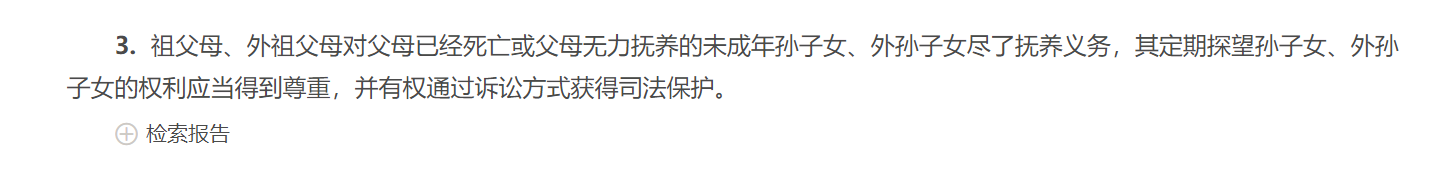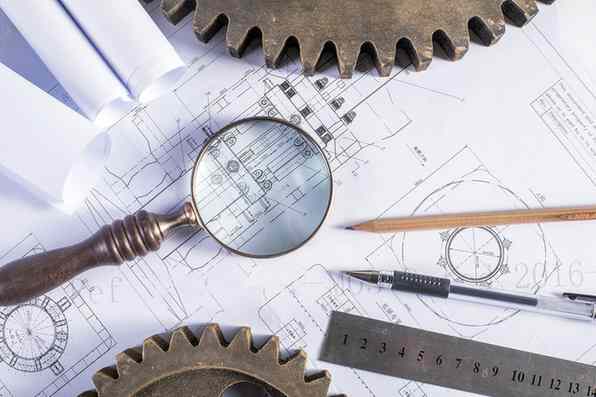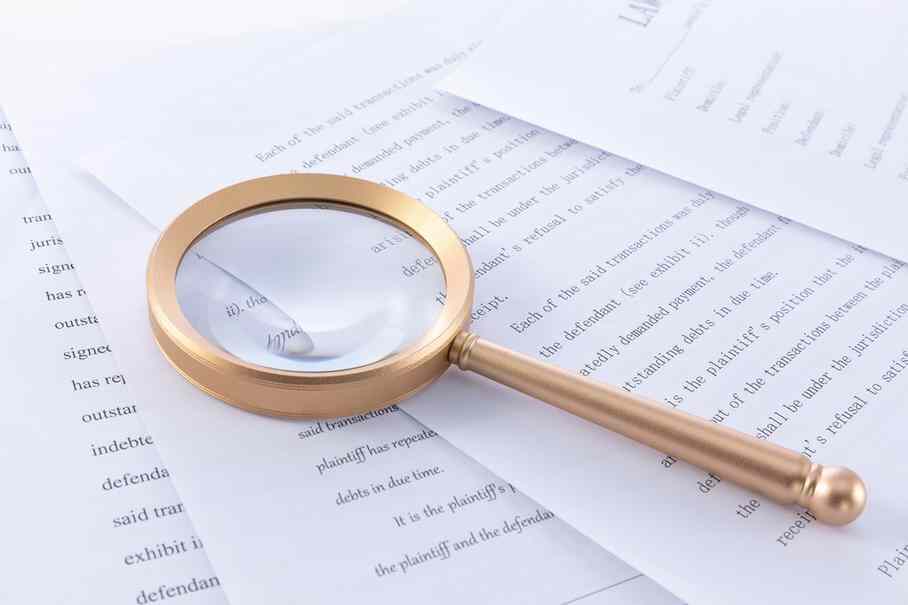建設工程轉包的定義與特征
 李楠楠律師2021.10.27601人閱讀
李楠楠律師2021.10.27601人閱讀
導讀:
建設工程轉包的定義與特征
建設工程轉包的定義與特征
基于轉包建設工程的重大危害,我國歷來重視通過法律規范禁止建筑業的轉包行為。
1984年頒布的《建筑企業營業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總包單位對所承包工程的主要部分必須自行完成,不得轉包。”
1986年頒布的《建筑安裝工程總分包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 本辦法中的轉包工程,是指建筑施工單位以贏利為目的,將承包的工程轉包給其他的施工單位,不對工程承擔任何技術、質量、經濟法律責任的行為。”第十八條規定:“下列行為均屬轉包:1.建筑企業將承包的工程全部包給其他施工單位,從中提取回扣者;2.總包單位違反本辦法第六條規定、將工程的主要部分或群體工程中半數以上的單位工程包給其他施工單位者;3.分包單位違反本辦法第八條規定,將承包的工程再次包給其他施工單位者。”
1989年頒布的《施工企業資質管理規定》第二十一條規定:“禁止施工企業倒手轉包工程。本條所稱倒手轉包系指工程承包者將工程轉交其他單位,只收取管理費,不對工程施工進行管理,不承擔技術、經濟責任的行為。”
1998年建設部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工程招標投標管理的規定》規定:“禁止工程轉包和違法分包……按照《建筑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凡承包單位在承接工程后,對該工程不派出項目管理班子,不進行質量、安全、進度等管理,不依照合同約定履行承包義務,無論是將承包的工程全部轉包給他人,還是以分包的名義將工程肢解后分別轉包給他人,均屬違法的轉包行為。”
2000年頒布的《建筑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第七十八規定:“本條例所稱轉包,是指承包單位承包建設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約定的責任和義務,將其承包的全部建設工程轉給他人或者將其承包的全部建設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義分別轉給其他單位承包的行為。”
2004年頒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禁止將承包的工程進行轉包。不履行合同約定,將其承包的全部工程發包給他人,或者將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義分別發包給他人的,屬于轉包行為。違反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分包工程發包人將工程分包后,未在施工現場設立項目管理機構和派駐相應人員,并未對該工程的施工活動進行組織管理的,視同轉包行為。”
上述法律和規章基于制定者的不同認識,或抽象概括,或具體列舉,從不同的角度定義了轉包行為或制定了轉包行為的認定標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就禁止轉包行為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筆者也注意到,上述法律和規章中的有的定義屬單獨定義,僅反映了某一特定現象,雖有很強的具體針對性和剛性,但抽象性不高;有的定義中的種差卻包含了定義對象,這顯然違反了定義的基本規則;有的定義和認定標準與現行有效法律存在沖突。而建筑市場的復雜性和轉包行為的多樣性,需要制定一個普遍定義或者抽象定義,以體現轉包行為的內涵和外延。定義轉包之前應先分析轉包的特征,特征即事物本身的獨特屬性,“一事物的特征,即它的質的規定性,是它區別于其他事物而獨立存在的基礎。”只有掌握了轉包行為的特征,才能運用準確、簡單、科學的語言對轉包作出恰當定義。
轉包一般通過轉包人與接受轉包人之間簽訂合同實現,旨在設立一種民事法律關系。民事主體基于意思表示,設立、變更和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行為稱之為民事行為,因此,不論轉包是否欠缺合法性要件,轉包定義中的屬當為民事行為。轉包定義中的種差比較復雜,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特征:
轉包行為發生在承包人承包建設工程之后。在意向承包人未能成為建設工程的承建主體之前,雖然也存在著意向承包人與他人預約轉包或約定“附生效條件”的轉包,但此時轉包行為的對象是否可以實現尚不確定。只有通過招投標或其他形式,使意向承包人成為建設工程的承包人,才具備承包人轉包的現實條件。在承包人具備轉包的現實條件后,承包人仍未與他人解除預約轉包或“附生效條件”轉包的,則視為承包人在承包建設工程之后實施了轉包行為。
承包人不履行承包合同的主要義務并約定由他人履行承包合同的主要義務,這是轉包行為的主要特征。若承包人僅不履行承包合同的義務,則構成違約,需向發包人承擔違約責任,但并不構成轉包。只有在承包人既不履行承包合同的主要義務,又約定了由他人履行承包合同的主要義務時,才符合轉包特征。這里之所以規定“承包人不履行承包合同的主要義務”而不是“承包人不履行承包合同的所有義務”,是因為在實踐中,有的承包人并非完全脫離合同義務,仍然會負責一些協調、聯系、結算價款、收集技術資料等行為,但非常明確的是,轉包行為實施后,建設工程施工這一合同的主要義務并非由承包人完成。這里的“約定”是指承包人與接受轉包人之間的約定。這里的“他人”是指接受轉包人,接受轉包人可以是單一主體,也可以是若干主體。
轉包行為具有整體性。承包人轉讓的是全部工程的建設;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承包人轉讓的是承包合同的所有義務或所有主要義務。實踐中,轉讓的義務不僅包括承包合同的所有義務或所有主要義務,而且一般會附加一些新的義務。僅轉讓部分工程建設或部分合同義務的,可能構成分包,若轉讓的是主體工程或雖非主體工程但未得到發包人同意的,構成非法分包,但不構成轉包。
轉包行為的實現方式具有多樣性,比如,將全部建設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義轉讓給其他人實際施工,或將全部建設工程直接轉讓給其他人實際施工。鑒于轉包實現方式的多樣性和人類思維的局限性,完全列舉轉包的實現方式是困難的,并且無論哪種實現方式,最終歸結為轉包人不履行承包合同的主要義務而約定由他人履行承包合同的主要義務這一本質特征。因此,定義轉包時可不將轉包的實現方式列入其中。
此外,轉包人在轉包行為中以收取管理費等名義從中牟利是普遍現象,但是否必須以牟利為目的才構成轉包呢筆者認為,禁止轉包的主要目的之一為保證建設工程質量,實現這一目的與轉包人是否牟利并無必然聯系。若轉包行為需以轉包人牟利為條件的,則在特殊情況下,比如承包人因不能按承包合同約定的工期完成建設義務而轉讓承包合同義務和權利的,則有可能不存在牟利目的,但這種行為仍可能對建設工程質量造成危害,當屬禁止之列。可見,從立法的目的解釋角度而言,轉包人是否具有牟利目的不應成為轉包的特征之一。
在歸納了轉包特征的基礎上,筆者認為,轉包是指承包人承包建設工程后,不履行承包合同約定的所有主要義務,并與他人約定由他人履行不少于承包合同中約定的所有主要義務的行為。轉包的外在形式與合同權利義務的概括轉讓非常相似,乃至有學者認為,“轉包在理論上稱為合同的轉讓,是合同權利義務的概括轉讓。” 有的學者則認為,“從民法的角度講,轉包屬于第三人代替債務人履行債務的行為,并構成違約,行為人應承擔違約的民事責任。
筆者認為,若轉包即為合同的概括轉讓,則由法律禁止轉包之規定可推出法律禁止承包人合同項下的權利義務概括轉讓,但若經發包人同意、又不違反招投標法律,并且受讓方的資質符合法定要求的,法律似無禁止承包人合同權利義務概括轉讓之必要;并且在轉包后,接受轉包人的權利通常比原合同少,而義務通常增多,這與合同權利義務的概括轉讓存有區別。若轉包的法律性質為第三人替代履行的,依據合同法之規定,不論第三人履行是否適當全面,第三人無需向債權人承擔責任,但轉包中的接受轉包人在特定情形需向發包人承擔責任;并且,債務人與第三人協議由第三人替代履行的,該協議并不必然無效,但轉包人與接受轉包人之間的轉包協議必然無效。因此,筆者不同意上述兩種觀點,筆者認為,轉包是一個獨立的法律概念,合同法總則中的概念與條文不能包含轉包,而且也沒有必要非得在合同法中找到相關依據。筆者的這種觀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可以得到印證,該法第39條規定,“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內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或者出租給第三方,承包方與發包方的承包關系不變”,這里的轉包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概念提出,既不同于合同權利義務概括轉讓,亦不同于第三人替代履行。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