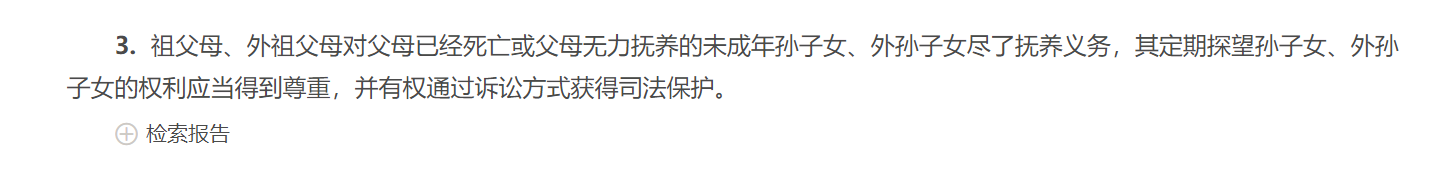債權債務的管轄法院
 李孟陽律師2021.10.20835人閱讀
李孟陽律師2021.10.20835人閱讀
導讀:
以物抵債是對合同的一種承諾,不以物品作為交付的前提下成立的條件,故此以物抵債協議成立并生效。雙方當時人之間在債務清償期屆滿后的以物抵債協議,一般應認定為新債清償,在無當事人明確的約定的情況下,其系雙方當事人之間另行增加的一種債務清償方式。債權人可以自行選擇更有利于債權實現的方式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
在實踐中,以物抵債協議非常常見。由于債務未得到履行,債權人依據與債務人之間已經存在的債權債務關系,與債務人簽訂以物抵債協議,約定將債務人名下不動產抵償給債權人。在這種情形下,存在大量債權人在以物抵債協議簽訂后,未辦理不動產變更登記的情況。這時,若債務人發生另案糾紛,由于抵債物仍然在債務人名下,其他債權人在訴訟程序中很可能對該抵債物采取保全措施,進而在債務人敗訴后申請進入執行程序,此時以物抵債協議的債權人往往會通過提起案外人異議之訴來阻卻法院的執行。
但是,在不動產已經被其他債權人申請強制執行時,債權人能否依據以物抵債享有物權期待權,即以物抵債的權利人是否具備排除強制執行的訴訟權利能力的問題,目前在司法實務中,尚未形成統一認識。本文在研究了大量案例的基礎上,通過選取部分典型案例,結合九民會議紀要新規,將從以物抵債協議的效力及性質進行分析,論證案外人能否依據以物抵債協議排除強制執行相關問題。
一、關于以物抵債協議的效力與性質的認定
(一)以物抵債協議的概念
以物抵債是指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存在金錢債務,經雙方約定以特定物替代原金錢債務進行清償而消滅債務的法律行為(或者債務人與債權人約定以債務人或經第三人同意的第三人所有的財產折價歸債權人所有,用以消滅債務人對債權人所負金錢債務的協議)。實務中將該種替代履行債務的方式稱為以物抵債,其中最常見的是不動產抵債協議(以房抵債)。
(二)以物抵債協議的效力
關于以物抵債協議的效力,在實踐中,其性質到底屬于實踐性合同還是諾成性合同頗具爭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曾認為,當事人在債務已屆清償期后約定以物抵債的,該約定實為債務的清償,且系以他物替代清償,因代物清償行為為實踐性法律行為,在未辦理物權轉移手續前,清償行為尚不成立,故當事人要求履行抵債協議的,人民法院應不予支持。但這一觀點在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九民會議紀要》)中已經有所改變,在這一點上,《九民會議紀要》在認定以物抵債協議的性質和效力時,要求根據訂立協議時履行期限是否已經屆滿予以區別對待。對于債務履行期屆滿前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根據《九民會議紀要》第45條的規定,當事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前達成以物抵債協議,抵債物尚未交付債權人,債權人請求債務人交付的,因此種情況不同于本紀要第71條規定的讓與擔保,人民法院應當向其釋明,其應當根據原債權債務關系提起訴訟。經釋明后當事人仍拒絕變更訴訟請求的,應當駁回其訴訟請求,但不影響其根據原債權債務關系另行提起訴訟。這意味著《九民會議紀要》并沒有對履行期屆滿前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效力予以認定。
而對于債務履行期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根據《九民會議紀要》的規定,當事人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達成以物抵債協議,抵債物尚未交付債權人,債權人請求債務人交付的,人民法院要著重審查以物抵債協議是否存在惡意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等情形,避免虛假訴訟的發生。經審查,不存在以上情況,且無其他無效事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也就是說,此條規定改變了過去審判實踐中“要物說”的觀點,認可了“諾成說”的觀點,債務履行期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成立并生效,這時債務人雖然還未實際交付標的物,但債權人可根據以物抵債協議要求債務人完成交付義務。不再像過去標的物的交付為成立要件。
(三)債務履行期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的性質
通過梳理最高法的判例,發現對債務履行期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可能構成債的更改(即成立新債務,消滅舊債務),也可能構成新債清償,即成立新債務,但同時舊債務不消滅,新舊債務并存。基于保護債權的理念,債的更改一般需有當事人明確消滅舊債的合意,否則,債務清償期屆滿后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性質應認定為新債清償。在新債務合法有效并得以履行完畢后,舊債務才歸于消滅。若債務人屆期不履行新債務,致使以物抵債協議不能實現的,債權人仍有權請求債務人履行舊債務,且該請求權的行使,并不以以物抵債協議無效、被撤銷或者被解除為前提。若因債務人反悔而屆期不履行新債務,但其又未能提供證據證明有能力繼續履行原債務的,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繼續履行以物抵債協議的,應予支持。
二、案外人能否以以物抵債協議提起執行異議排除法院強制執行
以物抵債協議實踐中多為以不動產進行抵債,如果雙方已經辦理不動產登記,則已經成為不動產所有權人,法律應當保護。但如果沒有辦理不動產登記,依前文所述,債務履行期屆滿后簽訂的以物抵債協議,協議有效,物權是否變動與否并不影響債權的效力。但這時抵債協議僅能產生債權效力,受讓人僅享有以物抵債標的物的登記請求權和物的交付請求權。這時,若債務人發生另案糾紛,由于不動產未辦理登記,此時仍然在債務人名下,其他債權人在訴訟程序中很可能對該抵債物采取保全措施,進而在債務人敗訴后申請進入執行程序。此時以物抵債協議的債權人往往會通過提起案外人異議之訴來阻卻法院的執行。而他們起訴的依據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執行異議復議規定》)第二十八條,即“金錢債權執行中,買受人對登記在被執行人名下的不動產提出異議,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權利能夠排除執行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簽訂合法有效的書面買賣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該不動產;(三)已支付全部價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約定支付部分價款且將剩余價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執行;(四)非因買受人自身原因未辦理過戶登記。”
然而,在以物抵債協議能否適用本條排除執行的問題上,實務中常常存在較大爭議。據查,最高人民法院最初擬將抵債受讓人也納入物權期待權人的保護對象,然而考慮到實踐中以物抵債的問題比較復雜,尤其是目前尚無鑒定合同確切簽訂時間的有效技術手段,不能排除部分案外人與被執行人惡意串通倒簽抵債時間以排除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同時抵債時無需支付對價,通過表面證據很難判斷抵債合意的真偽。最后,因未達成一致意見,未將抵債受讓人列入物權期待權保護范圍。本文經檢索案例發現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呈現出不同的觀點。
通過檢索到的最高院判決書來看,實務中存在大量以物抵債的債權人可以行使阻卻執行權利的觀點[(2019)最高法民申6083號、(2019)最高法民終1417號等],持此種觀點的法官認為,債務履行期屆滿時達成的以物抵債協議是各方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協議約定以房屋抵償債務,此時債權人應當被視為買受人且已交付全部購房款,而以物抵債僅僅是購房款的一種支付方式。在滿足《執行異議復議規定》第28條規定其他條件的基礎上,應當認定以物抵債協議的債權人對案涉房產享有足以排除執行的民事權利。
然而,也有部分法官認為以物抵債協議的債權人不具備可以阻卻法院強制執行程序的權利。這個觀點主要是從《執行異議復議規定》第二十八條的第一款出發,認為以物抵債協議是一種債的清償,是促使債務人履行債務的方式,其目的在于消滅債權,簽訂協議并非是為了房屋買賣。由于以物抵債協議的受讓人并不存在購房的本意,因此應當將以物抵債協議受讓人與真正的購房者相區別,從合同訂立的本意出發,不能簡單將以物抵債協議與房屋買賣合同劃等號。因此以房抵債并不屬于《執行異議復議規定》第二十八條規定的情形,在房屋權屬未變更登記前,以房抵債協議不能優于其他債權,因而不能阻卻其他合法權利人基于生效法律文書申請強制執行。
本文認為
在這個問題上,本文認為,對于執行異議之訴而言,本身涉及的就是權利大小的利益權衡,所以不能忽略制度設計背后的邏輯起點。要判斷以物抵債受讓人是否享有阻卻法院強制執行的實體權利,應當依據以物抵債協議所設立的基礎債權關系進行分析,從更深層次去探究基礎債權的性質,不能簡單一概而論。《執行異議復議規定》之所以要對買受人物權期待權進行保護,實際上是物權優先于債權的體現,因此,物之交付的債權也應當優先于普通債權。由于以物抵債所欲消滅的基礎法律關系為金錢債權的履行,抵債協議實際上也是依托于原債權而產生的抵債變通方式,因此也不應優先于另外一個金錢債權的實現。因此,無法產生物權期待權的法律效果。因此,若以物抵債協議所欲消滅消滅的基礎法律關系為金錢債務的履行而非設立房屋買賣行為,原則上不應當產生阻卻強制執行的效果。
但是,若能夠依據現有證據,判斷以物抵債協議成立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是成立新的買賣合意(比如將原債權中未為給付的部分轉為抵債房產的對價,原金錢之債解除并轉化為房屋買賣合同關系中的對價),則可適用《執行異議復議規定》的規定,在滿足其他條件的情況下,享有排除執行的權利,同時應當注意的是,若以物抵債協議消滅的是享有優先權的債權,則應當根據權利本身的性質接受抵債房產主體的身份判斷權利優先性的順位。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