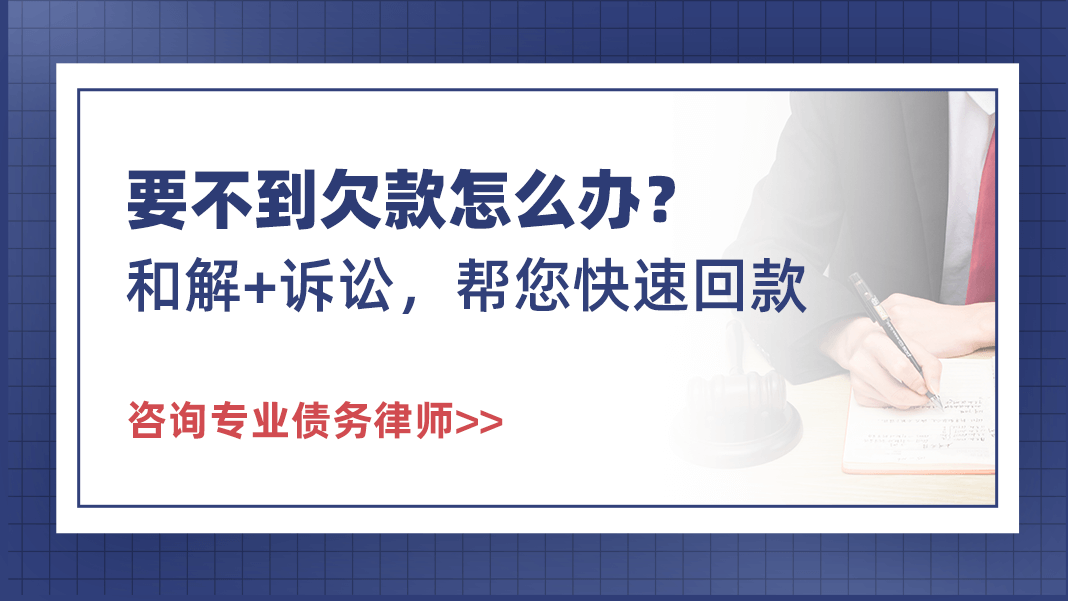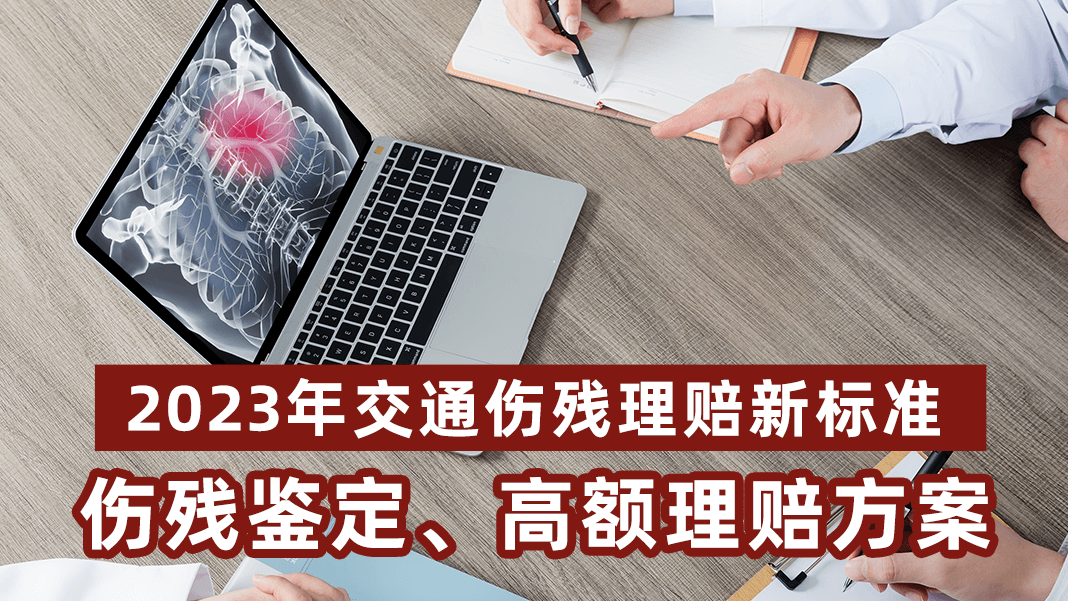簽訂過合伙合同想退伙怎么辦
 李楠楠律師2021.10.12853人閱讀
李楠楠律師2021.10.12853人閱讀
導讀:
設立有限責任公司作為經營主體,合伙各方作為股東,則中途退出的問題就是股東退出的問題。中途退出主要涉及的核心問題是:投資,要不要返還?如何返還?返還多少?根據創業所設立的目標主體類型,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設立有限責任公司作為經營主體,合伙各方作為股東,則中途退出的問題就是股東退出的問題。中途退出主要涉及的核心問題是:投資,要不要返還?如何返還?返還多少?根據創業所設立的目標主體類型,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退出的路徑相對固定:
1)如在合伙前期,已約定有退出方案,則按照先前的約定進行。
而忽視提前約定退出機制的現象普遍存在。
2)如未提前制定退出機制,則可選的退出方式基本圍繞股權轉讓展開,通過各種形式實現股權轉讓,進而退出。
關于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退出的具體路徑,可以參考我們之前的文章《股東爭議|股東退出機制的設置方法和原理》,不再贅述。
同時,在創業初期,簽訂合伙協議、成立合伙企業也是合伙的可選方式。
在有書面協議的前提下,中途退出可以按照協議的約定進行。
但實踐中,因中途退出而較難解決的原因主要是:
1)合伙各方無書面協議
2)合伙未進行工商登記注冊
3)借用他人營業執照經營
4)多人合伙而注冊為個體工商戶或個人獨資企業
在合伙關系中,即使未訂立書面協議,也需要注意以下內容:出資數額、盈余分配、債務承擔、入伙、退伙、合伙終止等。
合伙中途退出一般面臨兩個選擇:
一是合伙事業存續,則退出涉及的是財產份額的轉讓;
一是合伙終止,則退出涉及的是合伙財產的分割。
如合伙終止,則合伙財產的分割按照以下進行:
① 有約定,從約定
② 無約定,合伙各方進行協商
③ 協商不成按照出資比例分割
④ 出資比例難以確定,則平均分擔
如合伙事業存續,則退出方需轉讓財產份額:
① 向其他合伙人轉讓財產份額,由受讓方支付費用
② 向合伙人之外的第三人轉讓財產份額,由第三人支付費用
轉讓財產份額的對價,可以由轉讓方和受讓方協商。
如無人接收,或無法對轉讓價格達成一致,則容易陷入僵局。
案例
合伙創業,中途退出,協商為主。合伙合同是《民法典》合同編新增的有名合同,旨在引導人們在合伙時簽訂書面的合伙合同。如遇糾紛,首先需要判定的是雙方是否存在合伙關系。如一貫口頭約定,則對基礎法律關系的認定造成障礙。
2000 年8月6日,原告劉陸根與被告劉慶彪、劉玉良簽訂了合伙協議,協議對各合伙人的出資份額、所占股份、盈虧分擔比例、合伙債務的償還方式及具體事務作了明確約定,原告劉陸根按合伙協議投入30000元入伙資金。合伙時扣除購買手機款2000元,實際投入28000元。
在合伙過程中,因被告劉慶彪、劉玉良隱瞞經營狀況。2001年5月,原告提出退伙,二被告口頭同意,并承諾待年底盤存時再將合伙投入及經營利潤一起支付。原告退伙后,二被告拒退原告合伙投入及應支付給原告的合伙利潤合計58171.54元。同時要求后加入的二合伙人劉曉虎、靳青燕對上述給付義務承擔連帶責任。
劉玉良等四被告辯稱:
(1)宜昌長江會計師事務所鑒定依據不充分;
(2)本案被告應是合伙時合伙所起的字號,而不是四被告;
(3)原告的訴訟時效已過,喪失勝訴權,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
(4)被告劉曉虎、靳青燕認為原告退伙后才入伙,不應承擔連帶責任。
審判
葛洲壩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認為:原告劉陸根與被告劉玉良、劉慶彪之間所訂立的合伙協議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該合伙協議明確約定了三人系三個股東地位,為明確的個人合伙。劉陸根入伙前,被告劉玉良、劉慶彪借用宜昌市鑫融物資貿易公司昌盛經營部,而該經營部于2003年11月被吊銷營業執照資格,并非系被告劉玉良、劉慶彪所辯稱的宜昌市鑫融物資貿易公司盛昌經營部,且上述二被告未能在法庭期限內舉證證明二者的聯系,因此,二被告辯稱劉玉良、劉慶彪不能作為本案適格被告的辯論觀點不予采信。
庭審查明劉陸根一直在主張債權,因此二被告辯稱訴訟時效已過的觀點亦不予采信。同時,四被告未能在法庭限定的期限內提供合伙虧損的證據,故按宜昌長江會計師事務有限公司的鑒定結論進行清算,并酌情予以支持原告為主張權利而實際支出的損失,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五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四十五條第二款、第五十四條之規定,葛洲壩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19日判決如下:
(一)被告劉玉良、劉慶彪應返還原告劉陸根合伙期間應享有的利潤10411.17元,返還原告劉陸根應享有合伙期間積累的財產45204.41元,被告劉玉良、劉慶彪共計返還原告劉陸根55615.58元;
(二)被告劉玉良、劉慶彪應支付原告劉陸根差旅費損失1429元;
(三)被告劉曉虎、靳青燕對上述給付義務承擔連帶責任。
被告劉慶彪不服一審判決,向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
(1)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不應采納宜長會司鑒字(2004)第546號鑒定報告;
(2)上訴人劉慶彪在一審中不能作為本案適格被告,
其一,上訴人劉慶彪、原審被告劉玉良在經營宜昌市鑫融物資貿易公司昌盛經營部的過程中于2000年8月6日增加被上訴人劉陸根作為昌盛經營部的股東;
其二,一審法院將三人之間的合伙關系定性為“個人合伙”,在個人合伙有字號的情況下,應當以依法核準登記的字號作為訴訟當事人;
其三,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的合伙與本案的實際情況,其成立的應是合伙企業,在合伙企業吊銷執照后清算前,作為股東的被上訴人劉陸根就要求“返還出資”于法無據;
(3)原審原告的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喪失勝訴權,請求判令被上訴人劉陸根提供2000年8月6日至2000年10月7日及2001年1月16日至2001年3月31日的原始會計資料,以便各股東進行正常清算;判令駁回被上訴人的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劉陸根辯稱:
(1)宜長會司鑒字第546號鑒定報告系雙方當事人共同委托進行鑒定的結果,應當作為證據采納,上述鑒定報告明確排除了2000年8月6日至2000年10月7日、2001年1月16日至2001年3月31日期間的利潤。
(2)宜昌市鑫融物資貿易公司不是雙方當事人合伙時所起的字號,上訴人劉慶彪應是本案的適格的被告。
(3)被上訴人家住蘭州,其主張權利主要是用電話聯系,本案不存在超過訴訟時效問題。
評析
一、
關于訴訟主體資格問題我國民事法律規定:個人合伙可以起字號,起字號的個人合伙,在民事訴訟中,應當以依法核準登記的字號為訴訟當事人,未起字號的個人合伙,合伙人在民事訴訟中為共同訴訟人。本案中的合伙人劉慶彪、劉陸根、劉玉良合伙期間并未依法進行合伙企業登記,不具有合伙企業資格,應當按照股東協議內容確定為個人合伙,故在本案中,列共同合伙人為共同訴訟人符合法律規定。
二、關于原告的請求是否已超過訴訟時效問題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本案中,原告劉陸根于2001年5月退伙后,一直向四被告主張權利,一審時,四被告均認可上述事實,但上訴人又推翻自己的陳述,二審認定劉陸根退伙后返回甘肅省蘭州市工作遠離宜昌的事實,采信其主張債權是通過電話與上訴人一方當事人多次聯系的陳述,符合常理,從而肯定訴訟時效并未喪失的事實。
二審法院認為:
(1)2000年8月6日三人簽訂的合伙協議足以證明三人之間是一種個人合伙,從該協議約定“三個股份為三個股東組成,虧本與盈利由三股份均攤、均分”的內容上分析,三人所訂立的協議也是一種個人合伙協議。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7條:上訴人劉慶彪作為合伙人之一,在本案中的訴訟主體資格合法,且上訴人劉慶彪、被上訴人劉陸根,原審被告劉玉良合伙期間掛靠的是“宜昌市鑫融物資貿易公司昌盛經營部”的營業執照上載明的負責人為盛振萍。
不是三人中的任何一人依法核準登記的《營業執照》也不是三人中的任何一人依法核準的字號,因此,上訴人劉慶彪主張其在一審中不能作為本案的適格被告及被上訴人只能以三人合伙的字號“昌盛經營部”作為本案被告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2)宜長會司鑒字(2004)第546號鑒定報告系雙方當事人選定的鑒定機構作出的鑒定結果,其鑒定程序合法、鑒定結論明確,且上訴人并未申請重新鑒定,也未提供相應證據。因此,上訴人認為該鑒定報告不能作為證據采信的上訴理由不予采納。
(3)被上訴人工作遠離宜昌,被上訴人訴稱其主張債權系通過電話與上訴人一方當事人多次聯系的陳述符合常理,因此,本案不存在超過訴訟時效的問題。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