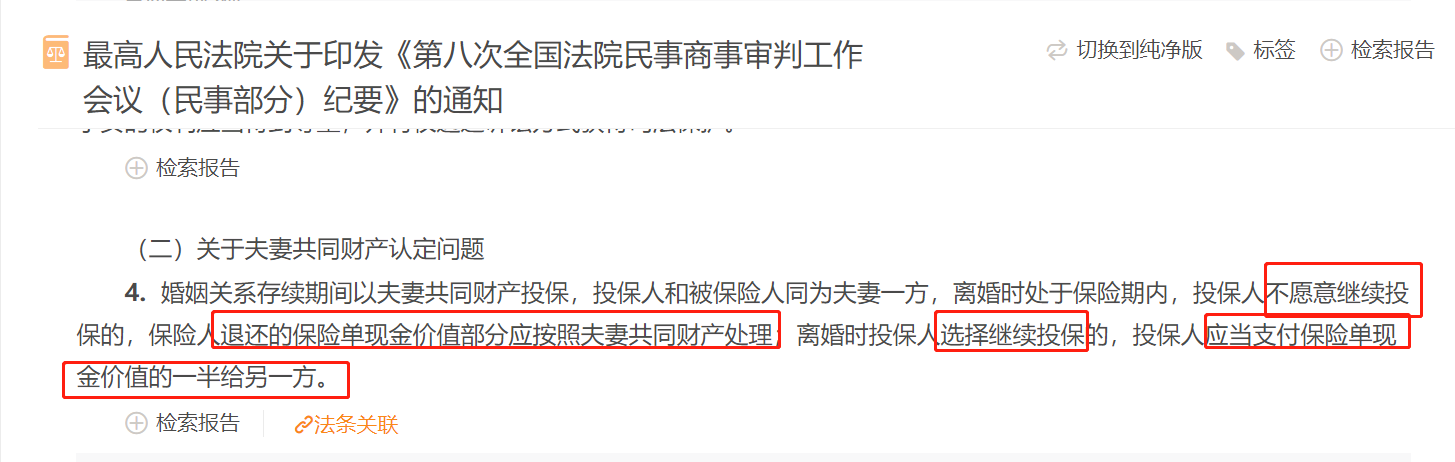保險代位權的時效是什么
 翁玉素律師2022.02.07858人閱讀
翁玉素律師2022.02.07858人閱讀
導讀:
保險代位權的時效是什么保險代位權的訴訟時效為法律規定的訴訟時效。我國民事訴訟的一般訴訟時效為3年;短期時效為一年;長期訴訟時效是指訴訟時效3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訴訟時效;最長訴訟時效為二十年;保險代位權的發生基礎當損害事故發生后,賠償權利人受有損害,但也有可能基于發生損害的同一原因而受有利益,對于這種利益,是否應從賠償權利人獲得的賠償額度中扣除,存在兩種完全相反的主張,一種為大陸法系的主張扣除的損益相抵原則;另一種為美國法上的否定扣除的平行來源規則。但這并非損益相抵理論,而是為保險人代位權的行使提供依據。那么保險代位權的時效是什么。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保險代位權的時效是什么保險代位權的訴訟時效為法律規定的訴訟時效。我國民事訴訟的一般訴訟時效為3年;短期時效為一年;長期訴訟時效是指訴訟時效3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訴訟時效;最長訴訟時效為二十年;保險代位權的發生基礎當損害事故發生后,賠償權利人受有損害,但也有可能基于發生損害的同一原因而受有利益,對于這種利益,是否應從賠償權利人獲得的賠償額度中扣除,存在兩種完全相反的主張,一種為大陸法系的主張扣除的損益相抵原則;另一種為美國法上的否定扣除的平行來源規則。但這并非損益相抵理論,而是為保險人代位權的行使提供依據。關于保險代位權的時效是什么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債權債務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保險代位權的時效是什么
保險代位權的訴訟時效為法律規定的訴訟時效。我國民事訴訟的一般訴訟時效為3年;短期時效為一年;長期訴訟時效是指訴訟時效3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訴訟時效;最長訴訟時效為二十年;
保險代位權的發生基礎
當損害事故發生后,賠償權利人受有損害,但也有可能基于發生損害的同一原因而受有利益,對于這種利益,是否應從賠償權利人獲得的賠償額度中扣除,存在兩種完全相反的主張,一種為大陸法系的主張扣除的損益相抵原則;另一種為美國法上的否定扣除的平行來源規則。
(一)損益相抵原則與保險
損益相抵的原則,在羅馬法上即已存在。在現代大陸法系各國,該原則或者表現為立法的明文規定,或表現為判例和學說予以確認的一般性原則。在現代社會,最典型的作為受害人平行來源的獲益為受害人投保的各類保險,對于受害人所獲保險金是否予以抵扣,大陸法系各國的態度卻幾乎完全一致,即保險金不能作為受害人所得利益而予以扣減。其原因卻有不同的觀點,并不統一。有觀點認為受害人取得的保險金,是以一定的保險費支付而取得的,因此并非利得;有觀點認為第一人保險的客觀目的在于受害人利益,而不是為加害人利益存在;還有觀點認為,對此應分人身保險與損失保險來說明,對于人身保險,在事故發生前,即已發生被保險人的債權,只不過是該債權的期限不定,因此保險金的取得,不能稱為基于損害事故發生而產生的利益,而損失保險不能適用損益相抵的原因在于損失保險以填補受害人損失為目的,此時加害人的賠償義務與保險人的保險給付義務,構成損害賠償義務的竟合,當一方義務的履行而使損害得到填補后,另一方的義務即歸于消滅。但這并非損益相抵理論,而是為保險人代位權的行使提供依據。因為,雖然受害人取得的兩種請求權具有相同的目的,但卻有著不同的內容,因此加害人不得主張損益相抵。
除了上述理論分析外,從實務看,保險金不能適用于損益相抵的原因有二。
第一,損益相抵無論如何不能使侵權責任的威懾功能落空。在使受害人雙重獲益和加害人免責的選擇中,侵權損害賠償必然選擇前者,更何況,由于訴訟成本和賠償范圍的限制,受害人實際上得不到完全賠償,其雙重獲益反而能彌補侵權責任制度在填補受害人損害上的先天缺陷。
第二,雖然保險人的保險義務與加害人的賠償義務具有相同的目的,但實質上,在侵權責任的雙邊結構中,損失保險的保險人與受害人具有共同的利益,一旦加害人因為受害人保險的存在而免責或減責,實際上會影響到保險人的代位權的行使,只有承認受害人的雙重獲益,保險人才能以不當得利為名,請求受害人返還已給付得保險金,從而使加害人成為一切損害賠償得最終承擔者,否則,損益相抵的結果只可能讓保險人承擔加害人的部分或全部責任,而使這種由受害者支付保險費并為其利益存在的保險反而成為加害人減輕責任的理由,這在法院、受害人和保險人看來,都是不能接受的。
在世界范圍內,完全肯定保險金適用損益相抵原則的只有斯堪的納維亞法系國家,在這些國家,在對損害的救濟上,其法律政策旨在讓保險發揮比侵權責任制度更大的作用。如瑞典保險法第20章第7條明確規定,加害人的賠償數額在一般保險支付的數額內相應扣減。丹麥損害賠償法第19條也明文規定,在已經被物損保險或者停工保險所覆蓋的責任范圍內無損害賠償責任,但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導致損害時除外。但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和意外事故保險的存在并不會減輕責任人的賠償,損益相抵原則主要適用于非人身保險領域。]因此在這些法定領域,第一人保險的存在使非故意的侵權行為得以減責或免責。
(二)平行來源規則與保險
美國法傳統上堅持損益不相抵,這一原則又被稱為平行來源規則。大多數學者認為該規則源自1854年的ThePropellerMonticellov.Molli2son案。該案中,同時裝載有貨物的一艘輪船與一艘帆船在湖上發生碰撞,導致帆船沉沒,但該船舶已投保。后保險公司接受帆船上貨物的貨主的委付而支付全部賠償,在其后由帆船船主提起的訴訟中,輪船的船主主張對方獲得的保險賠付應當在其承擔的賠償責任中予以抵扣。但法院駁回了這一主張,認為保險合同的存在是船主對第三方的保證,與侵害者無關,保險人并不是共同侵害人,因此從保險人那里獲得的賠償不應該減輕他人的責任。
而平行來源規則的理論根據,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為懲罰說,一為交易獲益說。根據懲罰說,盡管該規則可能使受害人雙重獲益,但基于對加害人的懲處之考慮,不能因此而減輕加害人的責任,因此該規則被某些法院視為對加害人的一種懲罰。但該說的缺陷在于懲罰性的責任在普通法上應僅限于欺騙、蓄意侵權等領域,而并不適用于大部分過失侵權案件。因此,某些法院轉而主張橫財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在有平行來源獲益時,法律選擇的結果不是使受害人得到橫財,就是使加害人獲得橫財,而使受害人因此而獲益明顯要公平得多。而交易獲益說則認為原告獲得的額外賠償是基于其事前的契約行為(保險合同)而獲益,屬于根據一般交易規則而獲得的,而不是基于侵權行為的發生而獲益,自然不能予以抵扣加害人的賠償。
在美國具有司法指導意義的權威學術解釋《侵權法第二次重述》中,該規則被闡述為:被告獲得的償還來自于或者受益于其他的來源,即為平行來源受益,這些受益沒有減輕被告賠償的效果。受到傷害的原告的凈損失可以相應的扣減,從這個程度上看,被告被要求承擔全部賠償數額可能會使受損的原告獲得雙倍的賠償,但是站在法律的立場看來,對于直接針對受害人的獲益不能轉化為加害人的橫財,如果原告是因為自己的原因而獲得這些利益(如獲得自己的保險補償),那么法律將允許其保留這些獲益;如果這些利益是源自第三方的贈與或者是法律的直接規定,那么他也不應該被剝奪這些利益。法律并不區分這些利益的性質,而只要它們不是源自被告或者被告的代理人。而最終的結論是,加害人應當對其造成的一切損害承擔賠償責任,而不僅僅限于受損方的凈損失。[5]從美國侵權法重述的觀點看,其對其他來源規則的理論糅合了橫財說與交易獲益說,其理論的核心是要加強對受害人的賠償,而另一方面看,則是要保持侵權責任的威懾效力。
但自美國的責任保險危機以來,平行來源規則被認為是加重了責任人的責任,而實際上是使保險公司承擔更大的責任,因此這場危機促使美國各州進行了侵權法改革,而平行來源規則即成為侵權法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截至2003年12月31日,共有23個州改革了平行來源規則。這23個州的改革分為三類:一類是完全廢除平行來源規則,允許法院予以扣減;另一類是限制該規則的適用范圍,即將該規則的適用范圍限制在人壽保險、政府補償、勞工賠償等獲益來源;第三類則是設定損益相抵的限額,如伊利諾斯州規定扣除必須在25000美元以下,且不得扣除賠償額度的50%。此外還有些州,如夏威夷州是通過賦予保險人或者第三人以代位權來阻止受害人獲得雙重賠償,而亞利桑那州的改革并不是直接廢除該規則,而是授權陪審團在衡平的基礎上,考慮受害人的其他來源獲益,再決定加害人承擔的賠償額度。因此總體而言,美國仍有半數以上的州沒有改革其他來源規則,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亞與得克薩斯這樣的重要州,因此損益不相抵的原則在美國法上仍然延續其旺盛的生命力。
保險代位權的性質對當事人選擇的影響
保險金不適用損益相抵將導致兩種結果,一是受害人獲得保險金給付和侵權損害賠償,這在平行來源獲益為人壽保險金時最為常見,此時保險機制與侵權責任制度相安無事;另一個是保險人在給付保險金后取得保險代位權,可以向造成保險事故發生的責任人追償。而在兩大法系,保險代位權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這也影響了保險代位權的實際效用。
(一)債權法定讓與理論對當事人行使代位權的影響
在大陸法系各國,對于保險代位權的性質,通說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法定讓與。中國《保險法》第45條的規定同樣如此。債權法定讓與理論表明,當保險人對受害人給付保險金后,即在保險金額的范圍內取得受害人的一切權利,而不需要受害人向保險人轉移賠償請求權的意思表示。因此如果受害人再向加害人求償,加害人完全可以債權已法定轉移為抗辯理由,而主張減輕賠償。此時,一旦保險人怠于行使求償權,加害人將因此獲益。即便法院不支持加害人的這一抗辯理由,對于受害人在獲得保險金后又從加害人那里獲得的侵權賠償,保險人可在保險金給付額度內以不當得利為由請求受害人返還。因此,除非保險賠償不足以彌補受害人的損失,否則受害人在經由保險賠償而實現完全損害填補后,往往不會再向加害人主張侵權賠償。因為排除義憤因素,僅從經濟需求上考慮,受害人除了支付一筆訴訟支出和耗費相對長的時間等待訴訟結果,并承擔著敗訴的風險外,不會獲得任何多余的利益。因此債權法定轉移理論迫使獲得完全賠償的受害人不會再向加害人主張損害賠償,(考慮敗訴風險,獲得大部分賠償的受害人可能也不會通過再向加害人追償)。而當保險人行使保險代位權向加害人追償時,已完全喪失了加害人在精神上(義憤的情緒)和物質上(損害需要得到填補)的動力,保險人更加不會為了實現侵權責任制度的威懾功能而行使代位權。無論是營利的保險人還是不營利的社會保險機構,行使保險代位權的動力只在于通過行使保險代位權能否獲益,即在可能耗費的訴訟成本與行使代位權可能獲益之間進行比較,一旦前者超過后者與保險費(保險人獲得保險代位權并不會退還保險費)之和,保險人便會放棄行使代位權,從而使加害人事實上免責。最終,在大部分小額的侵權事故中,損害分擔實現了社會化,侵權責任的功能在保險存在的情況下被吞噬。

(二)程序代位理論對于當事人行使代位權的影響
在英美法系當中,保險代位權的性質上并不是以債權的法定轉移為基礎的實體代位,而是程序代位。程序代位的核心在于,保險人不能以自己的名義,而只能以被保險人的名義起訴,除非被保險人向保險人轉讓了其權利。[7]366因此在英美法系,由于保險人只能以被保險人的地位行使權利,該權利仍屬于被保險人,并不發生權利的轉移。換句話說,一旦被保險人在獲得保險賠付后繼續向加害人追償,由此獲得的侵權賠償,保險人不能以不當得利為理由請求返還。但如果被保險人的行為與其對保險人的義務不符,他將負責彌補因此引起的損失,即將獲得的超額賠償返還給保險人。對于訴訟費用的分擔,如果保險合同有約定,將按協議分擔;如果沒有協議,將按照各自在訴訟中的利益分擔。可見在普通法上,被保險人不須承擔應返還給保險人的那一部分賠償的訴訟成本,這一規則既有利于被保險人就保險未能填補的損害向加害人追償,也有利于實現侵權責任的威懾目的。而保險人考慮成本而放棄行使代位權的結果,將使被保險人獲益,而不是使加害人免責。
保險代位權下正義與效率的博弈
對于受害者而言,侵權責任既承擔了補償功能,也往往是法律設想的實現正義的工具。但保險代位權的出現使這一實現落空,受害者不再單純尋求從侵權責任制度中獲得損害救濟,而保險人也僅僅從效率的立場考慮實施保險代位權,一旦實施保險代位權缺乏效率,通過保險代位權來實現侵權責任的價值的設想將不可避免的落空。
(一)保險代位權的正義觀之落空
盡管保險代位權的法理基礎并不明朗,但從該權利產生于保險合同來看,應該是保險人基于損失補償原則所設。而隨著保險與侵權責任的相交,這一權利也為侵權法所看中,因為既然損害填補的功能已經由保險理賠實現,那么損害預防功能就恰好可由保險代位權來傳遞。但不幸的是,大陸法系對保險代位權的制度設計僅僅是從實體法上考慮,而沒有顧及程序法上訴訟成本分擔對保險代位權行使的影響。而就侵權責任的功能而言,應該是寧愿讓受害人獲得雙重補償,也不能讓加害人免責。就保險法來說,盡管作為保險代位基礎的損失補償原則是如此重要,但無論是從保險人還是從立法者的初衷看,都不會是寧愿加害人免責,也不愿受害人雙重獲益。但從保險代位制度實際運行的結果看,卻是寧愿讓加害人免責,也不能讓受害人雙重獲益。因此盡管法律將伸張(矯正)正義的使命交予保險人,但保險人在利益得失的衡量后選擇了效率,從而使侵權責任的功能徹底在保險制度面前落空。而英美法系的程序代位理論雖然使訴訟成本由保險人負擔,但保險人在決定是否行使代位權時,同樣要考慮訴訟成本因素。雖然普通法的保險代位制度鼓勵受害人對加害人追償,但考慮到敗訴的風險和其損失已經獲得填補,受害人向加害人追償的經濟動力也不足。因此最終,無論是在大陸法系,還是在英美法系,保險代位權都是極少行使的。
將損害遏制的希望寄托在保險代位權上,只能是立法者的一廂情愿。而且即便存在保險代位權,對行為人的威懾實際上也不大。而考慮到美國侵權責制度的運行成本高達54%,保險人,甚至法官都可能主張放棄行使保險代位權,從而與社會財富最大化這一美國侵權法的價值相吻合。在中國,保險代位權的行使也同樣如此,因此也不難理解某些保險公司在車險合同中的“霸王條款”。正是由于保險代位權行使的不易,才使某些保險公司要求被保險人首先向加害人追償,但由于保險公司并不承擔這部分的訴訟成本,因此這類“霸王條款”才凸現其不公平。
(二)保險代位權中的效率論
如果從保險人、受害人與法官的立場上考察,放棄行使保險代位權,對三方都是可以接受的。在保險人看來,他并沒有任何損失。因為保險代位權的存在與否,并不在保險費率的考慮范圍內,保險代位權的存在也不會降低保險費率。如果保險人行使保險代位權,將可能獲益,因為除了加害人的賠償填補保險金支出外,保險人還憑空獲得了保險費;如果保險人不行使保險代位權,他也沒有損失,保險金的支出早已與保險費率相聯系。從被保險人看來,其損失已有保險金填補。除非義憤的情緒,理智的被保險人都不會選擇再向加害人追償,因為這樣行為的結果,不僅會承擔敗訴的風險,而且訴訟成本的負擔可能會剝奪一部分其已經獲得的保險賠償。甚至對于法官來說,這種結果也是其樂于見到的。在事故損害發生后,法官更關心的是受害人損害有沒有得到填補,既然保險人已經做出了理賠,侵權責任的主要功能已經實現,沒有必要再深究。更何況這種深究需要保險人行使代位權來實現,而保險人在對成本效益的考慮后放棄了保險代位權,也易于將法官從繁重的案件負擔中解脫出來,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那些大額的或者受害人沒有保險的案件中去。因此,保險人放棄保險代位權,事實上使事故侵權的各方當事人都得到解脫,而各方的利益反而實現了一種平衡,侵權責任的功能與價值就在這種利益平衡下湮沒了。
在損害賠償的實現中,通過侵權責任獲得賠償的不易,使受害人只能選擇保險作為賠償方式。這種不易也促使保險人在考慮成本效益后,放棄保險代位權。放棄的結果是,在保險足以填補事故損害的情況下,侵權責任制度被徹底架空。因此如果侵權責任制度要實現其功能,必須在實體法與程序法上做出改革,但受制于矯正正義的價值目標,侵權責任只能通過這種方式(構成要件、訴訟成本)運行,但擁有保險的人無須再經過侵權訴訟的煎熬,便可有效率地獲得救濟。因此人們選擇保險,而不選侵權責任,是侵權責任制度自身缺陷造成的,且侵權法自身無法克服這種缺陷。只有當保險不足以填補受害人損失時,受害人才會被迫求助于侵權責任制度,人們選擇保險制度而非侵權制度,完全是擇優的結果。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