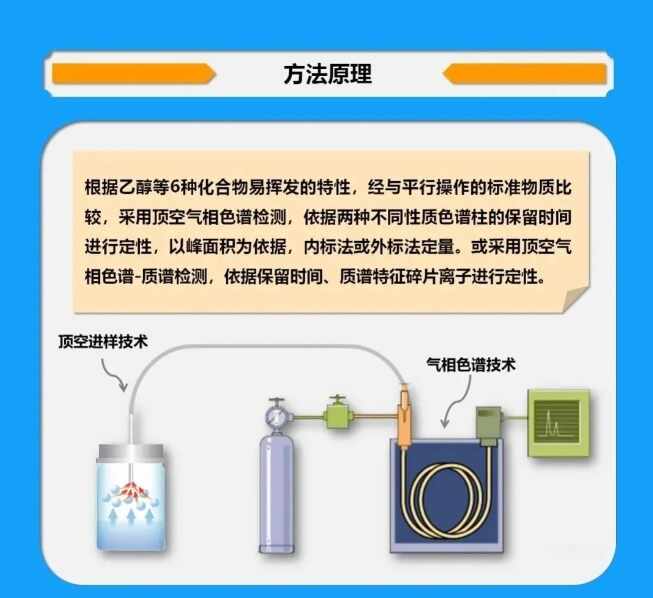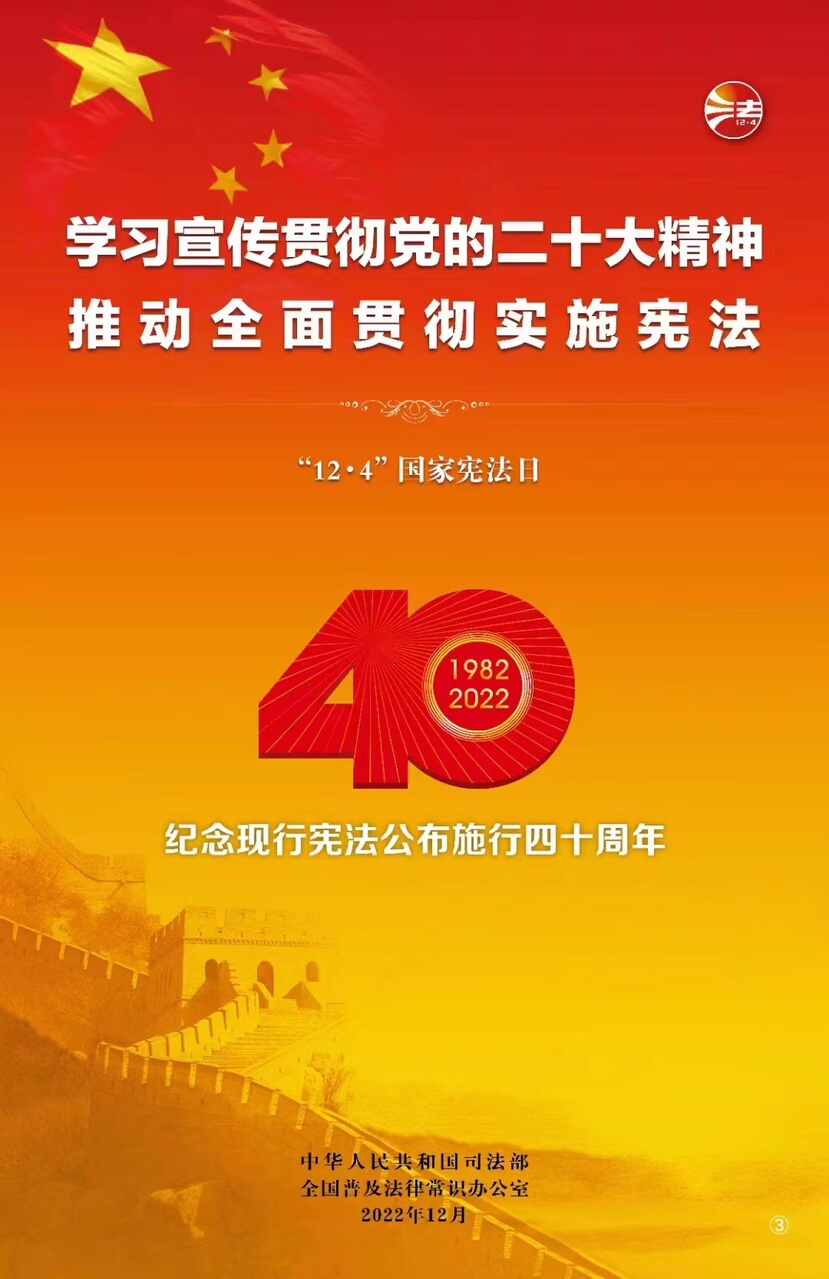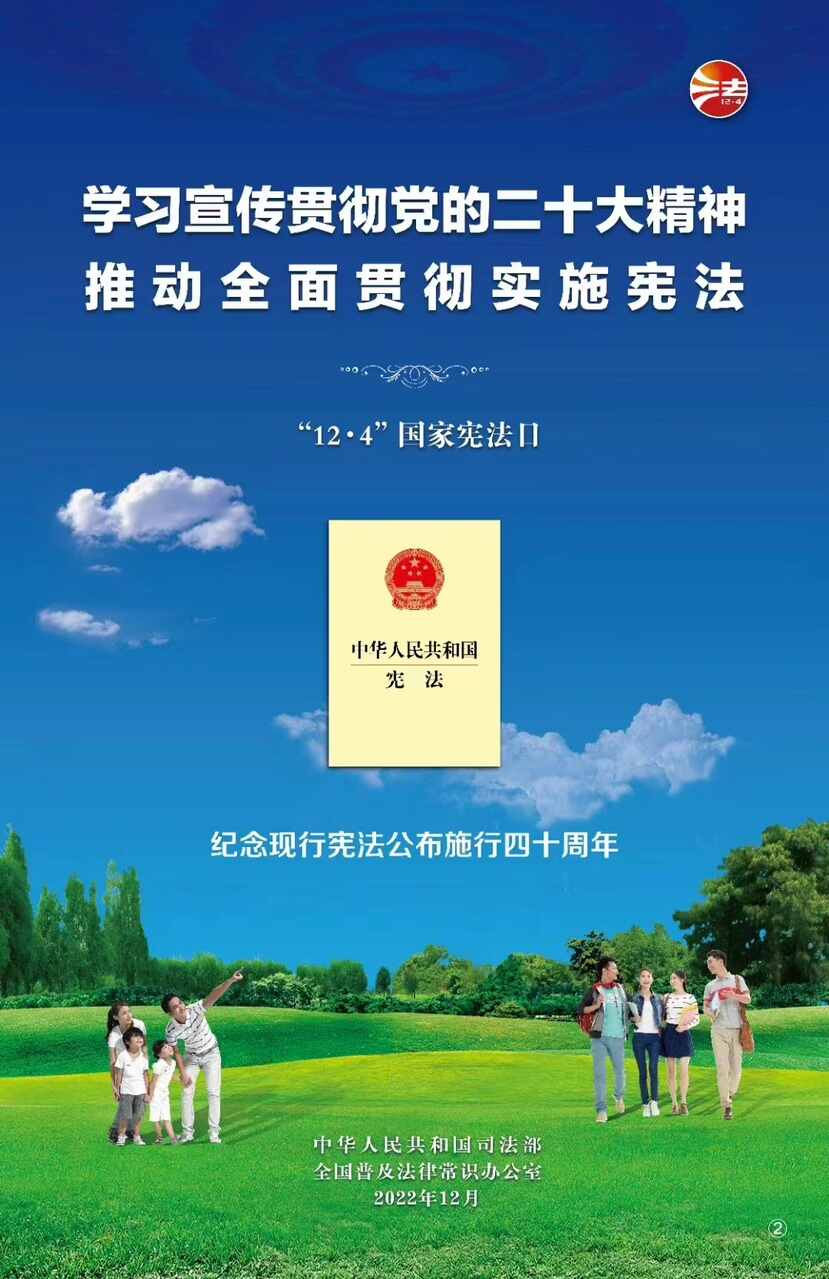冒充國家工作人員實施合同詐騙
 邢穎律師2021.12.24127人閱讀
邢穎律師2021.12.24127人閱讀
導讀:
第三種意見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偽造印章罪與合同詐騙罪數罪。本案中劉某的行為致使被害人損失達22萬元人民幣,合同標的額40萬元人民幣可以作為量刑情節,屬于數額特別巨大;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詐騙,嚴重損害國家機關的威信和形象,屬情節嚴重,此時,招搖撞騙罪的法定刑明顯低于合同詐騙罪,也可以說不能反映出行為人的行為應受的懲罰,所以應適用重法優于輕法的原則,構成合同詐騙罪。那么冒充國家工作人員實施合同詐騙。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第三種意見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偽造印章罪與合同詐騙罪數罪。本案中劉某的行為致使被害人損失達22萬元人民幣,合同標的額40萬元人民幣可以作為量刑情節,屬于數額特別巨大;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詐騙,嚴重損害國家機關的威信和形象,屬情節嚴重,此時,招搖撞騙罪的法定刑明顯低于合同詐騙罪,也可以說不能反映出行為人的行為應受的懲罰,所以應適用重法優于輕法的原則,構成合同詐騙罪。關于冒充國家工作人員實施合同詐騙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案情:2003年6月,劉某自稱是某省公安廳十七處的會計,并受該處處長王某的委托到甲地購買柚子。同年7月,劉某到甲地與當地老板宋某簽訂了一份買賣合同,合同約定由某省公安廳十七處向宋某購買柚子20萬斤,單價每斤2元。合同上蓋有“某省公安廳合同專用章”,簽約后,宋某按合同約定交付了20萬斤的柚子,但劉某一直未兌付貨款。宋某經多次催款,而劉某均以種種理由拒付。于是宋某向公安機關報案。經查:某省公安廳根本沒有十七處這個機構設置,公安廳在編人員中也沒有王處長和劉某(會計),“某省公安廳合同專用章”系其偽造的印章,實際造成宋某損失達22萬元人民幣。
分歧意見:本案對劉某的行為如何定性主要存在以下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招搖撞騙罪。第三種意見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偽造印章罪與合同詐騙罪數罪。第四種意見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偽造印章罪與招搖撞騙罪數罪。
評析: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其理由如下:
首先,要區分劉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還是招搖撞騙罪。本案中劉某的行為既符合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成,又符合招搖撞騙罪的犯罪構成,但行為人主觀上只有一個犯罪故意,客觀上也只實施了一個犯罪行為,其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合同詐騙也只是為了騙取財物,沒有涉及其他利益,因此本案是由犯罪手段而形成的法條競合。而根據刑法理論,在法條競合的情況下應遵循特別法?特別條款?優于普通法?普通條款?的原則。但也有例外,即當特別條款的法定刑明顯低于普通條款的法定刑時,根據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這時就應該按照重法優于輕法的原則處理。本案中劉某的行為致使被害人損失達22萬元人民幣,合同標的額40萬元人民幣可以作為量刑情節,屬于數額特別巨大;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詐騙,嚴重損害國家機關的威信和形象,屬情節嚴重,此時,招搖撞騙罪的法定刑明顯低于合同詐騙罪,也可以說不能反映出行為人的行為應受的懲罰,所以應適用重法優于輕法的原則,構成合同詐騙罪。
其次,再分析劉某偽造印章用于合同詐騙是否應當數罪并罰。從表面上看,劉某實施了兩個行為,構成數罪,實際上劉某的行為屬于牽連犯的范疇。對于牽連犯,除非刑法分則規定應實行數罪并罰的以外,一般適用從一重處罰的原則,顯然,合同詐騙罪法定刑重于偽造印章罪。本案不應當數罪并罰,而是根據從一重處罰的原則,以合同詐騙罪定罪,偽造印章行為可作為量刑情節。

需要說明的是,關于合同詐騙罪目前只能參照?沒有其他相關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1996第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個人詐騙公私財物20萬元以上的,屬于數額特別巨大”來定罪量刑。但合同詐騙罪是1997年刑法修訂增加的新罪名,對合同詐騙罪規定的數額也理應要高于普通詐騙罪,因此,這種犯罪數額的大小或犯罪情節的輕重的不同會造成最終適用刑罰的不同的情形,應由有關司法解釋予以完善。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