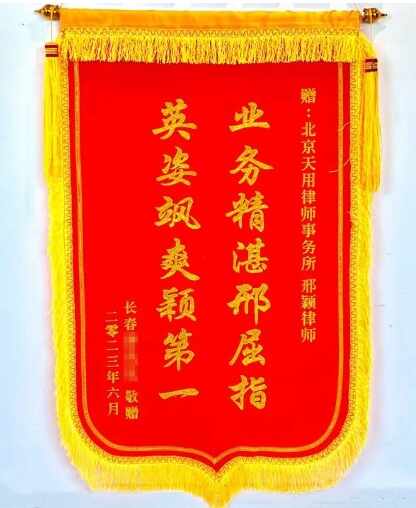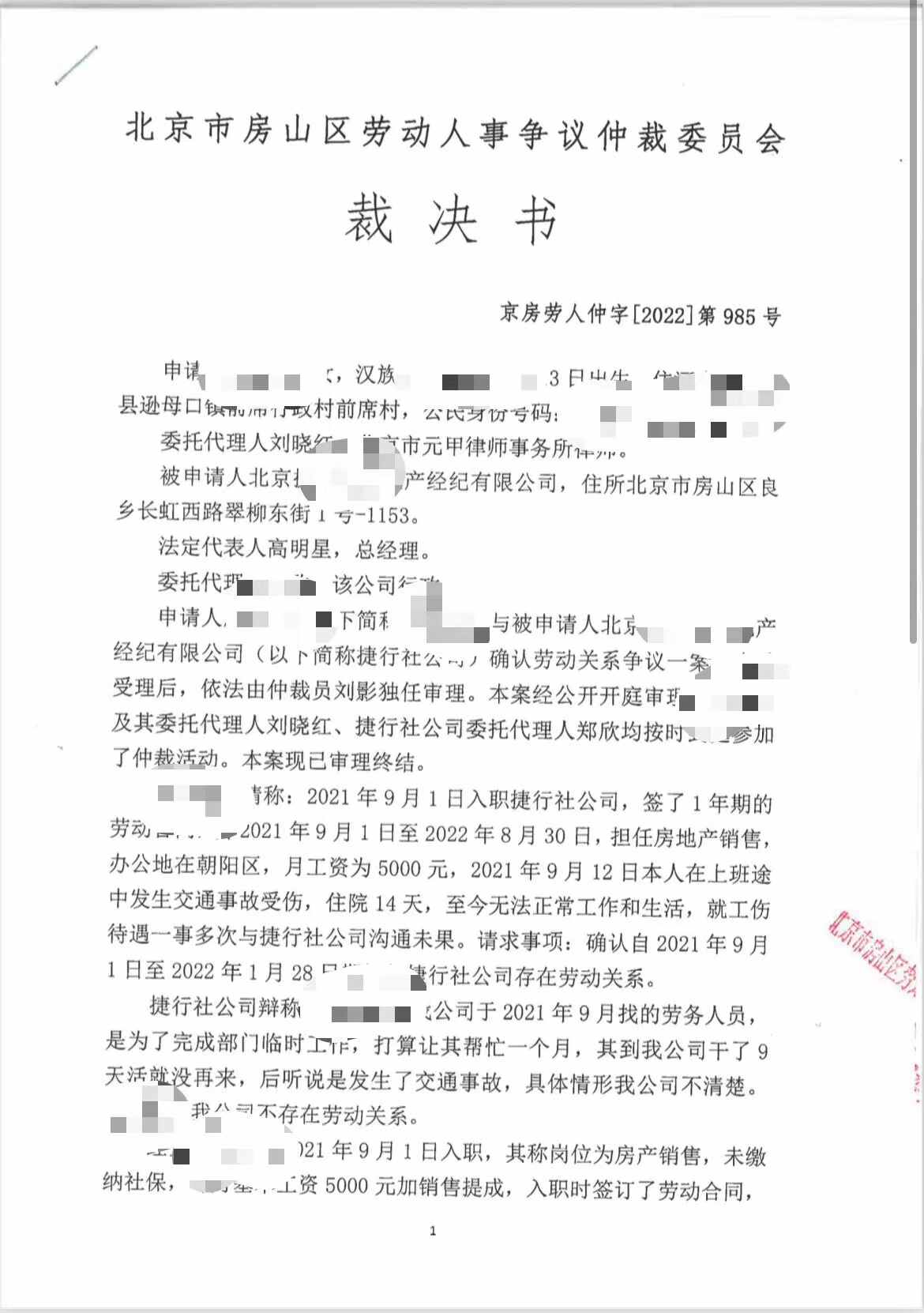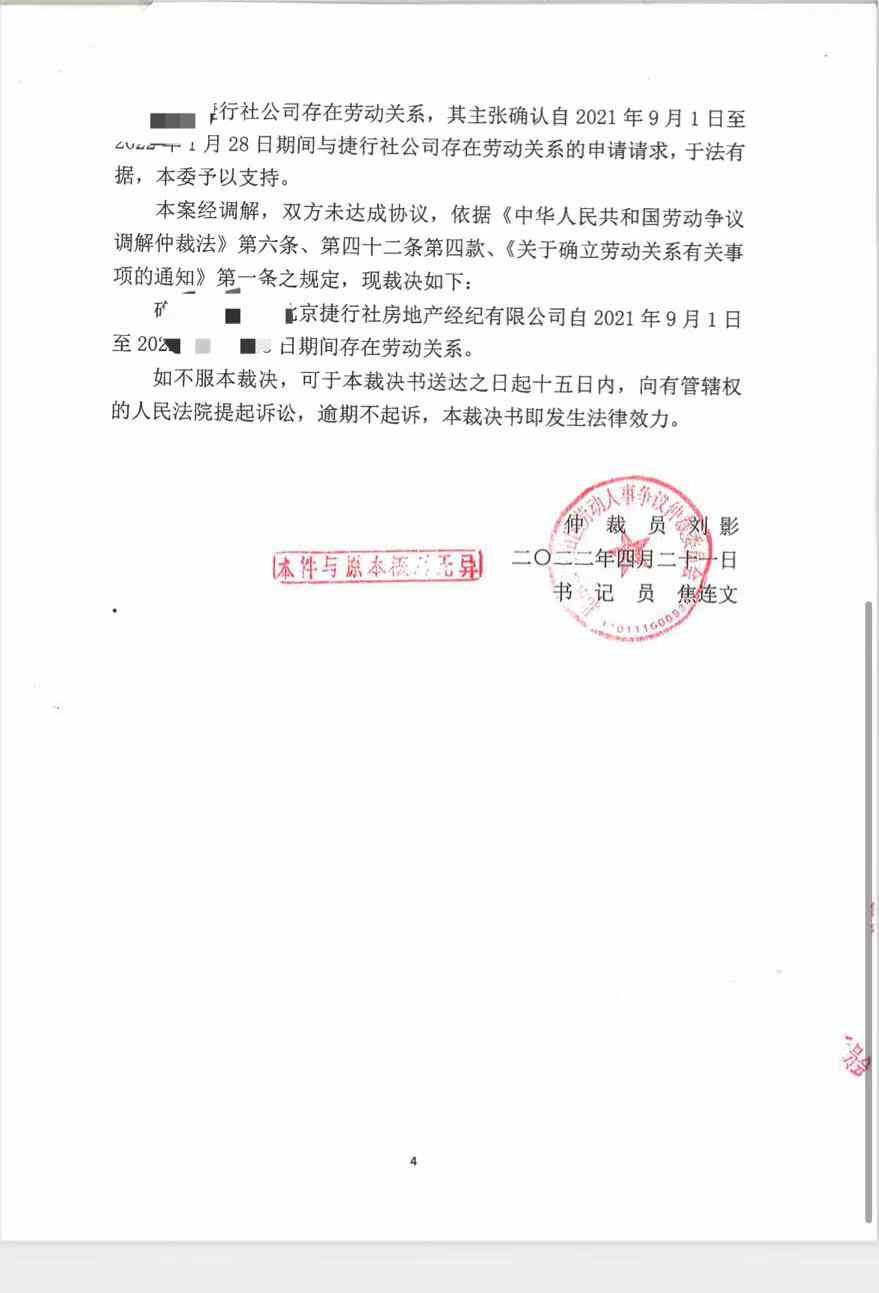臨時工與單位所簽集資建房合同效力認定
 姚平律師2021.12.23852人閱讀
姚平律師2021.12.23852人閱讀
導讀:
對單位職工而言,集資房具有一定的政策福利性。因此,從集資建房協議的主要權利義務看,其屬于附生效及解除條件的買賣合同。集資房所涉土地使用權及房改和產權登記上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體現的政策福利性,容易產生合同性質認定上的分歧。其二,本案中的集資建房協議無阻卻生效事由,依法具有法律效力。雙方爭議的焦點在于,涉案集資房所占用的國有劃撥土地及原告的臨時工身份是否影響協議的效力。但從原告的臨時工身份及相關人事制度和政策,并結合集資房占用的國有劃撥土地這一資產來看,還有待進一步的分析和考量。那么臨時工與單位所簽集資建房合同效力認定。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對單位職工而言,集資房具有一定的政策福利性。因此,從集資建房協議的主要權利義務看,其屬于附生效及解除條件的買賣合同。集資房所涉土地使用權及房改和產權登記上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體現的政策福利性,容易產生合同性質認定上的分歧。其二,本案中的集資建房協議無阻卻生效事由,依法具有法律效力。雙方爭議的焦點在于,涉案集資房所占用的國有劃撥土地及原告的臨時工身份是否影響協議的效力。但從原告的臨時工身份及相關人事制度和政策,并結合集資房占用的國有劃撥土地這一資產來看,還有待進一步的分析和考量。關于臨時工與單位所簽集資建房合同效力認定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案情】
原告李某1995年中專畢業后到被告某水利建筑勘察設計院工作(無正式人事編制)。1997年被告為了改善職工福利,決定以集資建房形式建職工宿舍樓。同年8月19日,原、被告雙方簽訂集資建房協議書一份,對住房面積、集資款額、住房分配辦法和房改等內容進行了約定。此后原告依約取得訴爭房屋居住至今。1998年6月至同年底,被告為其他集資戶相繼辦理了房改和產權登記,但一直以原告無正式人事編制為由,拒絕為其辦理。2009年4月原告訴訟來院,要求被告按集資建房協議的約定辦理房改及產權登記手續。
【分歧】
對本案的處理有兩種觀點。第一種是,涉案集資房仍屬于國有資產,是否能為原告辦理房改和產權登記,須由被告的主管部門及有關部門審批決定。對原告的訴訟請求應予駁回。第二種觀點是,本案中的集資建房協議有效,被告以原告無正式人事編制為由實行區別對待的做法,違反了誠實信用的合同法原則。應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
【評析】

筆者傾向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其一,集資建房協議屬于附條件的房屋買賣合同。集資房即政策性住房,是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等組織為了解決內部職工的住房問題,以國家劃撥的土地建設并按成本價出售給內部職工的房屋。集資房是我國城鎮住房制度改革轉型時期的特定產物。集資房的建設,一般由單位以國有劃撥土地報經主管及相關政府部門批準后,以核算的建筑成本收取內部職工的集資款項,并由單位作為發包方與建筑施工企業簽訂施工合同,待房屋竣工驗收合格后按集資建房方案移交給內部職工。對單位職工而言,集資房具有一定的政策福利性。其福利性主要體現在集資房的建設用地屬于國有劃撥土地,只需支付少量的土地使用費,而普通商品房建設用地則需交納大額的土地出讓金。這也是早期的房主對集資房只享有部分產權的原因所在。隨著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這類住房經第二次房改后,房主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產權所有者。從一般的集資建房協議來看,其主要內容包括兩部分,一是有關住房面積、集資款額及繳納時間、住房分配辦法的約定。二是有關前提性條件和房改的約定,如:職工此前享有其他政策性福利住房的,必須騰退后才能購買新的集資房;職工不愿意參與房改的,則退出所購的集資房;等等。因此,從集資建房協議的主要權利義務看,其屬于附生效及解除條件的買賣合同。職工在交納全部集資款并滿足所附生效條件后(如騰退其他政策性福利住房),集資建房協議生效,單位須履行交付集資房的義務。如果職工拒絕參與房改,則合同所附的解除條件成就,產生雙方互返財產的法律后果。集資房所涉土地使用權及房改和產權登記上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體現的政策福利性,容易產生合同性質認定上的分歧。事實上,參照高法《關于審理涉及國有土地使用權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約定提供資金的當事人不承擔經營風險,只分配固定數量房屋的,應當認定為房屋買賣合同”,也宜認定本案中的集資建房協議屬于房屋買賣合同。
其二,本案中的集資建房協議無阻卻生效事由,依法具有法律效力。雙方爭議的焦點在于,涉案集資房所占用的國有劃撥土地及原告的臨時工身份是否影響協議的效力。從合同法的角度看,因集資房建設方案事先經過了被告主管及相關政府部門的審批,集資房的出售不構成對國有劃撥土地的無權處分,該協議的生效沒有實質性的法律障礙。但從原告的臨時工身份及相關人事制度和政策,并結合集資房占用的國有劃撥土地這一資產來看,還有待進一步的分析和考量。在我國,事業單位的社會公益性決定了其與政府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政府與事業單位的關系,從政策調控到財政保障或補貼、土地劃撥直至人事安排,幾乎無所不包。這其中也包括與本案相關的職工編制問題。按通行有效的做法,編內人員享受相關政策福利和保障、編外人員不享受或只享受少部分利益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被告認為,本案中的集資房事關職工重大福利,沒有主管及相關部門的審批,單位無權決定臨時工可以享受這一福利。顯然,被告忽略了另一個事實,即,臨時工能否享受及享受福利的多少,在不違反法律和相關政策的前提下,單位有權根據實際情況自主決定。而本案訴爭的集資建房協議,正是集資建房方案報經被告的主管及相關政府部門審批同意后,被告在本單位具有人事編制的“正式職工”有房可居或不愿意購買的情況下,自主決定將剩下的一套集資房(即本案訴爭住房)出售給了原告。根據199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城鎮公有住房,除政府認為不宜出售的外,均可向城鎮職工出售”。因此,本案中的集資建房協議符合我國城鎮住房制度的改革政策,也契合了同工同酬的勞動合同法宗旨,依法具有法律效力。
作者: 肖樂新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