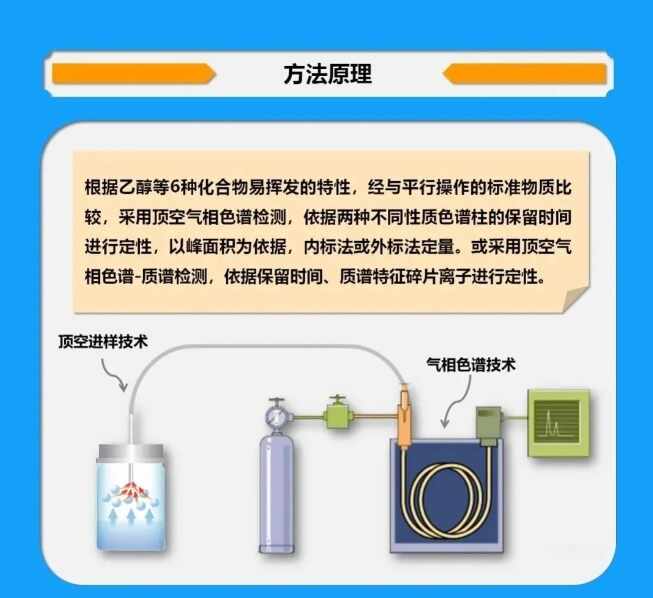中國有關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的規(guī)定和實踐
 吳夢云律師2021.12.08438人閱讀
吳夢云律師2021.12.08438人閱讀
導讀:
在1985年以前,中國尚無任何與仲裁條款獨立性有關的立法規(guī)定,《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在仲裁領域?qū)嶋H上充當了法律的角色,起著先導的作用。那么中國有關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的規(guī)定和實踐。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在1985年以前,中國尚無任何與仲裁條款獨立性有關的立法規(guī)定,《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在仲裁領域?qū)嶋H上充當了法律的角色,起著先導的作用。關于中國有關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的規(guī)定和實踐的法律問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債權(quán)債務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中國有關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的規(guī)定和實踐
(一)法律和仲裁規(guī)則
中國涉外仲裁機構(gòu)成立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受制于國家實行的對外政策,受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不多,對仲裁的理論研究也十分薄弱。在1985年以前,中國尚無任何與仲裁條款獨立性有關的立法規(guī)定,《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在仲裁領域?qū)嶋H上充當了法律的角色,起著先導的作用。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實行開放政策,中國涉外仲裁機構(gòu)的受案量急劇增加的情況下,中國涉外仲裁機構(gòu)也尚未充分意識到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在涉外仲裁中的重要地位,以致在1989年修訂仲裁規(guī)則時未能對仲裁條款的獨立性原則作出全面的規(guī)定。以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此間制定的仲裁規(guī)則為例,1956年《暫行規(guī)則》自不必說,1989年《仲裁規(guī)則》也沒有明確涉及這一問題,僅在第2條第3款規(guī)定:“仲裁委員會有權(quán)就仲裁協(xié)議的有效性和仲裁案件的管轄權(quán)作出決定。”(注:對于該規(guī)定,有人認為“隱隱約約接近獨立性理論的邊緣”,但“反應遲鈍”。參見宋連斌著:《國際商事仲裁管轄權(quán)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頁。)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國有關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的立法始于1985年。是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jīng)濟合同》第35條明確規(guī)定:“合同約定的解決爭議的條款,不因合同的解除或終止而失去效力。”該條雖然沒有明確規(guī)定了仲裁條款的獨立性,但因“解決爭議的條款”自然應包括“仲裁條款”,所以該條至少承認,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等解決爭議的條款與合同中有關當事人實體權(quán)利義務的條款在性質(zhì)上是不同的,它在合同解除或終止的情形下依然有效。但是也應看到,該條只規(guī)定了合同解除或終止情形下仲裁條款單獨有效,而沒有規(guī)定合同自始無效或不存在情形下仲裁條款單獨有效這一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中的核心問題,所以只是部分地采納了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
“導致合同無效的原因?qū)τ谥俨脜f(xié)議獨立性理論至關重要。”[14]如果合同自始有效,只是合同是否繼續(xù)有效存在爭議,這種情況下,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獨立于主合同而單獨有效當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主合同合同自始無效,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是否獨立于無效的主合同而單獨有效,在理論上存在爭議。鑒于此,1994年8月31日公布的《仲裁法》第19條第1款規(guī)定:“仲裁協(xié)議獨立存在,合同的變更、解除、終止或者無效,不影響仲裁協(xié)議的效力。”顯然,該規(guī)定也未就合同自始無效或不存在情況下仲裁條款的獨立性作出規(guī)定。而此前曾一度被個別學者認為“反應遲鈍”的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則迅速作出回應,在《仲裁法》頒布之前,于1994年3月7日修訂并通過了《仲裁規(guī)則》,并率先對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作出了并不全面的“擴充性解釋”。該規(guī)則第5條規(guī)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應視為與合同的其他條款分離地、獨立地存在的條款,附屬于合同的仲裁協(xié)議也應視為與合同其他條款分離地、獨立地存在的一個部分;合同的變更、解除、終止、失效或無效,均不影響仲裁條款或仲裁協(xié)議的效力。”但《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與《仲裁法》一樣,也沒有規(guī)定合同自始無效或不存在情況下仲裁條款是否有效的問題。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意識到這一缺陷,在1995年修訂其《仲裁規(guī)則》時,超越《仲裁法》之相關規(guī)定增補了這方面的內(nèi)容。1995年《仲裁規(guī)則》第5條規(guī)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應視為與合同其他條款分離地、獨立地存在的條款,附屬于合同的仲裁協(xié)議也應視為與合同其他條款分離地、獨立地存在的一部分;合同的變更、解除、終止、失效或無效以及存在與否,均不影響仲裁條款或仲裁協(xié)議的效力。”該《仲裁規(guī)則》后又經(jīng)1988年、2000年兩次修訂,第5條之規(guī)定除刪除“附”字外,其他一如1995年《仲裁規(guī)則》之規(guī)定。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對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的認識過程和認可程度也大致如此,其1994年《仲裁規(guī)則》、1995年《仲裁規(guī)則》、1998年《仲裁規(guī)則》和2000年《仲裁規(guī)則》之第5條與同期的《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第5條之規(guī)定完全相同。
應該說,自中國兩個涉外仲裁機構(gòu)的1995年《仲裁規(guī)則》第5條全面規(guī)定了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的要義以來,中國涉外仲裁實踐在仲裁條款獨立性的規(guī)制上與國際通行作法已趨于一致,但由于我國《仲裁法》并沒有規(guī)定合同自始無效或不存在情形下仲裁條款的有效性問題,因而《仲裁法》和《仲裁規(guī)則》之間有關該原則的矛盾和沖突業(yè)已存在。在法院對仲裁的充分支持態(tài)度尚未從法律規(guī)定完全變成實際行動的現(xiàn)實背景下,如何化解和協(xié)調(diào)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就成為一個現(xiàn)實難題。從法理上講,《仲裁法》是國家的法律,《仲裁規(guī)則》不具有法律的性質(zhì),《仲裁規(guī)則》應該服從于《仲裁法》,不得與之相抵觸,因此《仲裁規(guī)則》的有關規(guī)定明顯違法。從學理和實踐上講,《仲裁規(guī)則》的有關規(guī)定又具有科學性,與國際上通行的實踐也相一致,因而應予肯定和采納。客觀地看,修改《仲裁法》的有關規(guī)定,使其與《仲裁規(guī)則》一致,當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二)司法實踐
中國法院對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理解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
自實行開放政策至《仲裁法》生效(1995年9月1日)以前,我國法院基于“欺詐毀滅一切”的理念,對以欺詐方法訂立的仲裁條款的有效性持否定態(tài)度,即因欺詐而自始無效的合同,其仲裁條款無效。1988年10月11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中國技術(shù)進出口公司(下稱中技公司)訴瑞士工業(yè)資源公司(SwissIndustrialResourcesCompanyInc.,下稱IRC)侵權(quán)損害賠償上訴案”[15]的判決中認定:“上訴人(IRC——引者注)利用合同形式進行欺詐,已經(jīng)超出了履行合同的范圍,不僅破壞了合同,而且構(gòu)成了侵權(quán)。雙方當事人的糾紛,已非合同權(quán)利義務的爭議,而是侵權(quán)損害賠償糾紛。被上訴人(中技公司——引者注)有權(quán)向法院提起侵權(quán)之訴,而不受雙方當事人訂立的仲裁條款的約束。”顯然,法院對此案的處理,是以主合同自始無效以及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無效為前提的。這也就是說,通過欺詐訂立的合同自始無效,自始無效合同中的仲裁條款也應無效。
該案主要案情如下:1985年4月1日,受浙江省溫州市金屬材料公司委托,中國技術(shù)進出口公司(簡稱中技公司)與瑞士工業(yè)資源公司(簡稱IRC)簽訂了購買9180噸鋼材的合同。合同總價229.5萬美元,價格條件C&F溫州,IRC收到信用證兩周內(nèi)在意大利的拉斯佩扎港交貨。1985年4月19日,中技公司按照合同的規(guī)定通知中國銀行上海分行開出金額229.5萬美元、以IRC為受益人的信用證。信用證中載明交貨期限不得遲于1985年5月5日,不得分批裝運,運輸途中不得轉(zhuǎn)船。5月29日,中技公司收到IRC通過銀行轉(zhuǎn)來的全套議付單據(jù),其中包括由IRC開具的交貨實際金額為229.5萬美元的商業(yè)發(fā)票、提單、裝船明細單、重量、質(zhì)量證書等單據(jù)。提單是5月4日簽發(fā)的,托運人為IRC,承運貨物的船舶為“阿基羅拉”號。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審查后,單證相符,遂于6月1日將229.5萬美元實施對外付款。在通常情況下,中技公司應在7、8月份收到貨物,但直到10月底,中技公司仍未收到這批貨物。其間,中技公司多次電傳對方催詢和查找貨物下落,IRC或不予答復,或以“船舶改變航線”,或“已調(diào)整航程”等借口予以搪塞。后中技公司派人赴意大利進行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IRC提供的全套議付單據(jù)均系偽造,合同項下的貨物從未在拉斯佩扎港裝上“阿基羅拉”,且“阿基羅拉”1985年也未停泊過拉斯佩扎港。于是,中技公司于1986年3月24日向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IRC提起侵權(quán)損害賠償之訴,并申請對IRC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另一筆托收貨款440.8萬美元實施保全措施。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經(jīng)審理后于1988年5月11日作出判決:IRC賠償中技公司鋼材貨款、銀行利息、經(jīng)營損失、法律訴訟費等共計5136668.6美元。IRC不服此判決,于1988年7月11日上訴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其上訴理由之一就是雙方當事人之間訂立的鋼材買賣合同中規(guī)定有通過仲裁方式解決合同糾紛的條款,原審法院對此案無管轄權(quán)。1988年10月11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人IRC的上訴,維持原判。該判決作出后,引發(fā)了我國仲裁法學界對合同自始無效情形下仲裁條款是否單獨有效問題的爭論。一種觀點認為,“中技公司與IRC公司之間的《合同議定書》是IRC公司使用欺詐手段而訂立的,該合同自始無效,因此其中包含的仲裁條款也就隨之無效。”[16](注:在該書2000年修訂本中,作者已經(jīng)放棄了這一觀點。作者認為:“總的來說,以欺詐或侵權(quán)等理由否定仲裁協(xié)議的有效性,進而排除仲裁管轄權(quán),無論從中國內(nèi)地立法看,還是從中國已經(jīng)參加的國際公約看,都是缺少依據(jù)的。”韓健著:《現(xiàn)代國際商事仲裁法的理論與實踐》(修訂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頁。)其理論依據(jù)是:仲裁條款與合同之間存在密切聯(lián)系,影響合同效力的因素,往往也要影響仲裁條款的效力。在本案中,由于仲裁條款的訂立與合同的訂立同時進行,所以難以想象,在訂立合同時存在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的情況下,仲裁條款的訂立是自由意思的表示。試想,如果中技公司能獲得IRC真實情況,它會與IRC進行談判而締結(jié)任何合同嗎?因此,本案中的仲裁條款純屬欺詐行為的產(chǎn)物,人民法院有充分的根據(jù)宣布仲裁條款無效。[17]另一種觀點認為,“盡管中技公司與IRC之間訂立的合同是IRC通過欺詐方式訂立的自始無效的合同,但該合同約定的通過仲裁方式解決合同爭議的條款不一定就是欺詐行為的產(chǎn)物。仲裁條款既然可以獨立存在,即使合同訂立時一方當事人有欺詐行為,但雙方在談判仲裁解決合同爭議條款的問題上,應該是當事人雙方共同的意思表示,雙方同意將合同項下的一切爭議,包括合同的有效性及雙方當事人權(quán)利義務等爭議,通過仲裁方式而不是通過法院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說,仲裁條款不是欺詐的產(chǎn)物。它可以脫離主合同,包括自始無效的主合同而存在。”[18][page]
公允地講,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的處理并無不妥。因為,1988年法院在審理該案時,當時實行的1985年《涉外經(jīng)濟合同法》第35條只承認合同解除、終止時,仲裁條款仍然有效,并沒有規(guī)定自始無效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單獨有效,且最高人民法院也沒有相關的司法解釋,在我們這個只承認制定法不承認判例法的國家,嚴格依法辦事是司法活動所應恪守的原則,法院(法官)無權(quán)憑借其對法律的誠摯理解和良好的法學素養(yǎng)自由裁量。因此,任何將此案置于當今法制背景下進行的否定性評析,都有失公允,除具有些許學術(shù)價值外,免不了“事后諸葛亮”的嫌疑。
1995年9月1日后,我國法院遵循《仲裁法》之規(guī)定,對因欺詐而自始無效的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的有效性持肯定態(tài)度。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蘇省物資集團輕工紡織總公司訴(香港)裕億集團有限公司、(加拿大)太子發(fā)展有限公司侵權(quán)損害賠償糾紛上訴案”[19]中首次確認:即使當事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施行侵權(quán)行為,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并不因此無效。在該案中,江蘇省物資集團輕工紡織總公司(下稱輕紡公司)與(香港)裕億集團有限公司(下稱裕億公司)于1996年5月5日簽定CC960505號銷售合同,約定由裕億公司銷售普通舊電機5000噸給輕紡公司,每噸348.9美元。同年5月6日,輕紡公司與(加拿大)太子發(fā)展有限公司(下稱太子公司)簽訂了CC960506號銷售合同,約定由太子公司銷售普通舊電機5000噸給輕紡公司,每噸348.9美元。上述兩份合同第8條均明確規(guī)定:“凡因執(zhí)行本合同所發(fā)生的或與本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雙方可以通過友好協(xié)商解決;如果協(xié)商不能解決,應提交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根據(jù)該會的仲裁規(guī)則進行仲裁。仲裁裁決是終局的,對雙方均有約束力。”貨物到港后,經(jīng)商檢查明:貨物總重量為9586.323噸,“本批貨物主要為各類廢結(jié)構(gòu)件、廢鋼管、廢齒輪箱、廢圓鋼等”。輕紡公司遂以裕億公司和太子公司侵權(quán)給其造成損失為由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裕億公司和太子公司在法定的答辯期內(nèi)提出管轄權(quán)異議稱,本案當事人之間對合同糾紛已自愿達成仲裁協(xié)議,人民法院依法不應受理。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是因欺詐引起的侵權(quán)損害賠償糾紛。雖然原告輕紡公司和被告裕億公司、太子公司之間的買賣合同中訂有仲裁條款,但由于被告是利用合同進行欺詐,已超出了履行合同的范圍,構(gòu)成了侵權(quán)。雙方當事人的糾紛已非合同權(quán)利義務的爭議,而是侵權(quán)損害賠償糾紛。輕紡公司有權(quán)向法院提起侵權(quán)之訴,而不受雙方訂立的仲裁條款的約束。裕億公司、太子公司所提管轄權(quán)異議,理由不能成立。”據(jù)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裕億公司、太子公司對該案管轄權(quán)提出的異議。一審宣判后,裕億公司、太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裕億公司、太子公司訴稱:輕紡公司訴訟狀中的案由沒有事實予以支持,其故意混淆侵權(quán)責任和合同責任,企圖規(guī)避法律規(guī)定和合同約定。根據(jù)案件內(nèi)容,本案案由應為合同糾紛。當事人之間對合同糾紛已自愿達成仲裁協(xié)議,依照法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不應受理此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程序?qū)徖磉^程中,未經(jīng)實體審理,就對輕紡公司指控裕億公司和太子公司進行“欺詐”的訴訟請求作出認定,是違法裁定。故請求撤銷原審裁定,裁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案。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從輕紡公司在原審起訴狀中所陳述的事實和理由看,其所述裕億公司和太子公司的侵權(quán)行為,均是在簽訂和履行CC960505號和CC960506號合同的過程中發(fā)生的,同時也是在《仲裁法》實施后發(fā)生的。兩份合同的第8條規(guī)定有仲裁條款,根據(jù)《仲裁法》和《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guī)則》的有關規(guī)定,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委員會有權(quán)受理侵權(quán)糾紛,因此本案應通過仲裁解決,人民法院無管轄權(quán),遂裁定撤銷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裁定。
值得注意的是,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一審中的裁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前述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公布的裁定的制約或影響——殊不知“時過境遷”,《仲裁法》已經(jīng)生效,適才有了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銷的結(jié)果。在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裁定中,依稀可見法院與仲裁機構(gòu)競爭案件管轄權(quán)的傾向甚或?qū)ι嫱庵俨萌狈π湃蔚那榫w,且它們并沒有因為《仲裁法》的生效而有太大的改變。是故,切實實施《仲裁法》規(guī)定的仲裁條款獨立性原則,給涉外仲裁一個原本屬于它的生存和發(fā)展空間,的確還需要法院和法官轉(zhuǎn)變觀念。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