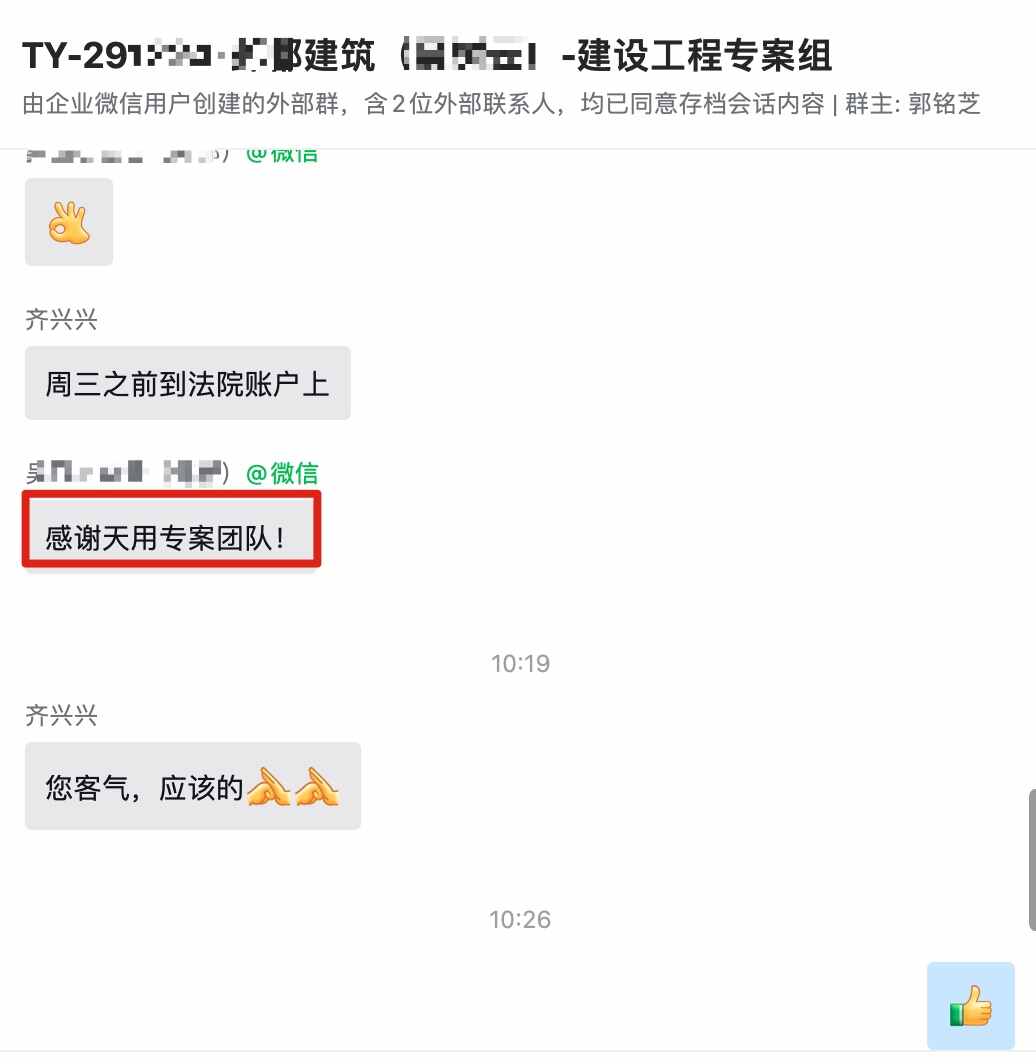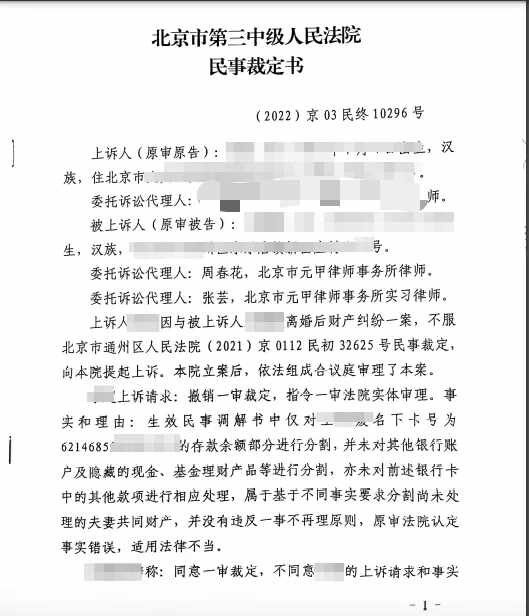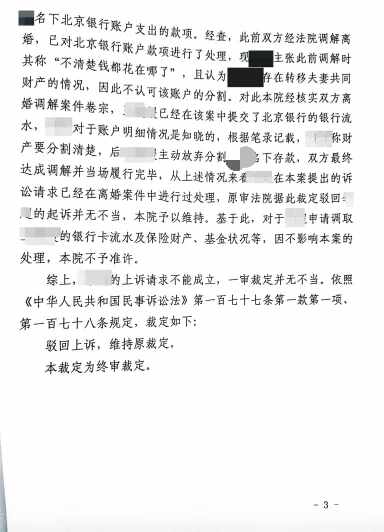艱難的勝訴之路
 崔玉君律師2021.12.08976人閱讀
崔玉君律師2021.12.08976人閱讀
導讀:
艱難的勝訴之路——解讀A公司訴B公司投資款糾紛案歷時近6年,歷經一審、2次再審、2次申訴、抗訴及發回重審,歷經被告人B公司法人資格的注銷、撤銷注銷、行政復議及確認其訴訟主體資格,原告A公司終于贏得了200萬元投資款官司。歷時近六年的馬拉松訴訟,暫時劃上了句號。因B公司拒不領取法律文書,下落不明,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已公告送達判決書,此案將于2004年3月8日上訴期滿。那么艱難的勝訴之路。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艱難的勝訴之路——解讀A公司訴B公司投資款糾紛案歷時近6年,歷經一審、2次再審、2次申訴、抗訴及發回重審,歷經被告人B公司法人資格的注銷、撤銷注銷、行政復議及確認其訴訟主體資格,原告A公司終于贏得了200萬元投資款官司。歷時近六年的馬拉松訴訟,暫時劃上了句號。因B公司拒不領取法律文書,下落不明,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已公告送達判決書,此案將于2004年3月8日上訴期滿。關于艱難的勝訴之路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債權債務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艱難的勝訴之路
——解讀A公司訴B公司投資款糾紛案
歷時近6年,歷經一審、2次再審、2次申訴、抗訴及發回重審,歷經被告人B公司法人資格的注銷、撤銷注銷、行政復議及確認其訴訟主體資格,原告A公司終于贏得了200萬元投資款官司。
一、A公司訴訟大事記。
1、1998年3月,A公司向海南中級人民法院起訴B公司(附件一),B公司提起反訴(附件二)。
2、1998年8月,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做出(1998)海南民二初字第15號《民事判決書》(附件三)判決:①合同無效。②B公司返還A公司86.368萬元。
3、1998年11月,A公司沒有上訴,而在判決生效后,向海南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附件四)。
4、1999年6月,海南中級人民法院以(1999)海民監字第2號通知書駁回A公司的再審申請(附件五)。
5、1999年6月,A公司繼續向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附件六、七)。
6、2000年5月,省高級人民法院以(1999)瓊高法民申字第154號《民事裁定書》指令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再審(附件八)。
7、2000年12月,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做出(2000)海南民再初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維持原海南中級人民法院(1998)海南民二初字第15號《民事判決書》(附件九)。
8、2000年12月,B公司在儋州市工商局未經清算即注銷。
9、2001年1月,A公司不服,仍未上訴,而是在判決生效后,向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申訴書同第5項。
10、2001年11月,省高級人民法院以(2001)瓊高法民申字第47號《駁回再審申請通知書》駁回了A公司的申訴(附件十)。
11、2001年12月,A公司仍不服,向省檢察院申訴,申訴書同第5項。
12、2002年2月4日,省檢察院以瓊檢民行抗字[2002]11號《民事抗訴書》(附件十一),向省高級人民法院就本案提起抗訴。
13、2002年2月25日,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02)瓊民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書》,提審本案,并中止海南中級人民法院(2000)海南民再初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的執行(附件十二)。
14、2002年6月,經A公司投訴,儋州市工商局撤銷對B公司的注銷登記,決定恢復B公司(附件十三)。
15、2002年6月28日,B公司法人代表陳某以其個人名義,向儋州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請求撤銷儋州市工商局恢復B公司的決定(附件十四)。
16、2002年10月18日,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審期間,以B公司注銷、恢復登記并行政復議為由,做出(2002)瓊民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書》(附件十五),裁定中止本案訴訟。
17、2003年7月10日,省高級人民法院做出(2002)瓊民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書》,撤銷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原來作出的兩份判決即15號及3號《民事判決書》,發回海南中級人民法院重審(附件十六)。
18、2003年12月12日,海南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03)海南民再初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終于判決A公司勝訴(附件十七)。判令B公司返還A公司192.668萬元投資款及利息,訴訟費用6.064萬元,均由B公司承擔。歷時近六年的馬拉松訴訟,暫時劃上了句號。因B公司拒不領取法律文書,下落不明,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已公告送達判決書,此案將于2004年3月8日上訴期滿。如B公司不上訴,該判決生效。
二、本訴與反訴
1、簽約。
1993年1月10日,A公司與B公司簽訂一份《聯營協議書》,合作開發B別墅苑項目,合作期限23個月,B公司出儋州美扶開發區36畝土地,A公司出全部建設資金,合作建設36棟別墅。
1993年4月8日,雙方簽訂聯營儋州市B公寓項目協議書一份。該協議因故未履行。
1993年4月13日,雙方簽訂聯營儋州市木棠開發區80畝土地的《合作協議書》一份。雙方約定,B公司出資600萬,A公司出資200萬,合作購買80畝土地。后又分別于1994年4月10日、1996年4月12日分別簽訂了兩份《補充協議》。
2、本訴。

A公司根據1993年4月13日的《合作協議書》投資200萬,B公司已還7.332萬元,故請求B公司返還192.668萬元投資款及利息。這本是一樁簡單的民事,但因B公司的反訴,變得復雜了起來。
3、反訴。
B公司根據1993年1月10日及1993年4月13日兩份協議提出反訴,請求A公司退還其多支付給A公司的8332元。理由是,根據2份合同,A公司共付給B公司402.5萬元,而B公司共付給A公司403.332萬元,多付8332元,A公司應退還此款。
針對A公司根據1993年4月13日合同投資200萬元的主張,B公司反訴稱,這200萬元是A公司根據1993年1月10日第1份《聯營協議書》投資的,根本不是依據1993年4月13日第3份《合作協議書》投入的。根據第1份《聯營協議書》,這200萬中只有80萬是投資第3份《合作協議書》的。
A公司認為,根據第1、3份協議,A公司都負有投資200萬元的義務,A公司都依約投資了,不可將二者混淆。A公司根據第1份《聯營協議》投資200萬元,并投入36萬土方工程款、7.2萬元土地平整款及1萬元規劃費,合計244.2萬元。B公司在1993年3月31日及4月1日分別支付A公司8萬及308萬合計316萬元土地款,其中200萬元是返還投資款,44.2萬元是返還土方工程、土地平整及規劃費,71.8萬元是支付A公司違約金和賠償損失的,因為B公司違約將此項目轉讓了。B公司支付A公司316萬元,了結了第1份《聯營協議書》的權利義務關系,與第3份《合作協議書》根本就沒有關系。
4、一審判決。
海南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為:“1993年1月10日,B公司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情況下,與A公司簽訂的名為土地聯營開發實為土地轉讓的《聯營協議書》違反法律規定,系無效合同。同年4月13日,B公司與A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書》,約定由A公司提供合作的20畝土地,亦未取得土地使用權,且雙方約定以租賃方式收取固定利潤,實際上是名為聯營實為借貸,違反了國家金融管理法規,應當確認協議無效。當事人根據上述無效合同收取對方的款項應各自返還。根據雙方當事人舉證表明,B公司共收取A公司409.7萬元,扣除已返還323.332萬元,余之86.368萬元應予返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七條第一款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四條第二款之規定,判決如下:(一)、海南儋州B住宅開發建設公司與海南A房地產實業公司于1993年1月10日簽訂的《聯營協議書》;同年4月13日簽訂的《合作協議書》及兩份補充協議書無效。(二)、海南儋州B住宅開發建設公司返還海南A房地產實業公司86.368萬元。上述款項限B公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逾期履行,則加倍支付延遲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page]
[點評]
1、什么是反訴?什么是反駁?遭遇起訴之后是反駁,還是在反駁的同時再提起反訴?應如何提起反訴?這是每一位訴訟當事人都要遇到的問題,也是在訴訟實踐中經常出現錯誤的問題。
反駁只能起到減少甚至駁回對方訴訟請求的作用,必須對方有訴,才有反駁。但反駁不能起到提出新的訴訟請求的作用,要在對方的訴訟請求之外,提出新的訴訟請求,只能通過反訴。
反訴是一種被動的訴,是在原告提起本訴之后,才由被告被動提出的,是建立在本訴前提之下的。因此,反訴必定受到本訴的約束,不能無條件地隨意提出。依照現行法律規定,反訴的提出,受三個條件限制:其一,必須針對本訴提出,超出本訴范圍之外,只能另行起訴,不能提起反訴。其二,必須在第一次開庭法庭辯論結束前提出。其三,不能超過訴訟時效。
2、就本案而言,B公司對反訴有誤解,不符合反訴法律規定。
其一,B公司反訴沒有針對A公司本訴提出。A公司是依據雙方1993年4月13日《合作協議書》提起本訴的,B公司也只能就此協議提出反訴,不能將雙方于1993年1月10日的《聯營協議書》牽連進來。如果B公司認為A公司違反了雙方1993年1月10日的《聯營協議書》,應另行起訴,不能在本案中就此協議提起反訴。海南中級人民法院(1998)海南民二初字第15號《民事判決書》及(2000)海南民再初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均認定B公司有權針對這兩份協議書提起反訴,明顯錯誤。正因此,這兩份判決被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02)瓊民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書》撤銷,并由海南中級人民法院(2003)海南民再初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改判。
其二,B公司未在法定期間,即第一次法庭辯論終結前提出,依法不能成立。
其三,B公司對反訴標的有誤解。B公司認為反訴標的為8332元,事實是,其反訴標的應為其主張的根據第一份協議所謂多付的100余萬元。省檢察院在其《民事抗訴書》里,對此問題有詳細的正確闡述,此不重復。
其四,B公司已超過反訴時效,喪失了勝訴權。對已過訴訟時效的當事人,喪失的是何種權利,學界有爭議。一說認為喪失的是程序權利,即起訴權,不能提起訴訟。二說認為喪失的是實體權利,即能起訴但不能勝訴。通說認為,不管什么權利,已過訴訟時效,喪失的是受法律保護的權利。
B公司依據1993年1月10日《聯營協議書》反訴,但沒有舉證其一直向A公司主張多付出的100余萬元款項的證據,因此,反訴時效已過,不再受法律保護。
三、再審、申訴與抗訴
A公司對一審判決不服,奇怪的是,A公司并不依法定程序上訴,而是等待判決生效后,仍然向一審海南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筆者帶著疑問,采訪了A公司胡某副總經理。“經與律師研究,我們認為一審程序違法。”“程序違法的表現呢?”“主要表現在反訴問題上,共有四項錯誤:其一,B公司的反訴沒有在法庭辯論終結前提出。其二,沒有針對本訴提出。其三,一審法院超出反訴請求審理本案。其四,反訴超過訴訟時效,不應受法律保護。”“程序違法與你們公司上訴有什么關系?”“根據法律規定,程序違法案件上訴后,只能是發回重審,二審法院不能直接改判。這樣,反而浪費時間,還莫不如直接向一審法院申請再審。”
1998年11月,A公司向海南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1999年6月28日,海南中級人民法院駁回A公司的再審申請。海南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復查結果表明原判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是正確的。你公司與儋州B住宅開發建設公司于1993年1月10日簽訂的《聯營協議書》和1993年4月13日簽訂的《合作協議書》均屬無效,原判將兩個訴訟一并審理,按無效合同的處理原則,判決雙方相互返還財產,符合法律規定。你公司對該案的申訴理由不能成立,原判決應予維持。”
A公司不服,向省高級人民法院繼續申請再審。此次A公司申請再審的結果是,省高級人民法院指令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再審。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再審維持了原判。基于與第一次申請再審相同的理由,A公司仍未上訴,而是在判決生效后,向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此次申訴的結果是,A公司被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A公司仍不服,向省檢察院提出申訴,依法申請省檢察院抗訴。省檢察院依法受理,就本案向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省檢察院《民事抗訴書》認為:“一、再審判決認為反訴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審、再審時A公司均主張B公司多付給該公司的107.8萬元系B公司當時不愿履行《聯營協議》的違約補償金;而B公司一審時主張該款多付是由于過失造成,A公司屬不當得利;再審時,B公司卻主張該款為該公司應A公司要求借給該公司使用的。由于該筆多付的107.8萬元款項的性質沒有其他證據予以證實,故只宜認定為B公司因疏忽而多支付給A公司。A公司取得的107.8萬元屬不當得利,B公司有權要求返還。但B公司向A公司追索或主張抵銷該款,均應在其付款后兩年之內,即1995年4月1日之前;否則,即超過訴訟時效。而B公司在訴訟時效內向A公司主張返還或抵銷該筆款項的事實無證據予以證實。因此,B公司于1998年7月本案審理時才提出反訴,主張以該筆債權抵銷其所欠A公司的債務,已超過《民法通則》第135條規定的訴訟時效,依法不應予以支持。二、再審法院審理B公司的反訴請求時,擴大了審查范圍,支持了其反訴請求范圍之外的訴訟請求。B公司的反訴請求為判令A公司返還多收取的款項8332元,B公司向海南中院交納了相應的訴訟費343元。根據法律的規定,反訴的請求是為了抵銷本訴的請求。應該指出的是,本案反訴審查的《聯營協議》涉及標的為316萬元,在履行該協議時,A公司向B公司支付的款項為208.2萬元,B公司向A公司返還款項為316萬元。因此,在該協議中B公司可以主張其向A公司多支付了107.8萬元。本案中B公司若反訴請求法院審理《聯營協議》中雙方的債權債務,并且以其在該協議中對A公司享有的上述107.8萬元的債權抵銷本訴中B公司所欠A公司的債務194.168萬元,則B公司應向法院請求應為107.8萬元,其訴訟費應為1萬余元。然而,反訴中,B公司只請求法院判令A公司返還8332元,其所交納的訴訟費也僅為343元,故一審法院依法只能審查《聯營協議》的部分內容。一審法院審查《聯營協議》的全部內容,并支持了B公司在該協議中對A公司所享有的債權107.8萬元,并以該債權抵銷A公司在《合作協議》中對B公司所享有的債權194.168萬元,最終僅判令B公司向A公司返還購地款86.368萬元,明顯擴大了反訴的審查范圍,支持了反訴請求之外的主張,違反了民事訴訟法關于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則,沒有法律依據。三、再審法院判決未依雙方的過錯程度劃分各自所應承擔的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錯誤。《聯營協議》、《合作協議》既然已經無效,則應各自返還取得的對方財產,此外,還要根據雙方對造成合同無效的過錯程度向對方賠償損失。本案中,再審法院未對雙方的過錯進行認定,也未判令B公司對A公司資金被其占用長達5年而造成的利息損失予以賠償,明顯違反了《民法通則》第61條第1款之規定,屬適用法律錯誤。”[page]
[點評]
1、關于再審與申訴。二者有相同點,也有質的區別。二者相同點是:(1)都必須在判決、裁定生效后提出。(2)都認為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有錯誤。(3)都必須向原審或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4)申請再審、申訴期間,都不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二者的區別是:(1)申請再審應當符合法定條件,符合條件的必然引起再審的法律后果。而申訴,則沒有法定條件限制,只要當事人認為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就可以提出。(2)當事人申請再審,必須在判決、裁定生效后兩年內提出,而申訴則無此限制。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的規定,五種情形當事人可以申請再審:(1)有新證據,定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2)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3)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錯誤的。(4)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的正確判決、裁定的。(5)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
2、當事人可以向原審人民法院,也可以向上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實踐中,慣例是,一般由作出生效判決的人民法院再審,對再審結果不服的,才能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本案即是如此,對海南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生效判決,A公司首先向海南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被駁回后才向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3、同是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的判決,為何對一審判決即(1998)海南民二初字第15號《民事判決書》,A公司可以申請再審,而A公司對海南高級人民法院發回重審后,由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的(2000)海南民再初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不服,不能申請再審,只能申訴呢?這緣于一項司法解釋,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07條的規定,根據該條規定,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后維持原判的案件,當事人不得申請再審。
省高級人民法院第一次將本案發回重審后,海南中級人民法院適用的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本案。審判監督程序不是每個案件的必經程序,也不是一般的第一審程序和第二審程序,而是一種審判救濟程序,是第一審和第二審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審級的一種特殊程序。海南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重審判決維持了原一審判決,根據上述司法解釋,對維持原判的重審判決不服,只能上訴或申訴,不能申請再審。
4、對于再審與申訴的區別,審判實踐中往往不注意區分,造成誤解,在本案中也存在此種情況。A公司第一次向海南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而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在駁回A公司的通知中,卻使用了申訴一詞,明顯混淆概念。A公司對海南中級人民法院的重審判決不服向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時,省高級人民法院卻以A公司不得在此種情況下申請再審為由予以駁回,也明顯混淆了概念。正是因為A公司知道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法的第207條司法解釋的規定,A公司向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的是申訴,而不是申請再審。這貌似玩文字游戲,實則是A公司嚴格遵守了現行法律關于審判監督程序的法律規定。A公司在此種情況下的確不能申請再審,但只要對生效判決、裁定不服,卻可以申訴。
5、抗訴是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實施審判監督的一種形式,抗訴與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最大不同是,檢察機關抗訴,審判機關必須再審,同時作出中執執行原判決、裁定執行的裁定。檢察機關抗訴的情形,與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情形,除“新證據”情形外,其它四種情形是一致的。需說明的是,同級檢察機關不能對同級審判機關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提出抗訴,必須通過其上級檢察機關抗訴。就本案而言,本案的生效判決是由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做出的,海南檢察分院不能對此判決提出抗訴,而應由海南省檢察院抗訴。
四、指令再審、提審、發回重審
1、指令再審。
1999年6月,A公司第一次向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指令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再審本案。2000年12月6日,海南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00)海南民再初字第3號《民事判決書》,作出了維持原該院作出的(1998)海南民二初字第15號《民事判決書》的再審判決。
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再審判決認定:“1993年1月10日,儋州B公司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情況下,與A公司簽訂的名為土地聯營開發實為土地轉讓的《聯營協議書》違反法律規定,系無效合同。同年4月13日,儋州B公司與A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書》,約定由A公司提供合作的20畝土地,亦未取得土地使用權,且雙方約定以租賃方式收取固定利潤,實際上是名為聯營實為借貸,違反了國家金融管理法規,應確認協議無效。在此協議基礎上所簽訂的兩份《補充協議書》亦屬無效。雙方當事人根據上述無效合同收取對方的款項應各自返還。儋州B公司共收取A公司409.7萬元,扣除已返還323.332萬元,余之86.368萬元應予返還。本案儋州B公司提出的反訴與本訴,主體相同,且屬同一合作關系,可合并審理;雙方在聯營協議糾紛中,儋州B公司多支付給A公司的106.3萬元,A公司稱該款是其投入的三通一平資金及儋州B公司賠償的經濟損失,未能提供證據予以證明,不予認定,儋州B公司的反訴主張,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A公司申請理由不成立,應予駁回。”
2、提審。
2002年2月4日,省檢察院就本案向省高級人民法院抗訴后,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02)瓊民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書》,決定提審本案。2003年7月10日,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02)瓊民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書》,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判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案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裁定如下:一、撤銷海南中級人民法院(1998)海南民二初字第15號民事判決和該院(2000)海南民再初字第3號民事判決;二、發回海南中級人民法院重審。”
3、發回重審。
根據省高級人民法院(2002)瓊民抗字第13號《民事裁定書》,海南中級人民法院另行組成了新的合議庭,重新審理了本案。2003年12月12日,該院作出(2003)海南民再初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
海南中級人民法院重審判決認為:“2000年12月11日B公司經申請被儋州市工商局核準注銷,2002年6月21日儋州市工商局又作出《撤銷B公司注銷登記的通知》,決定恢復B公司。該通知送達后,B公司便具有參加民事活動的主體資格,同時也享有訴訟主體資格。B公司與A公司于1993年4月13日簽訂的《合作協議書》中約定A公司所提供的20畝土地,A公司并未取得合法的使用權,且約定A公司以租賃方式收取固定利潤,是典型的名為聯營實為借貸。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聯營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四條第二款規定:“企業法人、事業法人作為聯營一方向聯營體投資,但不參加共同經營,也不承擔聯營的風險責任,不論盈虧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潤的,是名為聯營實為借貸,違反了有關金融法規,應當確認合同無效……”據此,雙方簽訂的《合作協議書》依法應確認無效。雙方憑據無效的《合作協議書》在此后簽訂的二份補充協議也屬無效。《經濟合同法》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經濟合同被確認無效后,當事人依據該合同所取得的財產,應返還給對方。有過錯的一方應賠償對方因此所受的損失;如果雙方都有過錯,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B公司依據無效的合作協議收取的A公司的200萬元以及A公司依據無效的補充協議取得的B公司的7.332萬元都應返還給對方。折抵后B公司還應返還192.668萬元給A公司。B公司雖然在原一審和再審中均以1993年1月10日雙方簽訂的《聯營協議書》和1993年4月8日雙方簽訂的《合作協議書》提出反訴,但B公司提出反訴所依據的《聯營協議書》涉及的開發土地位于儋州市美扶開發區;該《合作協議書》涉及的合作開發的B公寓位于儋州市那大市區,與本訴的《合作協議書》涉及的民事權利義務內容均相差甚遠,應不屬同一事實或同一法律關系,不具備合并審理中的反訴與本訴有牽連的條件。另之,B公司的反訴是在原一審庭審辯論結束之后才提起,已超過提出反訴的法定時間。B公司與A公司之間因1993年1月10日的《聯營協議書》及1993年4月8日的《合作協議書》發生的糾紛,B公司可另案起訴。判決如下:“海南儋州B住宅開發建設公司應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一個月內返還人民幣192.668萬元給海南A房地產實業公司,并按中國人民銀行一年期流動資金貸款利率計付50%的利息。”[page]
[點評]
1、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77條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以及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的,有權提審或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根據該條規定,對已生效的錯誤判決、裁定,最高級人民法院及上級法院有權提審和指令再審。至于是提審還是指令再審,完全由上級法院決定。所以,省高級人民法院第一次作出指令再審裁定,第二次作出提審裁定。
所謂提審就是提級審理之意,因為各級人民法院均有級別管轄。就本案而言,按級別管轄不由省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本案當為提審。
2、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84條之規定,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案件,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是由第一審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審程序審理,所作判決、裁定當事人可以上訴;上級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審的,按照第二審程序審理,所作的判決、裁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
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審本案時,本案只有海南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其所做判決因雙方當事人沒有上訴便生效了。因此,省高級人民法院如果不提審,應按一審程序審理,所作判決、裁定當事人可上訴。因省高級人民法院做出了提審裁定,其所做的發回重審的提審結論便是終審的,不能上訴。根據上述規定,提審是按第二審程序審理,而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一款第(四)之規定,對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二審法院應發回重審。正是基于這樣的法律規定,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審本案后,因原判決關于反訴程序違法,便作出了發回海南中級人民法院重審的裁定。換言之,程序違反案件,二審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改判,只能發回重審。
五、B公司的企業法人資格與訴訟主體資格
在本案訴訟過程中,B公司于2000年11月,向儋州市工商局申請注銷登記,該局于12月11日核準B公司注銷登記。A公司發現此情況后,便以B公司未經清算不能辦理注銷登記為由,向儋州市工商局提出異議。A公司認為,在訴訟期間,B公司未經清算便注銷登記,有逃避債務之嫌。儋州市工商局經調查核實于2002年6月21日撤銷了B公司的注銷登記,恢復了B公司的企業法人資格。B公司原法人代表陳某以其個人名義,對儋州市工商局撤銷B公司注銷登記的行為,向儋州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儋州市政府于2002年9月11日受理此案。此時正值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審本案期間,鑒于上述情況,省高級人民法院以“B公司訴訟主體地位尚待明確”為由,裁定中止本案訴訟。
[點評]
1、本案訴訟主體是明確的,不應中止訴訟。B公司注銷后,工商行政機關撤銷了注銷登記行為,B公司雖不服,并申請了行政復議,但復議期間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因此,B公司的企業法人資格仍然存在,故其訴訟主體資格也是明確的。
2、根據《行政復議法》第21條的規定,有四種情形,可以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1)被申請人認為需要停止執行的。(2)行政復議機關認為需要停止執行的。(3)申請人申請停止執行,行政復議機關認為其要求合理,決定停止執行的。(4)法律規定停止執行的。但就本案而言,不存在這四種情形。
3、根據《行政復議法》第12條第二款之規定,對海關、金融、國稅、外匯管理等實行垂直領導的行政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上一級主管部門申請行政復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已有原來的地方政府領導改制為垂直領導,對B公司的撤銷注銷登記行為不服,依法應向省工商局而不是儋州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
4、根據《行政復議法》第10條之規定,行政復議的申請人應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儋州市工商局的撤銷行政行為的相對人是B公司,而不是其法人代表陳某,因此,對撤銷行政行為不服申請行政復議的申請人應是B公司而不是陳某。
B公司以行政復議為由,拒不到庭應訴,拒不領取人民法院的法律文書,求“生”不愿,求“死”不能。歷時幾年的訴訟,最終落得敗訴的結局,教訓是深刻的。
實事求是地說,本案是一樁并不復雜的民事案件。如果說有點復雜的話,是人為地將兩個不同的合作項目、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攪在了一起。而這兩個不同的合作項目與法律關系,在法理及現行法律規定上,有沒有關聯性,能否與A公司的本訴合并審理,應該說,也是一個簡單、明了的法理。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樁簡單、明了的民事案件,A公司1999年6月第一次申請再審被駁回;2000年12月海南中級人民法院按省高級人民法院指令重審時,仍被駁回;2001年11月A公司向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時,再次被駁回。A公司被逼無奈,向省人民檢察院申訴。2002年2月省人民檢察院向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抗訴,省高級人民法院才采納了A公司的主張,撤銷了省中級人民法院以前做出的兩份錯誤判決。為什么一樁如此簡單明了的民事案件,歷經兩級法院多次重審、再審甚至經檢察機關抗訴才得以糾正錯判?為什么一樁如此簡單明了的民事案件,歷經近六年審判都不能最終劃上句號?這都值得深思。
與B公司正相反,A公司卻是求“死”不愿,求“生”不能。一樁標的不大簡單明了的民事案件,一拖近六年都不得解決,A公司已被拖得筋疲力盡,已被拖至崩潰的邊緣?是啊,有哪家公司經得起如此的折騰?
A、B兩家公司兩種命運兩重天。司法怎樣為民?司法怎樣為企業為經濟保架護航?此案的訴訟和審判,提供了一個參考和借鑒,值得全社會深刻反思。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