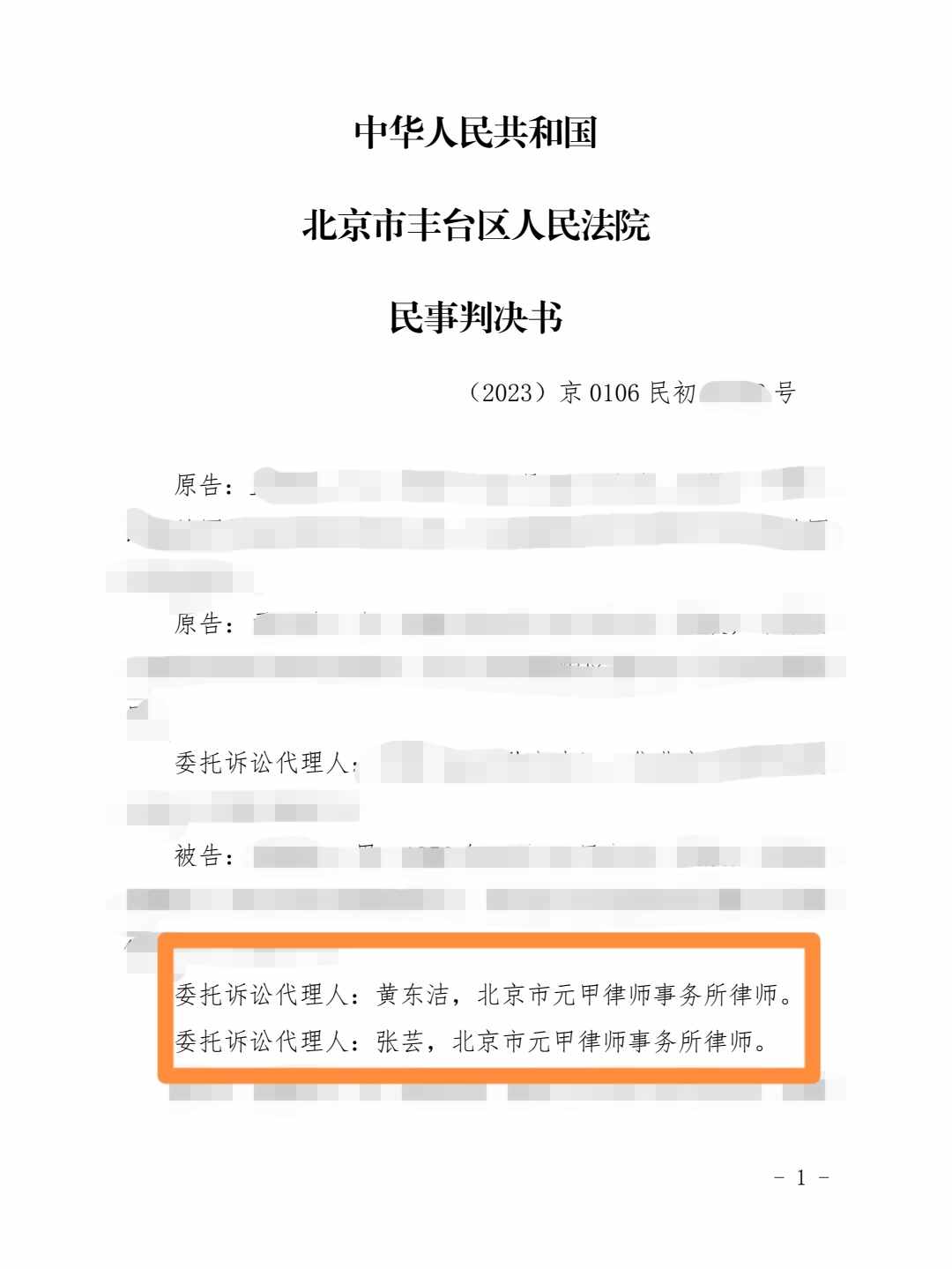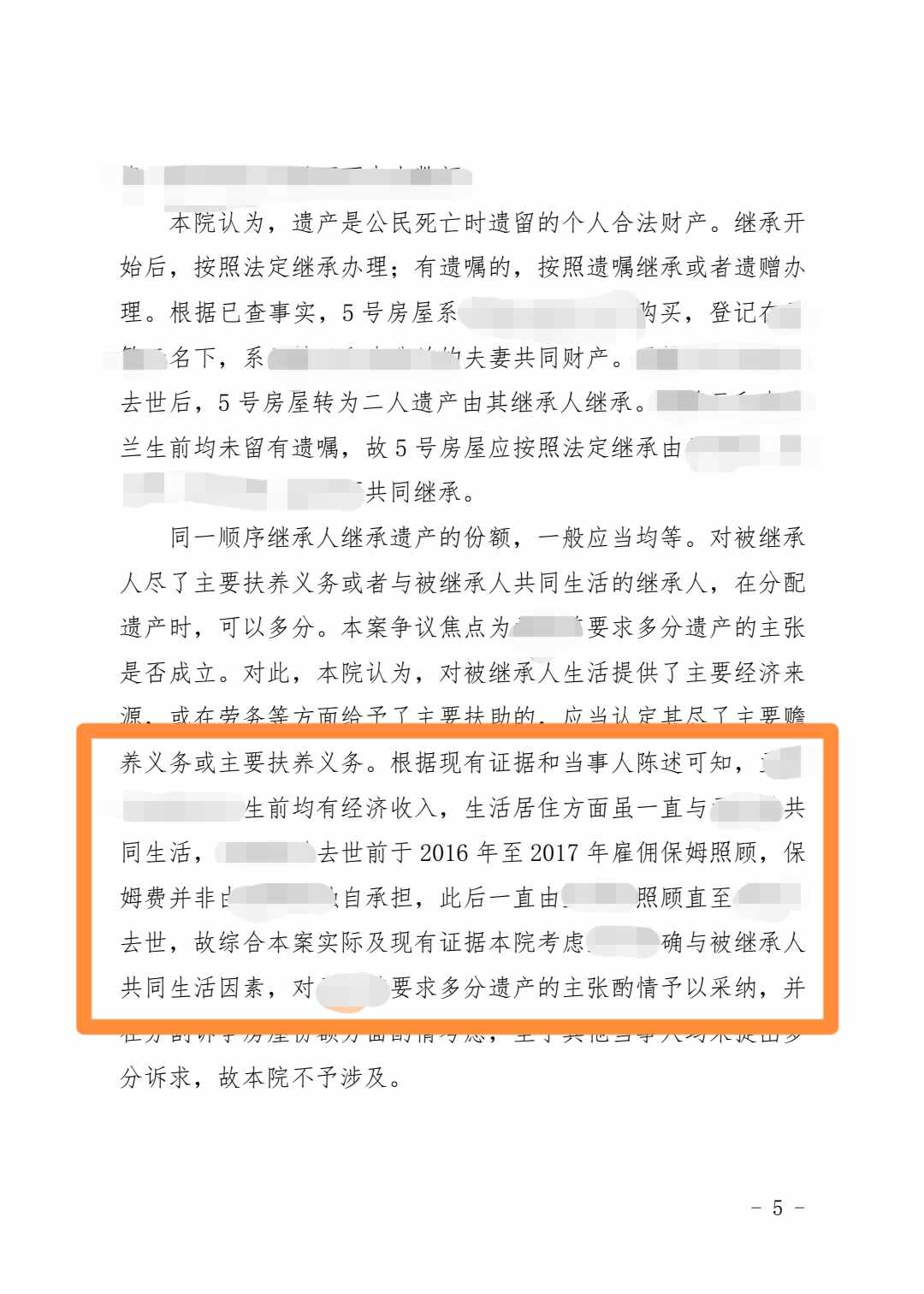效率違約的價值評析 什么是效率違約
 于海明律師2021.12.31632人閱讀
于海明律師2021.12.31632人閱讀
導讀:
效率違約,又稱“有效益的違約”,是指違約方從違約中獲得的利益大于他向非違約方作出履行的期待利益。違約責任是對違約行為的一種法律制裁,那么,關于效率違約的價值評析——對我國合同法第110條的再思考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效率違約,又稱“有效益的違約”,是指違約方從違約中獲得的利益大于他向非違約方作出履行的期待利益。違約責任是對違約行為的一種法律制裁,那么,關于效率違約的價值評析——對我國合同法第110條的再思考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效率違約的價值評析——對我國合同法第110條的再思考
一、效率違約的理論基礎
與傳統合同法學者的觀點不同,在經濟分析法學派學者的眼中,合同法已由“單純懲惡揚善的工具”變為一種“合理劃分商業風險的法律手段”(注:葉林:《違約責任及其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頁。)合同責任也不必然使當事人承擔嚴格履行的道德義務,而為當事人提供一種“或履約或在不履約時賠償損害的選擇。”(注:holmes:the common law(m.dew howe edn,1963),p.324.)經濟分析法學派正是通過對交易過程中成本與風險關系的分析來重新評價合同責任的功能和價值基礎的。正如其代表人物波斯納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中指出的那樣,“違約的補救應以效率為其追求的主要目標。如果從違約中獲得的利益將超出他向另一方作出履行的期待利益,如果損害賠償被限制在對期待利益的賠償方面,則此種情況將形成對違約的一種刺激,當事人應該違約。”(注: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led 2,boston and toronto (977)j,p.89-90.)
從某種意義上講,效率違約體現了兩大法系在違約責任理論認識上的分歧,效率違約的兩大理論依據均來自學者們對這些分歧的探討。分歧之一是違約行為在道德上是否應受譴責。大陸法系學者一貫認為違約行為在道德上的應受非難性歷來是合同責任存在的重要依據。但美國學者霍姆斯(oliver holmes)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道德與法律的混淆在合同法中表現得最為嚴重,違約的非道德性觀點完全混淆了兩者的關系。合同當事人在道德上并不負有履約的義務,“因為一個合同當事人具有一種選擇-履約或在不履約時賠償損害,締結合同并不承擔履行的義務”。(注:holmes:the common law(m.dew howe edn,1963),p.324.)“信守合同的義務意味著一種推斷,即如果你不信守合同,必須賠償損害,正如你侵權必須賠償損害一樣。”(注: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 10,harv l.rew p.457 458-469(189)。)霍姆斯所主張的違約不涉及道德因素的觀點對普通法的合同責任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效率違約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分歧之二是違約責任應體現為制裁功能還是補償功能。大陸法系學者普遍以為,違約責任是對違約行為的一種法律制裁,因為民事責任與民事制裁的外延是同一的,“責任為違反義務者應受一定制裁之根據也”。(注:鄭玉波:《法學編論》,三民書局1987年版,第116頁。)但違約責任具有制裁性的觀點,受到霍姆斯等人批評,霍姆斯認為,違約責任不應具有制裁性而是一種“分配風險”(allocation of risk)的方式。美國學者dowson也認為“傳統合同補救法津的目標并不是強迫允諾人履行其允諾,而是補嘗因違約所致的損失,……當損害賠償足以保護受害人時,則不采用實際履行方式”。(注:dowson:contracts,the foundation press,inc 1987,p.31.)上述學者們的觀點在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355條也有所體現。可以說,違約責任的補償性是效率違約的又一理論依據。
在其后的發展過程中,兩大法系國家雖然在合同法領域中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趨同與融合。但大陸法系學者(包括我國合同法學者在內)始終沒有接受效率違約理論,并一直對其進行著尖銳的批評,歸結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效率違約容易助長人們的功利主義傾向,淡化合同責任意識,不利于維護交易安全,保障交易秩序;第二,因履行利益難以精確計算,效率違約無法保證給非違約方以充分的補償。在這里,我不想對效率違約理論本身的褒貶作過多的評說,只想就該理論所體現的效益原則和經濟分析手段對我國合同法的借鑒意義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效率違約理論對中國合同法的借鑒意義
效率違約理論的突出特點在于把效率(effieiency)從經濟學領域引入合同法領域,彌補了單純法律分析方法的不足。不可否認,效率違約理論中包含著重要的經濟學觀點即在違約行為發生時,法官要求當事人實際履行還是賠償對方損失,取于合同的履行成本與合同雙方收益的比較。對此,波斯納曾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中舉例說明如下:甲廠與乙廠簽定協議,委托乙廠為之加工100,000個小器件,作為甲廠制造的某種機器的配件。在甲廠收到10,000個器件后,其生產的機器在市場上出現滯銷。甲廠立即通知乙廠終止合同,并承認自己違約,但乙廠回信表示要繼續履行合同。這些小器件除了安裝在甲廠的機器上外,別無他用。波斯納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為避免資源的損失浪費,使有限的社會資源獲得最佳配置,法院應終止原合同的效力,判決用損害賠償的方式代替實際履行。
應該說,波斯納所舉的例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量的違約行為中確有相當一部分是當事人在權衡比較了履約成本與違約收益后做出的。按照大陸法系“契約必須遵守”的法律觀念,這些行為顯然是不能提倡和鼓勵的,但卻往往使我們陷入這樣的尷尬境地:一方面不實行履行合同,是對合同效力和契約價值的破壞;但另一方面,尊重合同的效力并實際履行合同,又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甚至在某些場合會對違約方構成不公平,如何取舍就涉及到一個平衡社會一般公平正義與個別公平正義關系的法理問題。維護公平正義是一切法律的首要價值。合同法的首要價值是維護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即“通過對交易行為作出普通的調整,使交易雙方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體現社會公平正義觀,維護理想的社會秩序”。(注:楊永清:《預期違約規則研究》,載《民商法論叢》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363頁。)但是,這種對“交易行為的普遍調整”至多只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即一般公平正義,它無法保障個別公平正義的實現,這不僅是合同法局限性之所在,也是所有成文法的缺陷。因為“法律絕不可能發布一種即約束所有人同時又對每個人都真正最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完全準確地給社會的每個成員作出何謂善德、何謂正確的規定。人類個性的差異,人類行為的多樣性,所有人類事務無休無止的變化,使得無論是什么藝術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制定出可以絕對適用于所有問題的規則”。(注: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頁。)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無視對于個別公平正義的犧牲,因為沒有個別公平正義的存在,社會一般公平正義也就如同海市蜃樓般虛無縹緲。為了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為了避免法律適用的過于僵化而導致的不公正,應在遵循合同效力普遍性的前提下,賦予法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權,使其在處理具體案件的過程中可以對一般的法律規則予以變通,從而實現或接近個別公平和正義。正是從這一原則出發,波斯納運用經濟學中的效益原理對上案作出了合理的評判,用損害賠償替代實際履行合同,即維護了合同的效力,又避免了社會資源的浪費,最大限度地兼顧了一般公平正義與個別公平正義的關系。
在我國合同法領域,上述成文法的局限性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國合同法基本沿襲了大陸法系的法律傳統,強調“合同必須遵守”,把實際履行作為違約責任的主要形式。在司法實踐中,當一方違約時,如果非違約方要求實際履行合同而違約方又有履行能力時,法官通常不作干預。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是以制定法為主的國家,法官司法創造性較差,難以突破法律對合同效力的即有規定,另一個重要原因則在于無論是《民法通則》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都未將“效益”作為基本原則加以規定,使得我們的法官無法象波期納那樣自覺地運用經濟學中的效益原理“通過分析交易過程中的成本與風險之間的關系,借以評判違約當事人的行為動機和結果”。(注:葉林:《違約責任及其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頁。)其結果是社會生活中大量的違約責任以實際履行為救濟措施,不僅使合同的履行質量難以保證,無形中增加了法院執行監督的負擔,更為嚴重的是它強化了違約責任的懲戒功能而削弱了其社會補償性,加劇了社會公平與社會效益之間的矛盾,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

針對這種情況,我認為有必要深入研究經濟分析法學派提出的效率違約理論,借鑒其中的效益原則和經濟分析方法來完善我國合同法中的違約責任替代理論。違約責任的替代是指當一種違約責任不能由違約方承擔時,由其承擔另一種違約責任。在大陸法系國家違約責任的替代通常是指由損害賠償替代實際履行,相反的替代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國家的合同法理論中。
我國統一合同法在第110條對違約責任的替代及替代條件做出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錢債務或者履行非金錢債務不符合約定的,對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
(二)債務的標的不適于強制履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
(三)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
其中在與效率違約有關的第二條中的“履行費用過高”因缺乏明確的判斷標準,使其作為違約責任的替代條件顯得不夠嚴密,不免使人產生這樣的質疑;過高的標準是什么?究竟多高的履行費用法官才允許違約方以損害賠償代替實際履行呢?借鑒效率違約理論中的效益原理,我認為當違約方履約的成本超過合同雙方基于合同所能獲得的利益時,法官就應該允許他用損害賠償代替實際履行。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履約所需要的財力,物力將超過其他合理救濟措施所需要的代價,違約顯然比履約更具有經濟效益,在違約責任替代后,違約方可以充分補償非違約方基于合同所能獲得的履行利益,從而最大限度地削弱了違約給合同雙方造成的損失。
需要說明的是,將效益原則引入違約責任替代理論并不是要根本否定實際履行作為一種補救方式的存在價值。效率違約理論的存在必須同時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履行利益能夠精確地確定;二是合同規定的標的物能夠替代,(注:王利明:《違約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頁。)兩者只有同時具備,效益原理才能在違約責任的替代中真正發揮作用。這一方面要求法官具有較高的職業素質和高度負責的工作精神,對合同的履行利益有較為準確的把握;同時也要求合同雙方當事人有合作精神,能夠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盡早從已不完備的合同關系中解脫出來,重新投入市場交易環境中去。
誠然,效率違約理論因經濟分析法學自身的局限性也存在許多缺陷,其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然人視為不受道德因素影響而精于計算的“商業化”的人很難說就真實全面的反映出人的本性,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正是“普通法牢記合同義務的商業性質”的表現,(注:彼德·斯坦:《西方社會的法律價值》,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頁。)我們不應該也沒有必要去接受它的全部理論。但我認為,效率違約理論把經濟學的效益原則和分析方法運用于合同法領域,為我們更好地了解違約方的行為動機,健全和完善違約責任替代理論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模式,從這一意義上講,效率違約理論對中國合同法是有借鑒意義的。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