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轉(zhuǎn)包工程引起的債務(wù)承擔(dān)問(wèn)題
 許瑞林律師2021.12.16854人閱讀
許瑞林律師2021.12.16854人閱讀
導(dǎo)讀:
該案在審理過(guò)程中,經(jīng)法院調(diào)查,王某承認(rèn)預(yù)拌混凝土供需合同中B建筑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印章是其私刻的。第三種意見認(rèn)為,B建筑公司將工程轉(zhuǎn)包給不具備相應(yīng)資質(zhì)的王某,違反有關(guān)法律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而王某購(gòu)買的混凝土實(shí)際用于施工,故B建筑公司應(yīng)對(duì)王某的債務(wù)承擔(dān)連帶清償責(zé)任。那么非法轉(zhuǎn)包工程引起的債務(wù)承擔(dān)問(wèn)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guān)知識(shí),希望能幫助大家。
該案在審理過(guò)程中,經(jīng)法院調(diào)查,王某承認(rèn)預(yù)拌混凝土供需合同中B建筑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印章是其私刻的。第三種意見認(rèn)為,B建筑公司將工程轉(zhuǎn)包給不具備相應(yīng)資質(zhì)的王某,違反有關(guān)法律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而王某購(gòu)買的混凝土實(shí)際用于施工,故B建筑公司應(yīng)對(duì)王某的債務(wù)承擔(dān)連帶清償責(zé)任。關(guān)于非法轉(zhuǎn)包工程引起的債務(wù)承擔(dān)問(wèn)題的法律問(wèn)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建筑工程律師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shí),希望能幫助大家。
案情:
2005年11月15日,A房產(chǎn)開發(fā)公司將其開發(fā)的怡景新苑9號(hào)、10號(hào)住宅樓工程發(fā)包給B建筑公司承建,承建范圍為土建、裝飾、水電、暖衛(wèi);開工日期為2005年11月20日,竣工日期為2006年7月1日;合同價(jià)款713萬(wàn)元。B建筑公司承包上述工程后,將其轉(zhuǎn)包給王某,雙方于2006年8月20日補(bǔ)簽協(xié)議一份,約定:B建筑公司同意王某施工承建怡景新苑9號(hào)、10號(hào)住宅樓工程;工期自2005年12月26日至2006年10月30日;王某承擔(dān)B建筑公司在與建設(shè)單位A房產(chǎn)開發(fā)公司所簽建設(shè)工程施工合同中應(yīng)承擔(dān)的所有責(zé)任和義務(wù),按該建設(shè)工程施工合同約定的質(zhì)量標(biāo)準(zhǔn)、工期、安全生產(chǎn)等進(jìn)行施工;實(shí)行自主經(jīng)營(yíng),獨(dú)立核算,自負(fù)盈虧,一切債權(quán)債務(wù)由王某承擔(dān)。
2006年4月6日,王某以B建筑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名義,與原告C混凝土公司簽訂了預(yù)拌混凝土供需合同,由C混凝土公司供給混凝土,雙方對(duì)供貨數(shù)量、質(zhì)量、價(jià)款及其支付方式等進(jìn)行了約定。該合同由王某簽字并加蓋B建筑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印章。合同簽訂后,原告C混凝土公司按合同約定完成供貨義務(wù),經(jīng)雙方結(jié)算,共計(jì)貨款557812.50元,王某已付款40萬(wàn)元,尚欠157812.50元未付。原告C混凝土公司訴至法院,要求被告B建筑公司及王某支付欠款157812.50元及違約金。被告B建筑公司抗辯稱,其從未與原告簽訂預(yù)拌混凝土供需合同,雙方不存在買賣混凝土合同關(guān)系,更不知付款之事。該供需合同是原告與王某簽訂的,王某不是本公司職工,其簽訂合同所用印章是其私自刻制的,公司對(duì)此不知情,應(yīng)由王某自行承擔(dān)責(zé)任。被告王某未作任何抗辯。該案在審理過(guò)程中,經(jīng)法院調(diào)查,王某承認(rèn)預(yù)拌混凝土供需合同中B建筑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印章是其私刻的。
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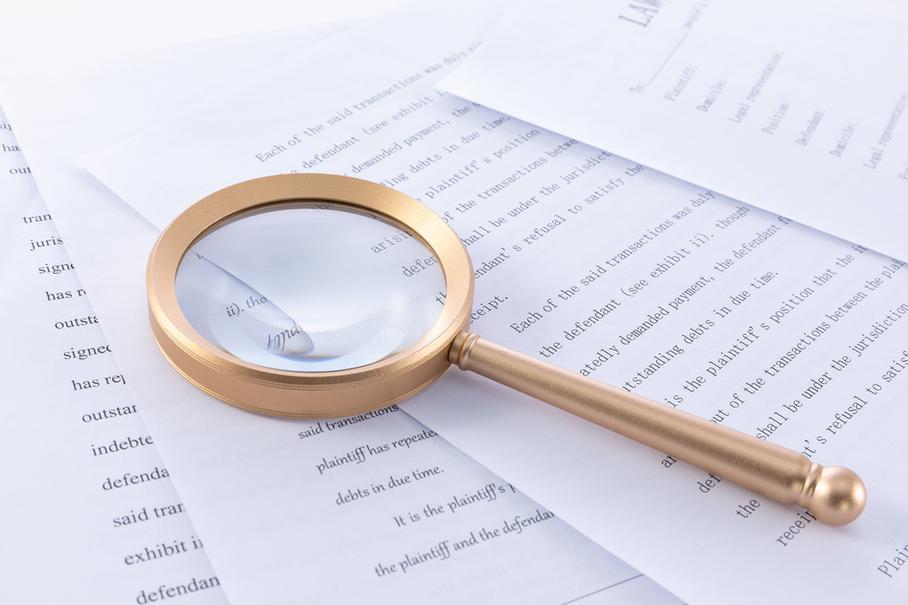
對(duì)于本案應(yīng)如何處理,存在以下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rèn)為,B建筑公司對(duì)王某以其項(xiàng)目部的名義簽訂預(yù)拌混凝土供需合同的行為不知情,事先既未授權(quán),事后也未追認(rèn),故B建筑公司不是該供需合同的當(dāng)事人。根據(jù)合同相對(duì)性原理,應(yīng)由王某自行承擔(dān)支付欠款的民事責(zé)任。第二種意見認(rèn)為,該建設(shè)工程施工合同是由B建筑公司承包的,B建筑公司將該工程全部轉(zhuǎn)包給王某后,王某以B建筑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名義與原告C混凝土公司簽訂預(yù)拌混凝土供需合同構(gòu)成表見代理。因此,應(yīng)由B建筑公司承擔(dān)還款責(zé)任。第三種意見認(rèn)為,B建筑公司將工程轉(zhuǎn)包給不具備相應(yīng)資質(zhì)的王某,違反有關(guān)法律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而王某購(gòu)買的混凝土實(shí)際用于施工,故B建筑公司應(yīng)對(duì)王某的債務(wù)承擔(dān)連帶清償責(zé)任。
評(píng)析:
本案是一起因建設(shè)工程轉(zhuǎn)包而引起的實(shí)際施工人與第三人交易中的債務(wù)承擔(dān)糾紛。解決該糾紛的關(guān)鍵在于正確認(rèn)定該預(yù)拌混凝土供需合同的當(dāng)事人及其責(zé)任承擔(dān)方式。
本案中,被告王某是以B建筑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名義與原告C混凝土公司簽訂的合同,該行為事先并未得到B建筑公司的明確授權(quán),事后也未得到B建筑公司的追認(rèn),因此,王某以B建筑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名義訂立合同屬于無(wú)權(quán)代理。在此情況下,B建筑公司應(yīng)否承擔(dān)王某無(wú)權(quán)代理的民事責(zé)任,關(guān)鍵是看王某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表見代理。
表見代理是“因本人的行為造成了足以令人相信某人具有代理權(quán)的外觀,本人須對(duì)之負(fù)授權(quán)人責(zé)任的代理。” [1]我國(guó)《合同法》第49條規(guī)定:“行為人沒(méi)有代理權(quán)、超越代理權(quán)或者代理權(quán)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duì)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quán)的,該代理行為有效。”根據(jù)上述規(guī)定,構(gòu)成表見代理須具備以下要件:1、行為人未獲授權(quán)而以本人名義與相對(duì)人為法律行為;2、因本人行為使行為人存在授權(quán)外觀且為相對(duì)人合理信賴;3、相對(duì)人為行為時(shí)主觀善意且無(wú)過(guò)失。本案中,王某自始即未獲得被代理人B建筑公司的授權(quán),其以B建筑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名義簽訂合同,符合表見代理的第一個(gè)構(gòu)成要件。但問(wèn)題的關(guān)鍵在于其是否符合表見代理的其他構(gòu)成要件。本案中,王某與C混凝土公司簽訂合同所用印章是其私刻的,B建筑公司對(duì)王某私刻印章一事并不知情,因此不存在B建筑公司以自己的行為表示授予王某代理權(quán),或者知悉王某以其代理人的名義實(shí)施民事行為而不作反對(duì)表示的情形,所以,本案不存在無(wú)權(quán)代理人王某被授予代理權(quán)的外表或假象,即不存在所謂的“授權(quán)外觀”。同時(shí),由于法律允許建設(shè)工程的承包人經(jīng)發(fā)包人同意將其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C混凝土公司不能僅僅依B建筑公司系該工程的承包人及王某私刻的印章,就輕易相信王某有權(quán)代理B建筑公司簽訂合同,必須查驗(yàn)王某是否已獲B建筑公司的明確授權(quán)。顯然,C混凝土公司并未進(jìn)行必要的審查,而是輕信王某有代理權(quán)而與之簽訂了合同。為此,不能確認(rèn)C混凝土公司在簽訂該合同時(shí)主觀上是善意無(wú)過(guò)失的。因此,本案中王某的行為不符合表見代理的其他構(gòu)成要件,其行為并不構(gòu)成表見代理,應(yīng)視為王某的個(gè)人行為,由王某自行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民事責(zé)任。從合同的實(shí)際履行來(lái)看,原告C混凝土公司直接將貨物運(yùn)交王某,貨款也由王某直接支付,故該供需合同的當(dāng)事人是原告C混凝土公司與被告王某,B建筑公司并非供需合同的當(dāng)事人。
既然王某是該預(yù)拌混凝土供需合同的實(shí)際當(dāng)事人,作為合同的相對(duì)人,理應(yīng)承擔(dān)因該合同所產(chǎn)生的義務(wù)。從本案的實(shí)際情況看,王某接收了原告C混凝土公司供給的混凝土,并由王某及其工作人員為原告出具了收料單。王某也實(shí)際支付貨款40萬(wàn)元,王某應(yīng)承擔(dān)支付剩余貨款157812.50元的民事責(zé)任,并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違約金。
B建筑公司在與A房產(chǎn)開發(fā)公司簽訂建設(shè)工程施工合同后,將其承包的怡景新苑9號(hào)、10號(hào)住宅樓工程全部轉(zhuǎn)包給沒(méi)有建筑施工資質(zhì)的被告王某個(gè)人承建,違反了《建筑法》第28條和第29條第3款關(guān)于“禁止總承包單位將工程分包給不具備相應(yīng)資質(zhì)條件的單位”以及《合同法》第272條第2款、第3款關(guān)于“承包人不得將其承包的全部建設(shè)工程轉(zhuǎn)包給第三人或者將其承包的全部建設(sh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義分別轉(zhuǎn)包給不具備相應(yīng)資質(zhì)條件的單位”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因此,應(yīng)認(rèn)定上述轉(zhuǎn)包合同無(wú)效。根據(jù)《合同法》第57條的規(guī)定,無(wú)效的合同自始沒(méi)有法律約束力。既然該轉(zhuǎn)包合同無(wú)效,B建筑公司作為怡景新苑9號(hào)、10號(hào)住宅樓建設(shè)工程的合法承包人,是對(duì)外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的獨(dú)立主體,其應(yīng)當(dāng)履行與建設(shè)單位A房產(chǎn)開發(fā)公司所簽合同項(xiàng)下的義務(wù)。B建筑公司與王某之間的關(guān)系類似于一種掛靠經(jīng)營(yíng)關(guān)系,其中轉(zhuǎn)承包人王某是掛靠人,B建筑公司是被掛靠人。在轉(zhuǎn)承包人以承包人的名義與第三人進(jìn)行交易發(fā)生糾紛的情況下,其責(zé)任承擔(dān)方式應(yīng)類推適用掛靠經(jīng)營(yíng)主體間責(zé)任承擔(dān)的有關(guān)法律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事訴訟法〉若干問(wèn)題的意見》第43條規(guī)定:“個(gè)體工商戶、個(gè)人合伙或私營(yíng)企業(yè)掛靠集體企業(yè)并以集體企業(yè)的名義從事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活動(dòng)的,在訴訟中,該個(gè)體工商戶、個(gè)人合伙或私營(yíng)企業(yè)與其掛靠的集體企業(yè)為共同訴訟人。”雖然該司法解釋并未解決掛靠人與被掛靠人之間的實(shí)體法律責(zé)任承擔(dān)問(wèn)題,但通說(shuō)認(rèn)為,最高法院上述規(guī)定的目的是直接追究掛靠雙方的連帶責(zé)任。 [2]本案中,王某作為與原告C混凝土公司直接發(fā)生購(gòu)銷合同關(guān)系的實(shí)際施工人應(yīng)對(duì)貨款承擔(dān)直接的付款責(zé)任,B建筑公司作為承包人應(yīng)承擔(dān)連帶償付責(zé)任。B建筑公司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的根據(jù)在于:1、該工程是由B建筑公司承包的,B建筑公司是對(duì)建設(shè)單位A房產(chǎn)開發(fā)公司承擔(dān)責(zé)任的獨(dú)立主體,原告C混凝土公司所提供的混凝土已實(shí)際用于該工程建設(shè),已物化為該工程的一部分;2、該工程所需材料是由實(shí)際施工人王某以承包人B建筑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名義簽訂合同購(gòu)買的,正是因?yàn)锽建筑公司非法轉(zhuǎn)包,才使王某得以對(duì)外以該公司項(xiàng)目部的名義進(jìn)行交易,從而導(dǎo)致原告誤認(rèn)并造成財(cái)產(chǎn)損失。在此問(wèn)題上,B建筑公司與王某存在共同過(guò)錯(cuò);3、B建筑公司將該工程非法轉(zhuǎn)包后從中提取了一定數(shù)額的管理費(fèi),是該工程的實(shí)際受益者,根據(jù)權(quán)利義務(wù)一致的原則,理應(yīng)對(duì)該工程所發(fā)生的債務(wù)承擔(dān)責(zé)任;4、B建筑公司將該工程非法轉(zhuǎn)包后,對(duì)轉(zhuǎn)承包人王某即負(fù)有監(jiān)督管理之責(zé),應(yīng)對(duì)王某加以嚴(yán)格管理監(jiān)督,督促其積極履行義務(wù)。B建筑公司未盡到上述職責(zé),應(yīng)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法律責(zé)任;5、讓實(shí)際施工人承擔(dān)直接的付款責(zé)任,讓非法轉(zhuǎn)包工程的承包人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能夠更好地制裁違法行為,遏制建設(shè)工程承包領(lǐng)域存在的非法轉(zhuǎn)包現(xiàn)象,有利于維護(hù)交易安全,具有更好的社會(huì)效果和法律效果。
 點(diǎn)贊
點(diǎn)贊
 收藏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