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債權罹于時效后的擔保物權保護
 黃東潔律師2021.12.11817人閱讀
黃東潔律師2021.12.11817人閱讀
導讀: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主債權罹于時效后的擔保物權糾紛案。關于時效的規定是否適用于抵押權,被擔保物權已屆時效時抵押權是否消滅,以及擔保物權的存續期間等問題一直是理論界與實務界爭論不休的話題。那么主債權罹于時效后的擔保物權保護。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主債權罹于時效后的擔保物權糾紛案。關于時效的規定是否適用于抵押權,被擔保物權已屆時效時抵押權是否消滅,以及擔保物權的存續期間等問題一直是理論界與實務界爭論不休的話題。關于主債權罹于時效后的擔保物權保護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債權債務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一、據以研究的案例
2000年3月9日,被告嚴某因購房需要而向原告中國建設銀行淮安市某支行(以下簡稱某支行)借款60000元,原、被告雙方簽訂了借款合同。合同約定:借款金額60000元;借款期限1年,即從2000年3月9日至2001年3月9日;借款月利率為3.45‰,逾期利率為日萬分之二點一。當日,雙方又簽訂了一份抵押合同,該合同約定:主債權種類為短期,數額60000元;抵押房地產的評估價格為82000元;抵押擔保的范圍包括主債權、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金、實現抵押權的費用等。合同簽訂后,雙方到淮安市淮陰區房產管理局辦理了抵押登記手續,抵押財產為淮安市某區淮北路75號202室、建筑面積為96.66平方米的房屋一幢。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催討,被告嚴某分文未付。2004年3月18日,原告某支行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嚴某承擔抵押擔保責任,以清償借款本金60000元,利息2525.40元、罰息14099.40元(利息及罰息均計算至2004年3月31日),以及2004年3月31日以后的每天12.60元的利息,并承擔本案訴訟費用。訴訟中,被告嚴某辯稱,借款的期限至2001年3月9日,到期后,原告并未主張權利,直至2004年3月18日才訴請歸還借款本息,故原告的主張已超過法律規定的訴訟時效,合同的主債權超過訴訟時效,作為從合同的抵押合同當然也隨之超過訴訟時效,故法院應當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主債權罹于時效后的擔保物權糾紛案。關于時效的規定是否適用于抵押權,被擔保物權已屆時效時抵押權是否消滅,以及擔保物權的存續期間等問題一直是理論界與實務界爭論不休的話題。本案的審理與判決,必須依賴于對這些基本問題的價值判斷與選擇。
二、關于抵押權之于被擔保債權的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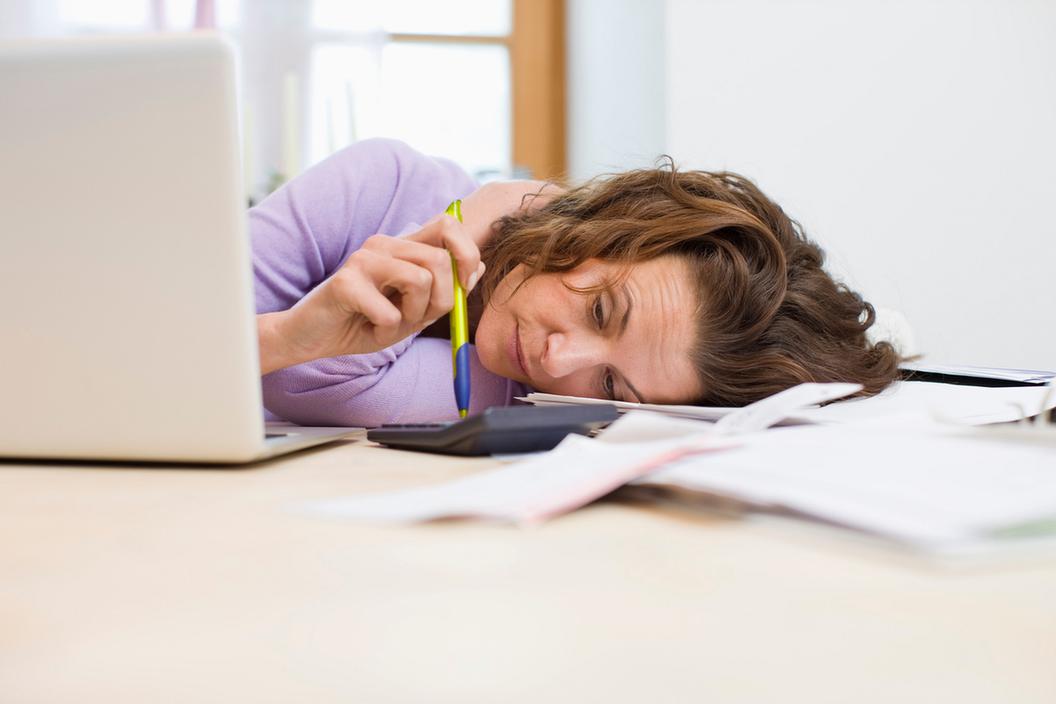
抵押權是指債權人對于債務或第三人不轉移占有而供擔保之物,于債務人屆期不履行債務時,可就該物的賣得價金優先受償的權利。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范圍向來是抵押權效力問題的重要內容。抵押權為約定擔保物權,其所擔保的債權范圍在設定之時就應有明確的界定,而且應當經登記公示。如果當事人僅約定對原債權擔保而未對附隨性的債權如利息、違約金等作出約定的,往往發生爭議。根據法國、德國、瑞士、日本等國立法的規定以及一般的學理解釋,附隨性債權屬于當然性被擔保債權,應在優先受償之列。也就是說,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范圍不僅在于原債權本身,還擴及至利息、遲延利息、實現抵押權費用、違約金等派生債權。本案好在當事人之間已對被擔保債權的范圍有所約定,并經登記公示,故爭議不大。但這卻是法官裁判需要首先明確的基本法理。
三、關于抵押權的時效問題
時效問題是否適用于抵押權,理論上一直存在肯定說與否定說之爭。肯定說認為,時效之適用客體為一切民事權利,抵押權既是民事權利當然應當適用。而否定說則認為,時效僅對于請求權可適用,物權請求權可作為時效的客體,但物權本身則不能適用時效的規定。我國現行法律中對抵押權的時效問題雖未規定,但同說認為,據《民法通則》規定的意旨,訴訟時效的適用客體應以請求權為限。從國外一些立法例來看,日本民法承認抵押權本身存在時效,而且“抵押權對于債務人及抵押權人非與其擔保的債權同時,不因時效而消滅”。法國民法中也有類似的規定。而德國、瑞士民法則對抵押權的時效持否定態度,但對于抵押權的行使卻規定有時間限制,其確立了消除抵押權的公示催告制度,對于不知名債權人在登記10年以后,為行使抵押權時,經抵押權人請求,法院可作出除權判決。再看我國的臺灣地區民法,其設有抵押權除斥期間制度,抵押權在被擔保債權時效屆滿后,經5年不實行的,其抵押權消滅。而根據我國《擔保法》第49條的規定,抵押人在抵押權存續期間對抵押物的處分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該規定既不利于抵押人,也不利于充分發揮物的效用。那么,我國究竟應當采取何種觀點呢?
我國物權法奉行物權法定原則,當事人不能在物權法之外消滅物權。作為擔保物權的抵押權,可因行使而消滅,可因所擔保的債權消滅而消滅,也可因抵押物的滅失而消滅,惟沒有當事人約定期限而消滅的。因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擔保法的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約定的或者登記部門要求登記的擔保期間,對擔保物權的存續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也就是說,該司法解釋否定了擔保期間在擔保物權存續上的任何意義。所以說,擔保物權在性質上主要不是債權請求權,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屬于支配權,故不應該適用時效規定。
在本案中,雖然作為借款合同的主合同中的債權罹于時效,但由于作為抵押權的期間對擔保物權的存續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即抵押合同中的抵押權并不適用時效規定,因而被告方的“主債權已過訴訟時效,作為從合同的擔保合同當然不受保護”的觀點便不能成立。所以,在本案的裁判結果中,并沒有保護已過訴訟時效的主債權,而是對原告所主張的抵押權給予了支持,是具有一定法理依據的。
四、關于擔保物權的存續期間問題
這個問題似乎與前一個問題相同,其實不然。前一個問題是解決擔保物權是否適用時效規定、是否有存續期間的問題,所要說明的是抵押權的存續期間總是存在,并不受當事人約定之約束,也不因時效而消滅,哪怕主債權時效已屆滿。而現在的問題是要解決實踐中的問題。
站在應用法學的角度上分析,抵押權的行使在實踐中又不能不受時間的限制,否則,抵押權人便會利用“抵押權無存續期間”之特征,濫用抵押權,從而永久限制抵押物之交易和使用。許多國家為解決這一問題,采取了各種制度對抵押權人加以限制。如德國,已取得時效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法國以訴訟時效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日本以訴訟時效與取得時效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我國的臺灣則以除斥期間來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我國的《擔保法》對限制行使擔保物權沒有明確規定,考慮到抵押物的流通和物之效能的發揮,本著社會經濟生活與司法實踐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的擔保法司法解釋及時地給于了補充,在表述上,以人民法院在何種條件下保護擔保物權為表述方法,避免了司法解釋的立法化性質。其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擔保物權所擔保的債權的訴訟時效結束后,擔保權人在訴訟時效結束后的二年內行使擔保物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從這個規定可以看出,我國采取了以除斥期間為限制擔保物權的行使的方法。這一解釋也被我國的學者所接受,如梁慧星教授主持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中就規定:“抵押權人自抵押所擔保的債權的訴訟時效完成后,經過二年不行使抵押權的,抵押權消滅。”王利明教授主持的《物權法草案建議稿》也規定:“抵押權人和抵押人沒有約定抵押權的存續期間或者其約定無效的,抵押權人之抵押擔保的債權的清償期滿后四年內不行使的,不得再實現抵押權。”兩個草案內容上有差異,但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
本案中,如果主債權的時效一直未超過,則抵押權也就一直存續,這本身并沒有問題。但由于主債權罹于時效,才帶來抵押權的行使期間問題。原告請求保護主債權的時效應當從2001年3月10日起算,截止于2003年3月10日。原告某支行因明知自己的主債權已超過訴訟時效,所以提起抵押權行使之訴。那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擔保法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第二款,為主債權擔保的抵押權的存續期間就應在2003年3月10日后兩年內,即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的截止期限應當為2005年3月10日。因此,本案原告某支行在抵押權行使的有效期間內行使抵押權,人民法院應當支持。此時的抵押權作為擔保物權,實際上是一個對已過訴訟時效的自然債權所作的有效擔保。所以在判決主文的表述上,應當判決被告嚴某在一定期限內將作為抵押物的房產變賣或交付拍賣,以所得價款為限優先向原告某支行清償債務。在這一點上,本案的判決在判決主文的表述上,似乎還有商榷的余地。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