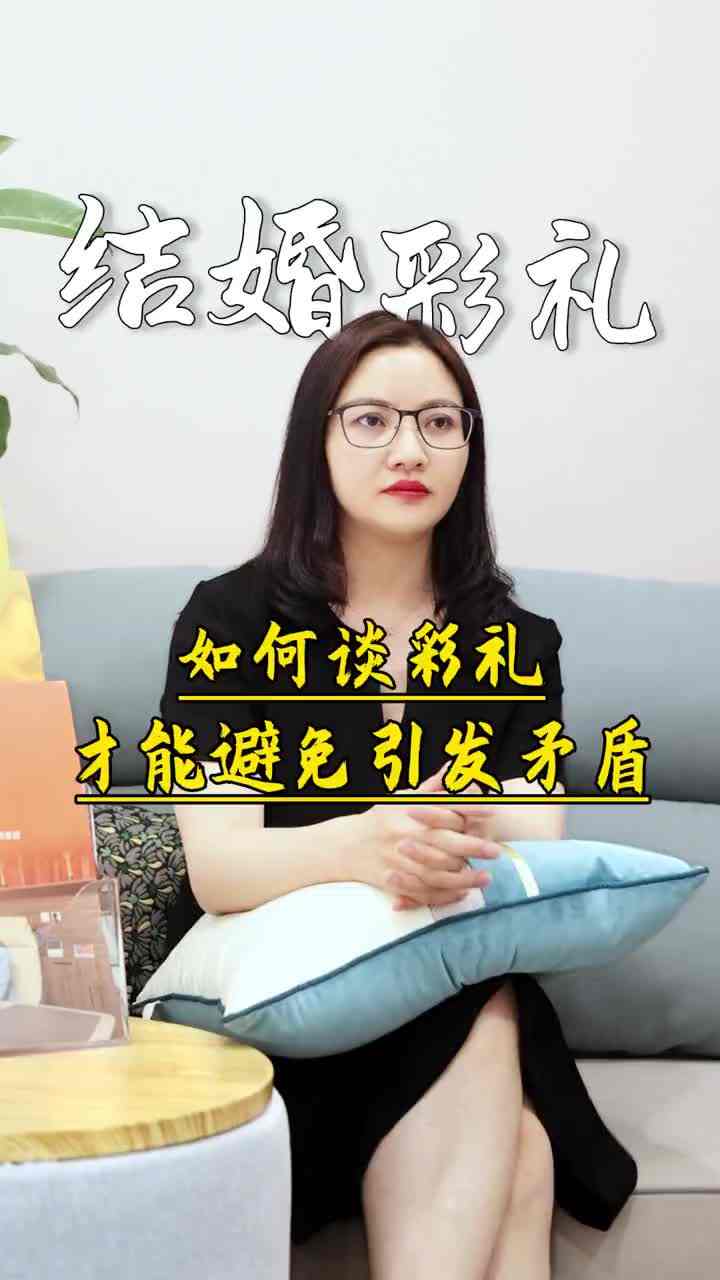一場由人才流動引發(fā)的官司
 孔孟廷律師2022.01.10598人閱讀
孔孟廷律師2022.01.10598人閱讀
導讀:
目前此案正由深圳市南山區(qū)檢察院審理。本周,庭審將基本結(jié)束,下一步將是等待法院的一審宣判。2003年6月17日,王等三位涉案人被深圳人民檢察院正式批準被捕。因此,華為認定該行為侵犯華為公司商業(yè)機密。2002年11月11日,王志駿等三人加入ut斯達康,2002年11月19日,收到來自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傳票。2002年11月19日,3人被拘之前,滬科公司接到由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所發(fā)的、華為起訴滬科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民事訴訟傳票,案由是不正當競爭。那么一場由人才流動引發(fā)的官司。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guān)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目前此案正由深圳市南山區(qū)檢察院審理。本周,庭審將基本結(jié)束,下一步將是等待法院的一審宣判。2003年6月17日,王等三位涉案人被深圳人民檢察院正式批準被捕。因此,華為認定該行為侵犯華為公司商業(yè)機密。2002年11月11日,王志駿等三人加入ut斯達康,2002年11月19日,收到來自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傳票。2002年11月19日,3人被拘之前,滬科公司接到由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所發(fā)的、華為起訴滬科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民事訴訟傳票,案由是不正當競爭。關(guān)于一場由人才流動引發(fā)的官司的法律問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今年有一個案子被多家媒體廣泛關(guān)注,就是華為公司起訴三名前員工分別為上海滬科公司、ut斯達康公司員工涉嫌盜竊商業(yè)機密、侵害知識產(chǎn)權(quán)。該案件被曝光之后,在各界引起較大爭議和反響。目前此案正由深圳市南山區(qū)檢察院審理。
有報道稱,三員工竊取華為公司幾萬頁的技術(shù)資料,并用于與上海貝爾公司的合作中,后又將其賣給ut斯達康,從中獲取巨大利潤。被告的辯護律師否認這一說法,稱幾萬頁的資料中絕大部分已被公安機關(guān)委托鑒定為沒有密級的普通資料,而非商業(yè)秘密;同時,轉(zhuǎn)讓給ut斯達康的部分技術(shù)資產(chǎn)也與本案所涉商業(yè)秘密無關(guān)。在庭審中,三辯護律師認為深圳警方辦案過程“滴水不漏”,而公訴方出示調(diào)取的佳木斯警方所取證據(jù),獲取形式不合法,存在嚴重瑕疵。本周,庭審將基本結(jié)束,下一步將是等待法院的一審宣判。按照相關(guān)規(guī)定,最遲在庭審結(jié)束后兩個半月將進行宣判,因而三人是否有罪,在9月底將初見分曉。
2001年7月,華為公司光網(wǎng)絡(luò)傳輸部研發(fā)部的王志駿、劉寧、秦學軍離開華為,成立了上海滬科科技有限公司,2002年10月,華為公司向佳木斯公安局報案,稱含滬科sdh技術(shù)的光傳輸產(chǎn)品與華為產(chǎn)品頗為相似,有涉嫌盜竊華為商業(yè)技術(shù)的嫌疑,佳木斯警方隨后立案展開調(diào)查。2002年11月21、22日,王等三人分別被拘留。2002年12月18日,該案被移交到深圳司法機關(guān)。2003年6月17日,王等三位涉案人被深圳人民檢察院正式批準被捕。
在華為看來,滬科公司能夠在短時間內(nèi)開發(fā)出與華為技術(shù)頗具競爭力的產(chǎn)品,最大的原因在于三位員工從華為公司帶走了大量的技術(shù)秘密,而這三人在加入公司時就簽署了同業(yè)競爭禁止協(xié)議,在離職時也簽署過保密協(xié)議。因此,華為認定該行為侵犯華為公司商業(yè)機密。
此間一個不可忽略的事件是,2002年10月16日ut斯達康公司以1500萬美元?含期權(quán)的價格收購了滬科光傳輸技術(shù)這部分資產(chǎn)。2002年11月11日,王志駿等三人加入ut斯達康,2002年11月19日,收到來自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傳票。2天之后,王等三人被拘捕。隨后華為將訴訟轉(zhuǎn)移到深圳市當?shù)厮痉C關(guān),對三位員工的訴訟也由原來的不正當競爭上升到盜竊商業(yè)機密并提請刑事立案。
華為公司發(fā)言人傅軍說,sdh光傳輸技術(shù)是華為于1995年開始投入研發(fā)的光網(wǎng)絡(luò)重點技術(shù)之一,每年華為都將該產(chǎn)品銷售的10%返還為研發(fā)費用,至2001年10月累計投入了2億多人民幣和1500名技術(shù)人員。“而滬科在一年不到的時間里,就可以研發(fā)出價值1500萬美元的技術(shù),這不得不令人存疑。”傅稱。
有關(guān)律師認為,案件已經(jīng)不能被理解為一個單純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糾紛,更深層次如商業(yè)利益和競爭策略的因素已經(jīng)表露明顯。知識產(chǎn)權(quán)糾紛,通常有3種解決方式。一種是采取民事訴訟的方式,有什么問題,雙方作為平等的民事主體,在民事法庭上解決糾紛;第二種是行政救助,即以向工商部門舉報、由工商機關(guān)查處的方式,中止侵權(quán)行為;最后一種就是刑事救助,即向公安機關(guān)報案。司法實踐上,有80%?90%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糾紛是以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的。這主要是因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案件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所決定的。通常,對于受理涉及侵犯商業(yè)秘密的案件,公關(guān)機關(guān)的態(tài)度是非常謹慎的。而這一次,華為是民事訴訟與刑事救助雙線同時進行。2002年11月19日,3人被拘之前,滬科公司接到由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所發(fā)的、華為起訴滬科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民事訴訟傳票,案由是不正當競爭。正在滬科積極準備應訴的時候,11月21日,即是滬科接到法院傳票2天之后,3人卻幾乎同時被拘捕。3人被拘后,華為立即從法院撤銷了他們提起的民事訴訟。
在涉案的第三方公司ut斯達康看來,對滬科公司的收購只是一場自愿互惠的商業(yè)行為,ut斯達康希望通過對滬科的收購鞏固其光網(wǎng)絡(luò)業(yè)務的競爭力。被認為以小靈通業(yè)務起家的ut斯達康近幾年來正加速朝著綜合電信服務商的目標快速擴張,與華為之間的業(yè)務重合和競爭也越來越頻繁。但讓ut斯達康始料不及的是,原本寄予促進業(yè)務發(fā)展的收購在現(xiàn)在看來似乎成了棘手的商業(yè)陷阱,盡管公司反復強調(diào),在滬科的并購案中,完全按照上市公司收購程序進行的,進行了嚴密的技術(shù)鑒定和審核。
不管案件最終的結(jié)果如何,對華為,對ut斯達康乃至所有企業(yè)來說,這個問題都是值得反思的,在員工尤其是掌握核心技術(shù)和機密的員工的流動管理中,如何更好地保護商業(yè)機密和知識產(chǎn)權(quán)以降低不必要的損失?
《保密協(xié)議》和《同業(yè)競爭禁止條例》被認為是主要手段。一般來說,公司會要求員工在一定時間之內(nèi),不能以任何方式從事同一行業(yè)的工作,作為對這種義務的交換,公司亦要給員工支付一定的補償。而同理,公司在吸納來自競爭對手公司的員工,亦要由員工給出不違反原公司商業(yè)秘密的承諾。
這個案子的意義不僅在于3人是否侵犯了華為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它留給業(yè)界乃至整個中國企業(yè)界的意義是巨大的。首先,利用法律措施保護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做法,將成為中國企業(yè)越來越多的選擇。其次,企業(yè)在保護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過程中,如何處理與員工的關(guān)系?一般地,企業(yè)的員工,尤其是部分技術(shù)人員和管理者,往往掌握著一個企業(yè)的技術(shù)或客戶資源。他們離職后如果再次進入同一行業(yè),尤其是在前企業(yè)的競爭者那里就業(yè),極有可能使其擁有的資源遷移到新的企業(yè)中。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問題,便由此產(chǎn)生。
同樣引人關(guān)注的是華為制定的離職員工保密協(xié)議書,被許多人稱為“不平等條約”。保密協(xié)議的第二條這樣寫道,“自離職之日起3年內(nèi)不在研究、生產(chǎn)、銷售或者維護華為公司經(jīng)營的同類通訊產(chǎn)品?包括程控交換機、光網(wǎng)絡(luò)通訊產(chǎn)品、無線通訊產(chǎn)品、數(shù)據(jù)通訊產(chǎn)品、寬帶多媒體產(chǎn)品、微電子產(chǎn)品、系統(tǒng)集成工程、計算機與配套設(shè)備、終端設(shè)備與相關(guān)的設(shè)備及維修、通訊電源、技術(shù)咨詢服務、其他網(wǎng)絡(luò)產(chǎn)品、其他通訊產(chǎn)品等且與華為公司有競爭關(guān)系的企業(yè)或事業(yè)單位中工作,且不以任何方式間接地為上述企業(yè)或事業(yè)單位工作”。不少人對此質(zhì)疑道:作為一個技術(shù)人員,離開華為之后,不做這行他(她)能做什么?公司強迫離職人員簽訂“不平等條約”,本身是不公平的。
對此,當事人家屬的律師臧煒談到,保密協(xié)議雖然是由雙方簽訂,但也要符合國家法律的規(guī)定。如果保密協(xié)議違反國家法律、無視公平,這樣的協(xié)議或條款是無效的。在保密協(xié)議中,還涉及到商業(yè)秘密的范圍,如果這個范圍特別廣,涵蓋了公知領(lǐng)域的信息,這樣的條款也是無效的。很明顯地,華為保密協(xié)議中的保密范圍已經(jīng)將整個it通信制造業(yè)一網(wǎng)打盡。如果嚴格地遵照整個協(xié)議,離職人員除了改行,沒有別的選擇。
對于這份被稱為“不平等條約”的保密協(xié)議,華為有關(guān)人士回應道,備受指責的保密協(xié)議第二條實際上是“競業(yè)條款”。在協(xié)議中,還有一條重要的保密條款,即 “不帶走載有華為公司秘密信息的一切載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凡記錄華為公司秘密信息的文件、資料、圖表、筆記、報告、傳真、磁帶、磁盤、儀器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載體,不將這些載體及復制件擅自保留或交給其他任何人”。滬科事件則適用于“保密條款”,王、劉、秦的被捕,是由于華為認定“3人帶走大量的商業(yè)機密”。

相信這一事件不是最后一件關(guān)于員工流動中涉及商業(yè)秘密的糾紛。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