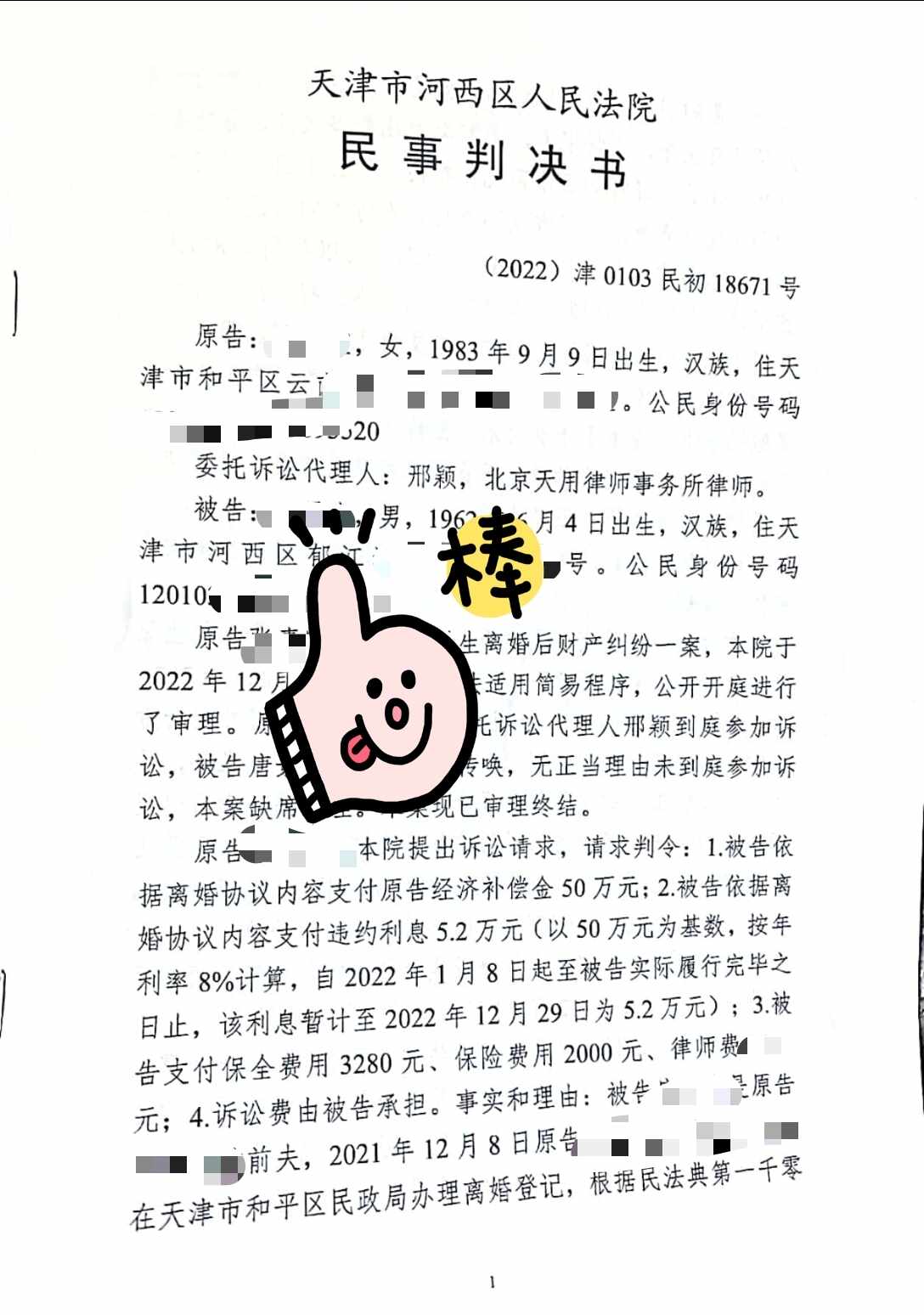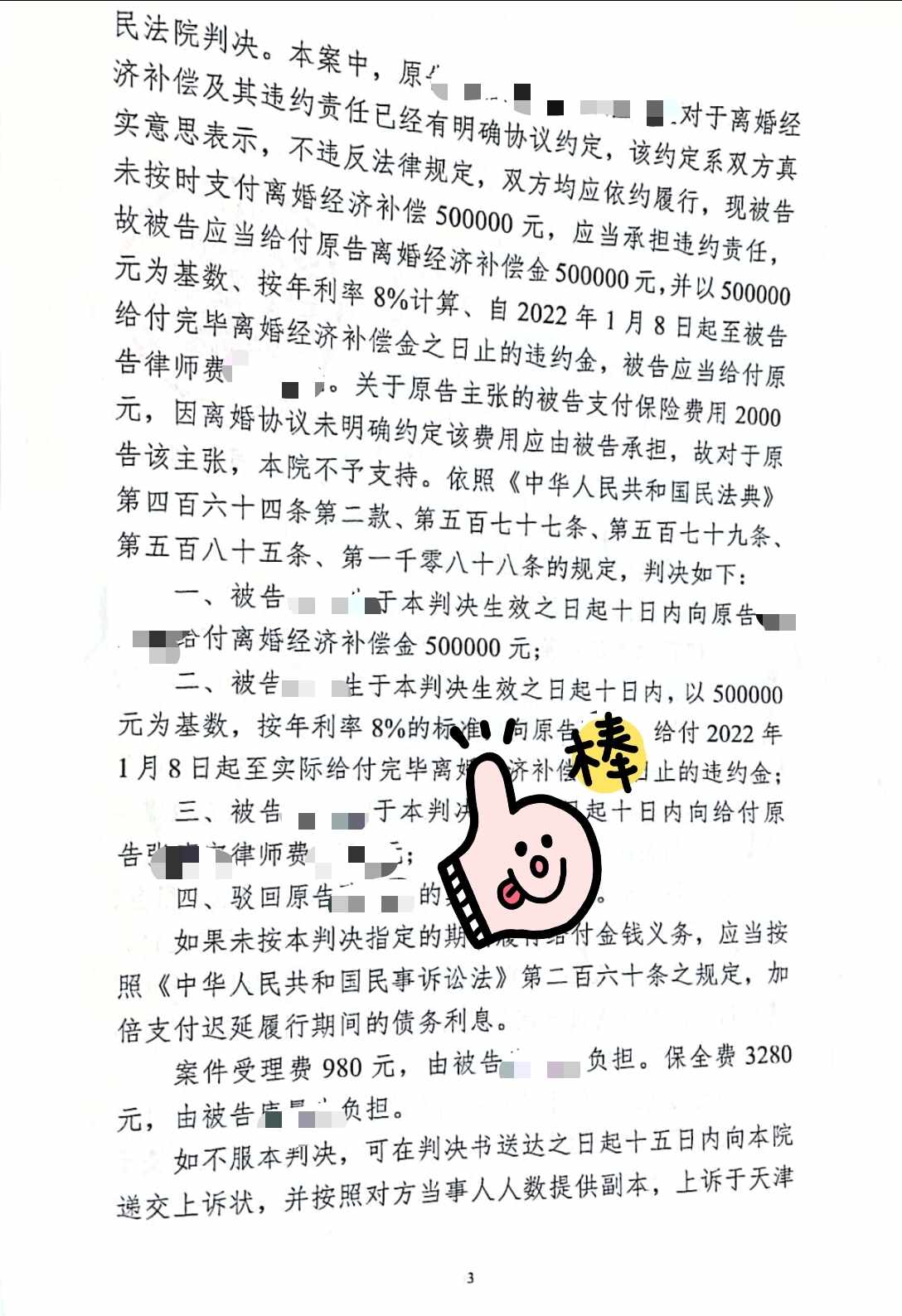違約金約定過高時如何確定違約金的數額
 孔孟廷律師2021.12.29120人閱讀
孔孟廷律師2021.12.29120人閱讀
導讀:
《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又規定:“……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的,當事人可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即一般高于實際損失則無權請求減少,這一方面是為了免除當事人舉證的繁瑣,另一方面表明法律允許違約金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損失,顯然大于部分具有對違約方的懲罰性。一審宣判后,義烏市海洋拉鏈有限公司提出上訴,經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是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是否過高?(一)違約金的性質違約金是指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或者法律直接規定,一方當事人違約的,應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錢。那么違約金約定過高時如何確定違約金的數額。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又規定:“……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的,當事人可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即一般高于實際損失則無權請求減少,這一方面是為了免除當事人舉證的繁瑣,另一方面表明法律允許違約金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損失,顯然大于部分具有對違約方的懲罰性。一審宣判后,義烏市海洋拉鏈有限公司提出上訴,經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是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是否過高?(一)違約金的性質違約金是指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或者法律直接規定,一方當事人違約的,應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錢。關于違約金約定過高時如何確定違約金的數額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違約金約定過高時如何確定違約金的數額?《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又規定:“……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的,當事人可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即一般高于實際損失則無權請求減少,這一方面是為了免除當事人舉證的繁瑣,另一方面表明法律允許違約金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損失,顯然大于部分具有對違約方的懲罰性。
【案情】
2011年7月18日,原、被告雙方為進行資源整合、優勢互補,簽訂了一份《企業合作(重組)合同》,原告為乙方,被告為甲方。2011年7月19日,雙方又簽訂了一份《補充協議》。《企業合作(重組)合同》約定:
1、合作(重組)的資產為雙方的所有固定資產,原告公司作為企業的生產基地,合作(重組)開始后,被告現有的所有機器設備搬遷至原告公司住所地,形成前后道拉鏈生產、染色、拉頭壓鑄一條龍式的生產鏈,在義烏國際商貿城設立銷售點,作為企業銷售、采購的門面和窗口;
2、合作(重組)后,企業的股權變更為朱銀仙分別占甲、乙兩個公司股份的51.8%,江長生分別占甲、乙兩個公司股份的48.2%;
3、雙方一致同意在條件成熟時,將兩個公司合并,合并更名前以兩個公司名稱經營,甲方公司主要經營銷售,乙方公司主要經營生產;
4、違約方必須向守約方支付500萬元違約金;
5、合作(重組)開始日為2012年1月1日。
《補充協議》約定:
1、機器設備中碼裝設備現有40余套,須新增60套,壓鑄設備現有2套,須新增4套,其他設備暫不增加;
2、投資資金包括原有資金和新增資金,其中原有資金為甲乙雙方的全部投資(甲方投資額為搬遷至乙方公司的全部機器設備價值約518萬元,乙方投資額為土地、房屋、基礎設施、機器設備和配套設施減去1750萬元融資貸款的差額約為482萬元),新增資金即為完成年度經濟目標需要增加投放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金投資,包括新增機器設備60套,投資約為310萬元,碼裝拉鏈生產流動資金投資約為270萬元,新建廠房2000平方米左右投資約為120萬元,新建辦公樓投資約為100萬元,條裝拉鏈生產流動資金投資約為300萬元。
《補充協議》還對合作(重組)后企業的經濟目標經營管理、資金籌措和利潤分配等作出了具體的約定。《企業合作(重組)合同》及《補充協議》簽訂后,原告方即著手按合同約定新建廠房及辦公樓共5979.96㎡。2011年8月24日,被告法定代表人朱銀仙以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對外簽訂《設備購銷合同》,由原告墊資322.6萬元購進了一批碼裝設備,設備安裝后原告開始進行生產,并將生產出來的拉鏈產品交給被告銷售,之后,被告提出不將在義烏國際商貿城的銷售門面及銷售業務列入合作(重組),繼而又提出其后道生產設備不搬遷至原告處,最后拒絕繼續履行《企業合作(重組)合同》及《補充協議》。2011年底原告停止將拉鏈產品交由被告進行銷售,但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證據證明具體的銷售明細及銷售金額。
【判決】
江西省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2)鷹民二初字第14號民事判決:
一、被告義烏市海洋拉鏈有限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一次性支付原告江西鑫之海實業有限公司違約金250萬元;
二、駁回原告江西鑫之海實業有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一審宣判后,義烏市海洋拉鏈有限公司提出上訴,經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一是雙方簽訂的《企業合作(重組)合同》及《補充協議》是否有效?二是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是否過高?
(一)違約金的性質
違約金是指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或者法律直接規定,一方當事人違約的,應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錢。違約金的標準是金錢,但當事人也可以約定違約金的標的物為金錢以外的其他財產。關于違約金的性質,從學術上,目前有補償說、懲罰說、雙重說以及目的解釋說四種。從立法上,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對違約金的規定強調違約金補償性的理念,同時有限地承認違約金的懲罰性,無疑是承認了雙重說。
一方面,違約金的支付數額是“根據違約情況”確定的,即違約金的約定應當估計到一方違約而可能給另一方造成的損失,而不得約定與原來的損失不相稱的違約金數額。另一方面,如果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的數額低于違約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適當增加,以使違約金與實際損失大體相當。這明顯體現了違約金的補償性,將違約金作為一種違約救濟措施,既保護守約方的利益,又激勵當事人積極大膽從事交易活動和經濟流轉。
同時《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又規定:“……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的,當事人可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即一般高于實際損失則無權請求減少,這一方面是為了免除當事人舉證的繁瑣,另一方面表明法律允許違約金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損失,顯然大于部分具有對違約方的懲罰性。我國違約金具有補償為主,懲罰為輔的性質。
(二)實際損失的認定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第一款“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這說明,確定違約金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那么本案的損失應當如何計算。
1、違約金過高的證明責任。根據《民事訴訟法》關于證明責任的分配,應當由當事人對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并予以證明,若訴訟終結時根據全案證據仍不能判明當事人主張的事實真偽,則由該當事人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也就是說根據“誰主張誰證明”的原則,違約方應當主張違約金過高應當承擔證明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中規定:“違約方對于違約金約定過高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非違約方主張違約金約定合理的,亦應提供相應的證據。”也就是說,守約方也負有證明違約金合理的證明責任。
在本案審理中,被告提供原告2011年、2012年度公司年檢報告書,證明原告2011年和2012年均虧損,從而予以證實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而原告認為自己的實際損失遠遠大于500萬元,并提供了《廢舊鋼鐵買賣合同》,證明原告拆除了舊設備的花費;《建筑承包合同》,證明原告按照合同約定投資220萬元興建廠房和辦公樓;《設備購銷合同》,原告墊資322.6萬元購進設備的損失。經一審質證,法院認為,被告提供的證據僅能證明原告在合作經營期間的經營狀況,不能反映原告因被告違約所遭受的損失。
2、實際損失的確定。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之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也就是說實際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直接損失是守約方現有、直接財產的減少,間接損失就是可得利益的喪失,即已經預見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將來可得利益因違約方的違約行為而沒有得到的。
[page]
在案件中,原、被告雙方主張的違約金過高或者合理都沒有盡到完全的證明責任,故而法院依照合同的履行情況、雙方過錯等綜合認定。結合本案,根據合同約定及雙方的履行情況,對于原告主張的拆除舊設備損失,因合同中未約定,且拆除舊設備系安裝新設備之前提,不應支持;對于經營損失及預期利益損失,因無法查清銷售數量,合同中未約定利潤,且原告方在被告違約后沒有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也不應支持。
原告主張其按合同約定投資220萬元新建了5979.96M2的廠房及辦公樓,并提供了房屋產權證予以證明,被告對原告的這一主張未提出任何證據予以反駁,由于原告新建廠房及辦公樓的實際投資金額無法查清,本院采信合同約定的金額220萬元;被告認可是朱銀仙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對外簽訂了《設備購銷合同》,并由原告墊資322.6萬元購進了機器設備。
因此,原告的實際損失主要為新建廠房、辦公樓及購買機器設備的損失,其中新建廠房的損失表現為占用220萬元資金的利息損失,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從2011年8月計算至2013年12月,約為120萬元;購買機器設備的損失表現為固定資產折舊,設備總價款為322.6萬元,按平均年限法從2011年9月計算至2013年12月,為70余萬元。上述二項合計近200萬元,可以認定為原告鑫之海公司的實際損失。
3、違約金的確定。當確定了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時,違約金如何確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第二款還規定,“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認定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本案中,法院最終認定實際損失為200萬元左右,而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為500萬元,約定的違約金超過損失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屬于過分高于實際損失。
那么,應當如何認定具體的違約金呢?這屬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的范圍,不同的法官或許會有不同的比例。因此,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在本案中,原告依照合同的約定履行了自己的義務,包括新建廠房、辦公樓,購買新設備等等,而被告在合同履行中擅自終止合同的履行,是過錯方。因此法院最終以實際損失的200萬元,以不超過30%,也就是以實際損失的130%的上限為標準,確定了違約金250萬元。
(三)值得說明的問題
被告在答辯過程中,認為原告提供的廠房、辦公樓、食堂《建筑承包合同》,證明原告興建廠房的損失,被告提出質疑,認為原告獲準的6000平方米的廠房不僅不存在損失,反而具有升值空間。在這里存在一個問題,雙方在《合作協議》中約定原告投資220萬元用于擴建廠房,原告依照約定新建廠房,那么新建廠房的該部分是否屬于實際損失?
筆者認為,這部分仍然應當屬于實際損失的范圍,理由如下:一是被告屬于違約方,正如前述,違約金的性質是補償性和懲罰性雙重性質,即使廠房有升值的可能和空間,對原告投資200萬元新建廠房的利息損失仍然應當計入損失,否則難以促進有序交易。二是廠房的價值判斷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房,是否具有升值可能,以及升值多少不能簡單的參照商品房。三是從雙方訂立合同的階段看,本案是從合作經營逐步過渡到雙方企業的合并,如果原告認為廠房有升值空間,待合并后共同財產,被告可以選擇繼續履行合同。
(原標題:違約金約定過高時如何確定違約金的數額?)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