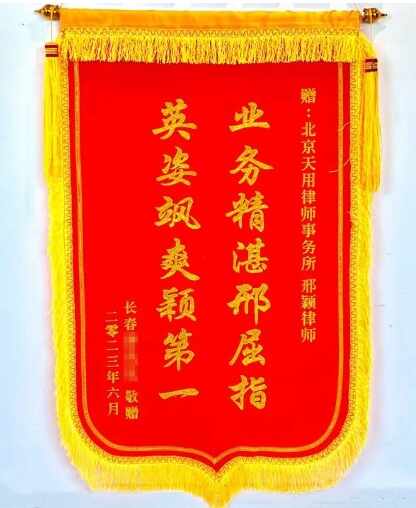一起施工合同糾紛的評(píng)析
 周春花律師2021.12.27484人閱讀
周春花律師2021.12.27484人閱讀
導(dǎo)讀:
2009年3月25日,該建筑公司向中院起訴要求解除原被告間的施工合同。2009年5月31日,中院裁定建筑公司在裁定書送達(dá)之日起5日內(nèi)退場(chǎng)。建筑公司提起復(fù)議,2009年6月5日,中院裁定中止執(zhí)行2009年5月31日的裁定。同年12月31日,中院作出一審判決解除原被告簽訂的施工合同,雙方當(dāng)事人均提起上訴。本案已經(jīng)由中院裁定,中院已經(jīng)對(duì)本案行使管轄權(quán),現(xiàn)該案已上訴至高院。但是,鑒于原告的訴訟請(qǐng)求的基礎(chǔ)是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已經(jīng)解除,而目前高院尚未對(duì)合同是否解除做出終審判決,現(xiàn)基層法院不宜立即下裁定。那么一起施工合同糾紛的評(píng)析。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guān)知識(shí),希望能幫助大家。
2009年3月25日,該建筑公司向中院起訴要求解除原被告間的施工合同。2009年5月31日,中院裁定建筑公司在裁定書送達(dá)之日起5日內(nèi)退場(chǎng)。建筑公司提起復(fù)議,2009年6月5日,中院裁定中止執(zhí)行2009年5月31日的裁定。同年12月31日,中院作出一審判決解除原被告簽訂的施工合同,雙方當(dāng)事人均提起上訴。本案已經(jīng)由中院裁定,中院已經(jīng)對(duì)本案行使管轄權(quán),現(xiàn)該案已上訴至高院。但是,鑒于原告的訴訟請(qǐng)求的基礎(chǔ)是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已經(jīng)解除,而目前高院尚未對(duì)合同是否解除做出終審判決,現(xiàn)基層法院不宜立即下裁定。關(guān)于一起施工合同糾紛的評(píng)析的法律問(wèn)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合同糾紛律師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shí),希望能幫助大家。
【基本案情】:
原告某置業(yè)有限公司和被告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07年11月10日簽訂了《建設(shè)工程施工合同》,約定原告將自行開(kāi)發(fā)的某工程發(fā)包給被告修建。2009年3月25日,該建筑公司向中院起訴要求解除原被告間的施工合同。在案件審理過(guò)程中,置業(yè)公司與建筑工程公司就撤場(chǎng)問(wèn)題進(jìn)行了磋商。2009年5月31日,中院裁定建筑公司在裁定書送達(dá)之日起5日內(nèi)退場(chǎng)。建筑公司提起復(fù)議,2009年6月5日,中院裁定中止執(zhí)行2009年5月31日的裁定。同年12月31日,中院作出一審判決解除原被告簽訂的施工合同,雙方當(dāng)事人均提起上訴。但建筑公司至今拒不撤離施工現(xiàn)場(chǎng)。現(xiàn)置業(yè)公司訴至工程所在地基層法院,要求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立即撤離該項(xiàng)目施工現(xiàn)場(chǎng),并將該施工地及已完成工程交付原告。被告在舉證期限內(nèi)以撤場(chǎng)問(wèn)題已由中院裁定,案件應(yīng)由高院管轄為由向基層法院提出管轄權(quán)異議申請(qǐng),主張?jiān)摶鶎臃ㄔ簩?duì)該訴訟無(wú)管轄權(quán),要求將本案移送至高院管轄。
【處理意見(jiàn)】:
對(duì)該案如何處理,形成三種處理意見(jiàn)。第一種處理意見(jiàn)認(rèn)為:基層法院不應(yīng)受理,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本案已經(jīng)由中院裁定,中院已經(jīng)對(duì)本案行使管轄權(quán),現(xiàn)該案已上訴至高院。根據(jù)《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五項(xiàng)所體現(xiàn)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基層法院理應(yīng)不再受理,裁定駁回原告起訴。第二種處理意見(jiàn)認(rèn)為:基層法院應(yīng)裁定對(duì)本案有管轄權(quán),繼續(xù)審理。根據(jù)民事訴訟法相關(guān)規(guī)定,判決的做出必須以原告的訴訟請(qǐng)求為前提。該某置業(yè)有限公司并沒(méi)有在中院審理案件過(guò)程中提出反訴,中院判決也沒(méi)有涉及撤場(chǎng)的內(nèi)容。所以雖然中院裁定被告退場(chǎng),并不影響基層法院對(duì)該案的管轄權(quán),因此應(yīng)裁定對(duì)該案具有管轄權(quán),繼續(xù)審理。第三種處理意見(jiàn)認(rèn)為:基層法院應(yīng)裁定中止訴訟,等待高院最終判決。雖然根據(jù)《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五項(xiàng)規(guī)定,基層法院應(yīng)該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裁定駁回起訴。但是,鑒于原告的訴訟請(qǐng)求的基礎(chǔ)是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已經(jīng)解除,而目前高院尚未對(duì)合同是否解除做出終審判決,現(xiàn)基層法院不宜立即下裁定。再加上中院所作出的裁定的合法性有待商榷,高院有可能會(huì)撤銷此裁定。若簡(jiǎn)單裁定駁回起訴,就會(huì)使當(dāng)事人陷入訴訟無(wú)門的尷尬境地,造成事實(shí)與法律的嚴(yán)重不符,有損司法公正與權(quán)威。因此在對(duì)法律效果和社會(huì)效果綜合考量之后,基層法院不宜立即裁定是否駁回原告起訴,而應(yīng)該裁定中止訴訟,等待高院判決。
【評(píng)析】:
對(duì)本案的處理,之所以會(huì)產(chǎn)生三種不同的意見(jiàn),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與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筆者認(rèn)為第三種處理意見(jiàn)較為適宜,即本案應(yīng)該使用一事不再理原則,但是又不能立即裁定駁回,而應(yīng)中止訴訟,等待高院終審判決,理由如下:
一事不再理原則起源于古羅馬人對(duì)“審判”結(jié)果的敬畏,后又逐漸發(fā)展為羅馬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在羅馬法中,一事不再理原則包含了訴訟系屬的效力與判決的既判力兩層涵義,具體來(lái)講即時(shí)當(dāng)案件尚在訴訟系屬時(shí),被告可以針對(duì)原告的雙重起訴實(shí)施“訴訟系屬的抗辯”,使原告的所能夠請(qǐng)求不至于產(chǎn)生訴訟系屬之效;當(dāng)案件的訴訟系屬已因判決確定而消滅時(shí),被告對(duì)原告方的再次起訴可以實(shí)施“既判案件的抗辯”,是原告方的訴訟請(qǐng)求不能系屬于法院。[1]一事不再理原則發(fā)展至今,在對(duì)其進(jìn)行定義時(shí),產(chǎn)生了狹義說(shuō)與廣義說(shuō)之分歧。狹義說(shuō)認(rèn)為一事不再理原則僅指判決的既判力,既判決確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訴,如我國(guó)《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五項(xiàng)之規(guī)定:“對(duì)判決、裁定已將發(fā)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dāng)事人又起訴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訴處理,……”;廣義說(shuō)則認(rèn)為一事不再理原則仍將訴訟系屬的效力和裁判的既判力視為一事不再理的兩層涵義,不僅判決確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訴,而且訴訟已經(jīng)提起就不得以同一案件再次起訴,關(guān)于訴訟系屬的效力如《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之規(guī)定,“對(duì)于正在法院系屬中的案件,當(dāng)事人不得重復(fù)提起訴訟。”,此即為“禁止二重起訴原則”。從一事不再理原則的起源來(lái)看,廣義說(shuō)更能體現(xiàn)該原則的歷史演變進(jìn)程;但我國(guó)立法長(zhǎng)期秉承狹義說(shuō),認(rèn)為一事不再理原則僅包含判決的既判力,縮小了一事不再理的內(nèi)涵,有失偏頗。
但是案件的審理必須以法律為準(zhǔn)繩,特別是在成文法國(guó)家,因此本案的處理只能依照我國(guó)民事訴訟法之規(guī)定,其中對(duì)“一事”并不存在爭(zhēng)議,本案的焦點(diǎn)也就為中院所做的裁定是否具有既判力。

既判力即是指終局判決一旦獲得確定,該判決對(duì)請(qǐng)求之判斷就成為規(guī)范今后當(dāng)事人之間法律關(guān)系的基準(zhǔn),當(dāng)同一事項(xiàng)再度成為問(wèn)題時(shí),當(dāng)事人不能對(duì)該判斷提出爭(zhēng)議、不能提出與之相矛盾的主張,法院也不能做出與該判斷相矛盾或抵觸之判斷。[2]早期,發(fā)生既判力的裁判形式是確定判決,判決已經(jīng)確定后,無(wú)論其對(duì)與否,當(dāng)事人及法院均受同一判決內(nèi)容約束,不得就判決內(nèi)容再次起訴。這是源于對(duì)國(guó)家司法權(quán)力強(qiáng)制性的認(rèn)可和對(duì)當(dāng)事人及其訴權(quán)的尊重。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司法實(shí)踐開(kāi)始要求理論界對(duì)裁定是否具有既判力的問(wèn)題作出回答。裁定一般分為訴訟裁定和非訴裁定,由于本案分析需要,縣重點(diǎn)討論訴訟裁定的既判力問(wèn)題。對(duì)該問(wèn)題我國(guó)學(xué)界存在三種學(xué)說(shuō),裁定既判力否定說(shuō)、裁定既判力肯定說(shuō)和裁定既判力限制說(shuō)。
裁定既判力夠定說(shuō)認(rèn)為我國(guó)裁定多數(shù)針對(duì)程序性事項(xiàng),少說(shuō)裁定涉及實(shí)體問(wèn)題但又不是針對(duì)訴訟標(biāo)的法律關(guān)系作出的,因此裁定不具有既判力。此說(shuō)顯然未顧及到民事訴訟對(duì)裁定所判斷特定事項(xiàng)必須具有約束力的實(shí)際需要,缺乏實(shí)踐意義。裁定既判力肯定說(shuō)則認(rèn)為民事判決、裁定一經(jīng)生效,非經(jīng)法律程序不得改變,就應(yīng)該對(duì)法院、當(dāng)事人和社會(huì)一般人產(chǎn)生約束力。這里似乎賦予裁定與判決一樣的完全的既判力,又有絕對(duì)化之嫌。裁定既判力限制說(shuō)認(rèn)為無(wú)論裁定是針對(duì)程序問(wèn)題還是實(shí)體問(wèn)題,均具有既判力,但是不同客體的裁定,其既判力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一般說(shuō)來(lái),其基本立場(chǎng)體現(xiàn)為只要裁定是發(fā)生法律效力,且具有終局性,就應(yīng)該賦予其既判力,無(wú)論該裁定是針對(duì)程序性事項(xiàng)還是實(shí)體性事項(xiàng)。相較而言,筆者認(rèn)為限制說(shuō)更加合情合理,既承認(rèn)部分裁定的既判力,又未將既判力效果過(guò)分?jǐn)U大,是綜合考量法律與實(shí)踐的結(jié)果。[3] [page]
結(jié)合上述結(jié)論,我國(guó)《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規(guī)定的裁定種類中,如不予受理的裁定、對(duì)管轄權(quán)有異議的裁定、駁回起訴的裁定、準(zhǔn)許撤回上訴的裁定、鐘姐訴訟的裁定等因?yàn)閷?duì)所涉事項(xiàng)具有終局性效力,因此一般都承認(rèn)其具有既判力;而類似于財(cái)產(chǎn)保全裁定、限于執(zhí)行的裁定、中止訴訟的裁定、準(zhǔn)許撤回起訴的裁定、補(bǔ)正判決書中的筆誤的裁定,因其可能在訴訟過(guò)程中被法院更正不具有終局性而不應(yīng)有既判力。本案中,中院對(duì)被告退場(chǎng)事宜作出裁定是對(duì)雙方當(dāng)事人實(shí)體權(quán)利義務(wù)的確定,該裁定一經(jīng)作出立即生效,并不會(huì)隨著訴訟的進(jìn)程需要而改變,因此該裁定是對(duì)撤場(chǎng)事宜的終局性裁判。雖然被中止執(zhí)行,但是并不影響裁定對(duì)該事項(xiàng)的終局性效力,因此該裁定理應(yīng)具有既判力。根據(jù)一事不再理原則之規(guī)定,基層發(fā)法院應(yīng)當(dāng)駁回原告之起訴。
筆者之所以又主張不宜立即裁定駁回起訴,乃法律規(guī)定與社會(huì)效果之博弈的結(jié)果。
首先,裁定被告限期撤場(chǎng)的前提是原、被告之間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已經(jīng)解除,否則在合同存續(xù)期間,被告是有權(quán)利占據(jù)施工現(xiàn)場(chǎng)的。雖然中院已經(jīng)判決解除雙方之間的合同,但是目前案件已上訴至高院,即是說(shuō)一審判決效力并未生效,《建筑施工合同》也尚未解除,那么,中院作出裁定的基礎(chǔ)法律關(guān)系未確定。如若二審改判,維持合同效力,則中院責(zé)令被告限期撤場(chǎng)的裁定無(wú)疑是公權(quán)力對(duì)公民權(quán)利的嚴(yán)重侵害,終審判決與中院之裁定相互矛盾,會(huì)使當(dāng)事人對(duì)司法公正產(chǎn)生質(zhì)疑,消弱司法權(quán)威。
其次,中院之裁定的合法性也是值得商榷的,高院可能會(huì)撤銷此裁定。在民事訴訟中,當(dāng)事人的訴訟請(qǐng)求決定了法官所作裁判的行使和內(nèi)容。在案件審理中,除非當(dāng)事人的行為違反法律規(guī)定,或者法律明文規(guī)定法院應(yīng)當(dāng)行使國(guó)家干預(yù)權(quán),法官一般都應(yīng)該根據(jù)當(dāng)事人的訴訟請(qǐng)求作出相應(yīng)的裁判。在本案中,原告并未在前訴中提起要求被告撤場(chǎng)的訴訟請(qǐng)求,在沒(méi)有訴訟請(qǐng)求的情況下,中院作出責(zé)令被告限期撤場(chǎng)的裁定的基礎(chǔ)何在?因此,中院作出的裁定本身的合法性有待商榷,高院在對(duì)案件事實(shí)與法律適用的審查過(guò)程中,有可能會(huì)撤銷該裁定。那時(shí)高院未對(duì)被告撤場(chǎng)問(wèn)題作出判決,原告訴至基層法院,基層法院又已經(jīng)駁回起訴,就造成原告陷入訴訟無(wú)門的尷尬境地。
在本案中,如果嚴(yán)格遵守法律規(guī)定,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不僅不能解決糾紛,還可能對(duì)整個(gè)社會(huì)秩序造成不良影響。因此,筆者認(rèn)為,在對(duì)法律規(guī)定和社會(huì)效果的綜合考量之后,對(duì)本案的處理應(yīng)該采取第三種處理意見(jiàn),即應(yīng)中止訴訟,等待高院的終審判決。
最后,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gè)假設(shè),如果原告在中院一審過(guò)程中提起反訴,中院針對(duì)其訴訟請(qǐng)求作出一審判決,現(xiàn)案件上訴至高院,本案又應(yīng)該如何處理,是否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是否還是應(yīng)該中止訴訟,等待高院判決?
如前所述,我國(guó)《民事訴訟法》采納狹義一事不再理的定義,僅承認(rèn)已經(jīng)發(fā)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既判力,而沒(méi)有就前訴法院已經(jīng)受理還未作出判決的案件,是否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作出相關(guān)規(guī)定。本案中,如果原告曾在中院一審過(guò)程中提起反訴,現(xiàn)案件進(jìn)入二審程序,尚未終結(jié),就不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的規(guī)定,法院應(yīng)該受理。但是從一事不再理原則的起源來(lái)看,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重復(fù)起訴,避免司法裁判相互矛盾。若法院裁定繼續(xù)審理此案,無(wú)疑是開(kāi)了允許重復(fù)起訴的先河,任何案件只要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決,當(dāng)事人就可以再次提起起訴,而法院在一般情況下還必須受理,這必然將導(dǎo)致無(wú)法估計(jì)得司法資源的浪費(fèi),而且勢(shì)必會(huì)影響整個(gè)秩序的安定。在司法實(shí)踐過(guò)程中,在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使用中,理應(yīng)適當(dāng)考慮適用“禁止二重起訴”原則,賦予我國(guó)一事不再理原則訴訟系屬的效力,對(duì)前訴法院正在審理的案件,法院不應(yīng)受理。
結(jié)語(yǔ):
我國(guó)民事訴訟法僅規(guī)定狹義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并未對(duì)前訴尚未作出判決時(shí)原告再次起訴的情況是否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作出相關(guān)規(guī)定。但是在司法實(shí)務(wù)中,司法機(jī)關(guān)往往會(huì)根據(jù)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應(yīng)由涵義來(lái)決定是否受理起訴的案件,這是因?yàn)樵诜梢?guī)定和社會(huì)效果的博弈中,法官選擇了社會(huì)效果而非法律規(guī)定。我們可以看到法官在司法裁判的過(guò)程中,首先應(yīng)當(dāng)嚴(yán)格依照我國(guó)法律的相關(guān)規(guī)定,這事毋庸置疑的,但是法官又不能僅僅考慮法律效果而忽視了社會(huì)效果,這是由我國(guó)立法尚不完善的國(guó)情所決定的。將法律規(guī)定與社會(huì)效果結(jié)合考慮,不僅有利于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還有利于保證司法公正,加強(qiáng)司法權(quán)威,能夠最大程度的解決社會(huì)糾紛,是構(gòu)建和諧司法的重要舉措。另一方面,社會(huì)效果往往游離于法律之外,法官僅從社會(huì)效果的角度進(jìn)行裁判,實(shí)質(zhì)上也是對(duì)法律的背棄,對(duì)法律來(lái)說(shuō),無(wú)疑是給了其當(dāng)頭一棒。所以,在對(duì)法律規(guī)定與社會(huì)效果進(jìn)行權(quán)衡時(shí),社會(huì)效果的不確定性就要求法官的態(tài)度必須要慎重,不能讓社會(huì)效果成為某些法官枉法裁判的借口,在根本上動(dòng)搖法律的尊嚴(yán)。
陳波 李成玲
 點(diǎn)贊
點(diǎn)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