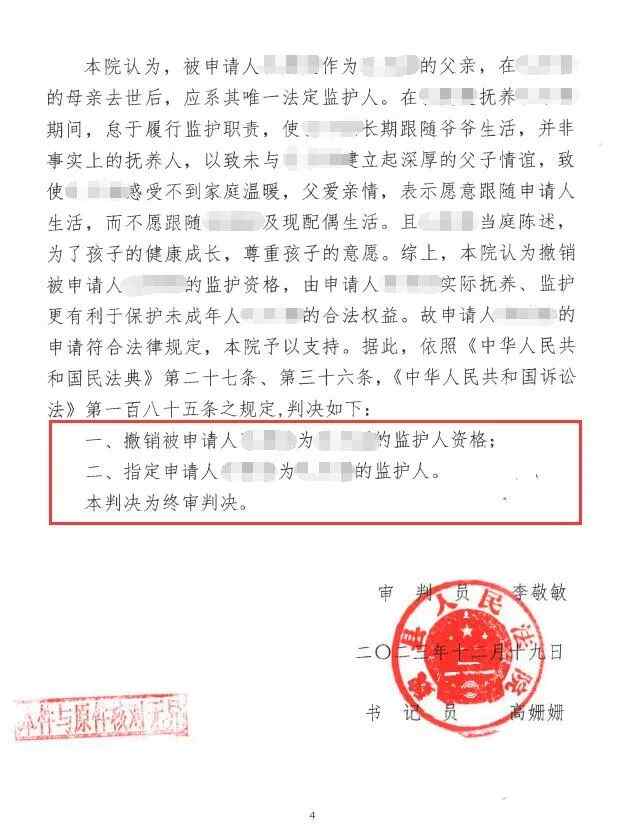論離婚后父母對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
 崔玉君律師2021.12.19364人閱讀
崔玉君律師2021.12.19364人閱讀
導讀:
論離婚后父母對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一、監(jiān)護權(quán)的淵源及概念監(jiān)護是淵出羅馬法的一種民事法律制度。按照我國《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監(jiān)護是監(jiān)護人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財產(chǎn)和其他合法權(quán)益依法實行的監(jiān)督和保護。即使婦女已離婚,前夫也常利用監(jiān)護權(quán)來達到控制前妻的目的,父親可任意剝奪母親對子女的會面權(quán),運用對子女的完全控制來實現(xiàn)對母親的潛在控制。我國大陸直到1986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才對監(jiān)護制度作了法律上的規(guī)定,基本上采用了廣義上的監(jiān)護制度,父母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監(jiān)護。那么論離婚后父母對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guān)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論離婚后父母對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一、監(jiān)護權(quán)的淵源及概念監(jiān)護是淵出羅馬法的一種民事法律制度。按照我國《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監(jiān)護是監(jiān)護人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財產(chǎn)和其他合法權(quán)益依法實行的監(jiān)督和保護。即使婦女已離婚,前夫也常利用監(jiān)護權(quán)來達到控制前妻的目的,父親可任意剝奪母親對子女的會面權(quán),運用對子女的完全控制來實現(xiàn)對母親的潛在控制。我國大陸直到1986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才對監(jiān)護制度作了法律上的規(guī)定,基本上采用了廣義上的監(jiān)護制度,父母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監(jiān)護。關(guān)于論離婚后父母對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的法律問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婚姻家庭律師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論離婚后父母對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
一、監(jiān)護權(quán)的淵源及概念
監(jiān)護是淵出羅馬法的一種民事法律制度。最初是為了維護繼承人的繼承權(quán)而設(shè)立,它實行的是親權(quán)和監(jiān)護權(quán)分離的制度。監(jiān)護是親權(quán)的延長和“彌補親權(quán)的方法”。這一制度為后來的大陸法系國家所繼承和發(fā)展。近現(xiàn)代立法中,有些國家的民法典對監(jiān)護對象的范圍有所調(diào)整,將其中的部分被監(jiān)護對象從中刪除,但被監(jiān)護對象范圍過窄也使有些學者感到殊為遺憾,認為被監(jiān)護對象的范圍應更為擴展。在英美法系,普遍采用親權(quán)和監(jiān)護權(quán)合一的方法,不區(qū)分親權(quán)和監(jiān)護權(quán),統(tǒng)一規(guī)定為監(jiān)護權(quán)。我國《民法通則》亦采用此例。按照我國《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監(jiān)護是監(jiān)護人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財產(chǎn)和其他合法權(quán)益依法實行的監(jiān)督和保護。我國《婚姻法》至今尚未規(guī)定全面系統(tǒng)的父母對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制度,這已不適應新形勢下調(diào)整父母子女關(guān)系的需要。
二、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的歷史沿革
在英國,直到十九世紀中期,父母的親權(quán)一直處于不平等的狀態(tài),所謂的親權(quán)只是父親對婚生子女的權(quán)力而言,母親和兒童的利益根本不受重視,離婚或分居后的兒童的監(jiān)護權(quán)只有父親可以享有,十九世紀的婦女往往因為無法放棄子女而繼續(xù)留在暴力與絕望的婚姻生活中。即使婦女已離婚,前夫也常利用監(jiān)護權(quán)來達到控制前妻的目的,父親可任意剝奪母親對子女的會面權(quán),運用對子女的完全控制來實現(xiàn)對母親的潛在控制。這種狀況引起了平權(quán)主義者的強烈反對,伸張母權(quán)的運動逐漸在二十世紀展開,由此出現(xiàn)了幼年原則(tenderyearsdoctrine),即推定七歲以下的兒童或嬰兒最有利的生活環(huán)境是由母親照顧下的環(huán)境。幼年原則成為平衡父權(quán)的有利主張,它亦與兒童發(fā)展的認知相連接,由于認識到母親對兒童發(fā)展的重要性并且考慮到母子間的血緣關(guān)系,母權(quán)逐漸受到重視,又因兒童權(quán)益的萌芽,法院改變以往對父權(quán)的觀念而代之以照顧兒童的程度作為兒童利益的評價標準,因此母親所能提供的照顧被認為更加重要。
之后,這一原則被擴大使用,幼兒的年齡不再限制在7歲以下,進而包括了所有未成年兒童,除特殊情況外,法院的判例均將未成年兒童的監(jiān)護權(quán)判給了母親。這種狀況持續(xù)了近半個世紀,新父權(quán)主義者為爭得對兒童的監(jiān)護權(quán)一直在不懈努力,他們聲稱,兒童需要父親,離婚的母親可能僅僅因為自己的利益而從父親處奪走子女,而不顧及兒童的利益,而且離婚后因家庭關(guān)系破裂,亟需父親的形象來保持兒童情緒上的穩(wěn)定,且父親的照顧有助于兒童對離婚后新環(huán)境的適應。這種觀點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法院逐漸對母親在離婚后申請監(jiān)護權(quán)的態(tài)度轉(zhuǎn)為嚴厲,監(jiān)護權(quán)不再一味地授予母親,父母都可以在離婚時申請對兒童的監(jiān)護權(quán),之后又發(fā)展為父母可在離婚后都享有對兒童的監(jiān)護權(quán),實現(xiàn)了從單獨監(jiān)護到單獨監(jiān)護與共同監(jiān)護并存的轉(zhuǎn)變。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我國長期封建家長統(tǒng)治的歷史,使監(jiān)護制度缺乏生存的必要環(huán)境,以至于舊律沒有關(guān)于監(jiān)護制度的規(guī)定,直到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及前大理院判例,始認有此制。1930年公布的民國民法典《親屬編》專章規(guī)定了監(jiān)護制度,將監(jiān)護分為不在親權(quán)之下的未成年人監(jiān)護和禁治產(chǎn)人的監(jiān)護,我國臺灣地區(qū)一直沿用至今。我國大陸直到1986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才對監(jiān)護制度作了法律上的規(guī)定,基本上采用了廣義上的監(jiān)護制度,父母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監(jiān)護。
三、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行使的原則
(一)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行使的類型
關(guān)于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或親權(quán)的行使原則,從現(xiàn)代國外立法看,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 1、單方行使原則,即離婚時法院確定由父或母一方單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或親權(quán)。這主要以本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修訂后的立法為代表。
2、雙方行使原則,即離婚后父母雙方仍有權(quán)行使對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權(quán)或親權(quán)。
3、單方行使原則和雙方行使原則并存,即離婚時,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法院決定由父母雙方共同或一方單獨行使親權(quán)。這以本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修改后的立法為代表。
“以未成年子女利益為基準”,決定離婚后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或親權(quán)歸屬于父母一方或雙方行使,即兼采單方行使和雙方行使原則,將成為當今世界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qū)立法的通例。而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或親權(quán)的行使方式,由傳統(tǒng)的父或母單方監(jiān)護,發(fā)展為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由父母共同監(jiān)護,無疑有利于達到把離婚對子女的損害減少到最低限度之目的。
(二)我國離婚后父母對子女行使監(jiān)護權(quán)現(xiàn)狀
我國《婚姻法》第29條規(guī)定:“父母與子女間的關(guān)系,不因父母離婚而消除。離婚后,子女無論由父方或母方撫養(yǎng),仍是父母雙方的子女。”“離婚后,父母對子女仍有撫養(yǎng)和教育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離婚后,哺乳期內(nèi)的子女,以隨哺乳的母親撫養(yǎng)為原則。哺乳期后的子女,如雙方因撫養(yǎng)問題發(fā)生爭執(zhí)不能達成協(xié)議時,由人民法院根據(jù)子女的權(quán)益和雙方的具體情況判決。”據(jù)此表明,父母對子女撫養(yǎng)、教育、管教、保護的權(quán)利義務(wù)(教育、管教、保護均為監(jiān)護內(nèi)容之一),均不因父母離婚而消除。但由于父母離婚,父母雙方已不能同時與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對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的行使及其他權(quán)利義務(wù)如撫養(yǎng)義務(wù)的履行方式上會有所變化,父母面臨決定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的歸屬及行使方式(即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歸屬于父母雙方行使或一方行使及如何行使)的問題。
當前,隨著我國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實施,獨生子女日益增多,離婚時父母雙方爭要獨生子女隨其生活的情況也增多。但有些爭要孩子隨其生活的父母一方,是“想在日后割斷另一方和孩子的關(guān)系”,單方行使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另一方面,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有些父母的價值觀念發(fā)生了變化,離婚時考慮問題不是以子女利益為本位,而是以父母利益為本位。為使父母本人今后再婚更容易或生活更舒適,視子女為包袱,出現(xiàn)了離婚時有的父母雙方相互推諉均不要子女隨其生活,或有的有撫養(yǎng)能力和條件的父母一方堅決不要子女隨其生活等推卸撫養(yǎng)、監(jiān)護子女責任的情況。對這些問題應如何解決?我國《婚姻法》第29條僅規(guī)定了離婚后子女由父母何方撫養(yǎng)的原則。
關(guān)于離婚時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的行使原則,我國《婚姻法》尚無明文。一些離婚父母誤以為,離婚后未成年子女隨何方生活,則應由該方單獨行使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也就是說,他們以未成年子女隨何方父母生活,作為離婚時確定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行使的原則。這既非法剝奪了未與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對子女的監(jiān)護權(quán),也不符合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現(xiàn)實生活中,不少離婚父母一方對此感到十分痛苦,甚至有的訴至法院,一些人民法院處理此類問題往往也感到無法可依。
四、我國關(guān)于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順序及范圍
(一)監(jiān)護人的順序。監(jiān)護人的順序,是指監(jiān)護人有數(shù)人時,法律規(guī)定的承擔監(jiān)護職責的先后順序。確定監(jiān)護人的順序是為了便于協(xié)調(diào)監(jiān)護當事人之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避免濫用權(quán)利和推諉義務(wù)。《民法通則》第16條對監(jiān)護人的資格和監(jiān)護順序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此外,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貫徹民法通則《意見》第14條的規(guī)定:前一順序有監(jiān)護資格的人無監(jiān)護能力或者對被監(jiān)護人明顯不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jù)對被監(jiān)護人有利的原則,從后一順序有監(jiān)護資格的人中擇優(yōu)確定。被監(jiān)護人有識別能力的,應視情況征求被監(jiān)護人的意見。在監(jiān)護人自然死亡的情況下,其監(jiān)護職責消滅,監(jiān)護關(guān)系終止。只有在其無監(jiān)護能力或者對被監(jiān)護人明顯不利時,序位在后的監(jiān)護人才能請求變更監(jiān)護人。
如被收養(yǎng)人的父母恢復對其親權(quán)、實現(xiàn)了對其的管領(lǐng)和照顧,則基于收養(yǎng)發(fā)生的監(jiān)護權(quán)轉(zhuǎn)移亦告結(jié)束。再如被監(jiān)護人被收容教養(yǎng),監(jiān)護權(quán)從被監(jiān)護人被收容教養(yǎng)時開始,依公法上的權(quán)力形成事實上的監(jiān)護權(quán)轉(zhuǎn)移,受托人的職責始于被監(jiān)護人置于其照管之下。再如學校的監(jiān)護職責始于學生到校,終于學生離校,學生在校的全部期間,均為學校應履行監(jiān)護職責的期間。即使在學生自由活動期間,學校亦負監(jiān)護之責。除非有特別約定,學校不負責學生的接送,學生在入校前和離校后的監(jiān)護職責仍由監(jiān)護人履行。又如精神病人到精神病醫(yī)院接受治療,從病人入院的那一刻起,醫(yī)院就應當履行監(jiān)護的職責,直到其出院為止。在精神病醫(yī)院接受治療的精神病人,受到人身傷害或者給他人造成人身傷害的,由精神病醫(yī)院承擔民事責任。
(二)監(jiān)護權(quán)的主體因被監(jiān)護人的身份不同而不同。根據(jù)《民法通則》第16條的規(guī)定,如被監(jiān)護人是未成年人,則其監(jiān)護權(quán)主體范圍如下:
(1)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是一種法定的親權(quán)關(guān)系。基于這種親權(quán)關(guān)系,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權(quán)是依據(jù)法律規(guī)定而產(chǎn)生的。
(2)有監(jiān)護能力的近親屬、其他公民和有關(guān)機關(guān)、團體、組織擔任監(jiān)護人。他們享有監(jiān)護權(quán)的原因是未成人的父母已經(jīng)死亡或者沒有監(jiān)護能力,否則,他們不得以任何借口與未成年人的父母爭議監(jiān)護人資格,因為父母對子女的撫養(yǎng)教育是一項法定義務(wù)。

五、在我國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存在的問題及相應對策
我國未設(shè)親權(quán)制度,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保護教養(yǎng)通過監(jiān)護制度來實現(xiàn),最基本的法律規(guī)范是我國《民法通則》的有關(guān)規(guī)定,該法第16條第1款規(guī)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人。”另外(婚姻法》第36條規(guī)定:“父母與子女的關(guān)系,不因父母離婚而消除,離婚后,父母對于子女仍有撫養(yǎng)和教育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還有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21條規(guī)定:“夫妻離婚后,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無權(quán)取消對方對該子女的監(jiān)護權(quán)。但是,未與該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對該子女有犯罪行為、虐待行為或者對該子女明顯不利的,人民法院認為可以消除的除外。”可見,我國關(guān)于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是以共同監(jiān)護為原則,以單獨監(jiān)護為例外的。
比較我國和外國關(guān)于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制度,可以看出,除日本的規(guī)定較為特殊外,大多數(shù)國家都規(guī)定了單獨監(jiān)護和共同監(jiān)護的雙軌制,其目的無非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quán)益,而日本是通過另設(shè)監(jiān)護人的制度來實現(xiàn)這一目的的。再比較規(guī)定了單獨監(jiān)護和共同監(jiān)護制度的國家,發(fā)現(xiàn)仍有不同,德國和英國的立法,對單獨監(jiān)護和共同監(jiān)護采同樣的態(tài)度,均可由當事人自由選擇,作為處理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人監(jiān)護的方法。而法國和我國的立法則以共同監(jiān)護為常態(tài),而以單獨監(jiān)護為補充。兩種立法例的差異在于對單獨監(jiān)護的可否自由選擇上,筆者認為,以德國和英國的立法例較為優(yōu)越,畢竟民法是私法,當事人意思自治是基本的原則,如果當事人雙方認為單獨監(jiān)護對子女更有利,應該賦予當事人選擇的權(quán)利,而不必通過法律的強制規(guī)定來排除這種選擇。在雙方不能達成協(xié)議時,可由法院根據(jù)子女的利益做出單獨監(jiān)護或共同監(jiān)護的判決。
從我國目前的法律規(guī)定來看,也過于簡單,缺乏法律規(guī)定來明確當事人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司法實踐中,離婚案件涉及到子女問題時,法院的調(diào)解書或判決書往往表述為婚生子(女)XXX隨原(被)告YYY生活——至于隨誰生活所包含的權(quán)利義務(wù)則無從可知,而不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法律除規(guī)定了探望的權(quán)利和撫養(yǎng)的義務(wù)以外,也沒有其他詳細的規(guī)定,在共同監(jiān)護的前提下,顯然未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權(quán)利沒有得到保障。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完善我國監(jiān)護人的權(quán)利義務(wù),然后在雙方當事人中間進行合理分配,以實現(xiàn)權(quán)利義務(wù)相一致的原則。
目前我國法律關(guān)于監(jiān)護人職責的規(guī)定體現(xiàn)在《民法通則》第18條:“監(jiān)護人應當履行監(jiān)護職責,保護被監(jiān)護人的人身、財產(chǎn)及其他合法權(quán)益,除為被監(jiān)護人的利益外,不得處理被監(jiān)護人的財產(chǎn)。”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0條:“監(jiān)護人的職責包括:保護被監(jiān)護人的身體健康,照顧被監(jiān)護人的生活,管理和保護被監(jiān)護人的財產(chǎn),代理被監(jiān)護人進行民事活動,對被監(jiān)護人進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監(jiān)護人合法權(quán)益受到侵害或與人發(fā)生爭議時,代理其進行訴訟。”由以上兩個法律規(guī)定可以看出,我國法律對監(jiān)護人職責的規(guī)定似乎只涉及到了日常生活照顧權(quán)和法定代理權(quán),而未涉及兒童重大事項的決定權(quán),如兒童就學、醫(yī)療、改變姓氏等事項。
綜合大陸法系國家關(guān)于親權(quán)的規(guī)定以及英美法系國家關(guān)于監(jiān)護的規(guī)定,筆者認為,我國的監(jiān)護人職責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日常生活照顧權(quán);(2)居所指定權(quán);(3)教育權(quán);(4)戒權(quán);(5)重大事項決定權(quán)(包括學校的選擇、醫(yī)療的同意、姓氏的改變等);(6)對兒童財產(chǎn)的管理、使用、收益和處分權(quán);(7)代理權(quán)。其中,日常生活照顧權(quán)、居所指定權(quán)、教育權(quán),懲戒權(quán)、對兒童財產(chǎn)的管理、收益權(quán)應由直接撫養(yǎng)子女的一方行使,而重大事項的決定權(quán)、對兒童財產(chǎn)的使用和處分權(quán)、代理權(quán)應由雙方共同行使。明確了離婚父母雙方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可以使當事人明確自己的訴訟目的,從而做出有利于己的抗辯。
筆者認為,我國《婚姻法》對離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權(quán)單采雙方行使原則,已不適應現(xiàn)代社會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成長的需要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的愿望。誠然,現(xiàn)實生活中有不少離婚父母雙方撫養(yǎng)、監(jiān)護子女的條件大體相同,住所相距不遠,且雙方又有離婚后仍共同監(jiān)護未成年子女的愿望,協(xié)議采取輪流撫育、共同監(jiān)護子女的方式。但也有些離婚父母一方因種種原因,如職業(yè)、身體健康狀況、住房條件及再婚等,愿意在離婚后停止行使對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權(quán)。因此,修改立法應考慮到上述兩方面的情況,對離婚后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的行使,以兼采單方行使原則和雙方行使原則為宜。
鑒于我國《婚姻法》未規(guī)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權(quán)(或親權(quán))制度,已不適應新形勢下調(diào)整父母子女關(guān)系,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需要,為使父母依法承擔對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義務(wù),離婚時父母亦能依法解決對未成年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或親權(quán))的歸屬及行使方式問題,人民法院在處理離婚父母對子女監(jiān)護權(quán)的爭議時亦有法可依,建議在修改我國《婚姻法》時,根據(jù)我國實際,借鑒國外立法,增加規(guī)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親權(quán)制度。筆者贊成該學者們的主張,在我國《婚姻法》中以增設(shè)親權(quán)制度為好。因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權(quán)并不完全相同于父母外的第三人對未成年子女的監(jiān)護權(quán);其次,我國屬于大陸法系國家,許多大陸法系國家都專設(shè)有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親權(quán)制度,調(diào)整父母子女關(guān)系。)在新增的親權(quán)制度中,就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親權(quán)的行使規(guī)定為:
離婚時,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則下,依父母協(xié)商決定親權(quán)由父母一方單獨或雙方共同行使。可以協(xié)商決定由父母雙方共同行使親權(quán)的,應以書面形式約定與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以何種方式參與行使對未成年子女的親權(quán)。如果父母協(xié)議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據(jù)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則判決。
父母關(guān)于子女親權(quán)的協(xié)議不利于子女的,人民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本人、其他利害關(guān)系人、未成年人保護機關(guān)或監(jiān)護機關(guān)的請求或依職權(quán)改定。
另外,《婚姻法》與解釋(一)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yǎng)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中均未使用《民法通則》中規(guī)定的“監(jiān)護”一詞,而是使用了“撫養(yǎng)”一詞。雖多有學者對此提出質(zhì)疑,認為二者在外延與內(nèi)涵上均有差別,建議應統(tǒng)一用語;但在司法實踐中,還尚未引起認識上的混亂。陳喜政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