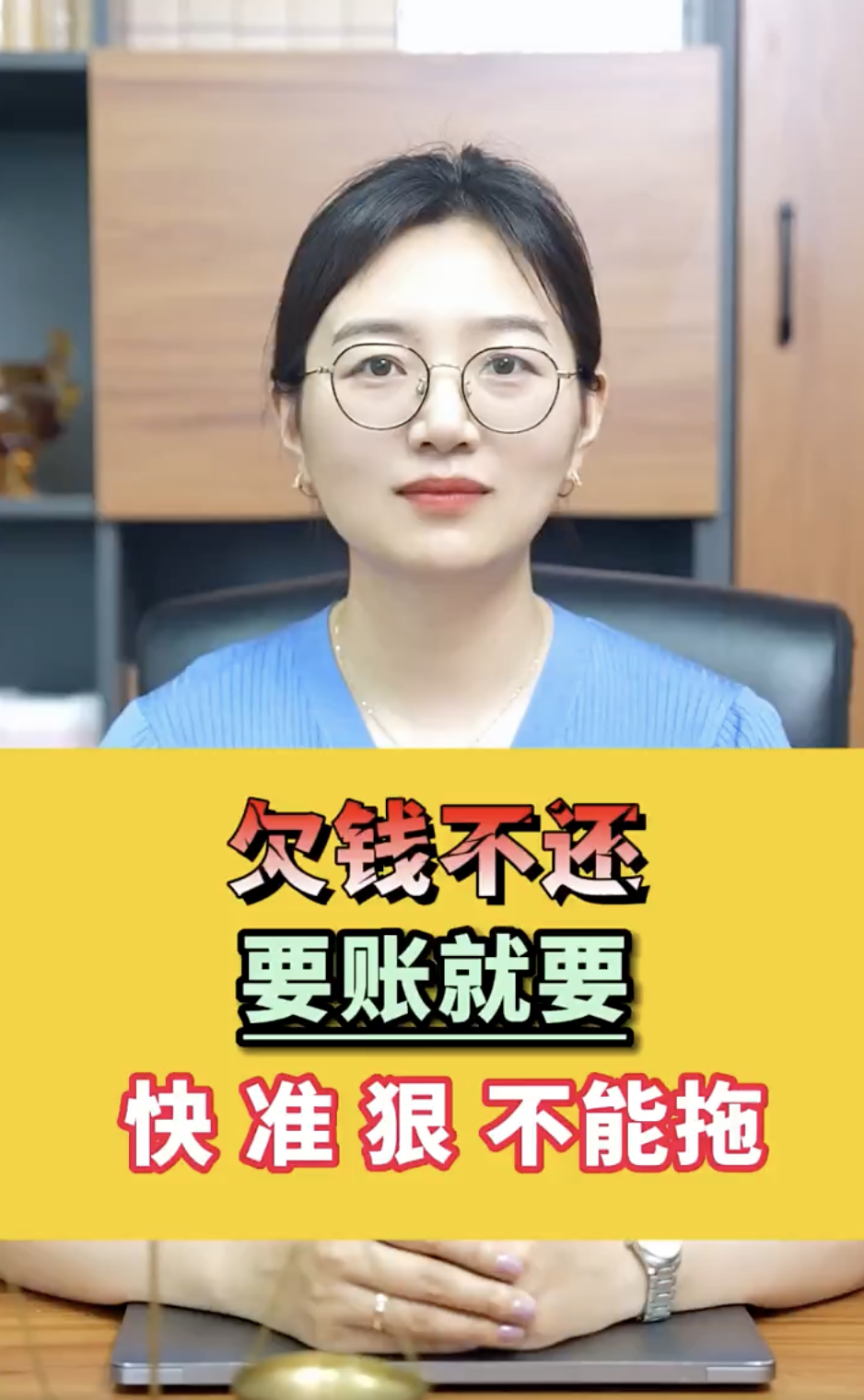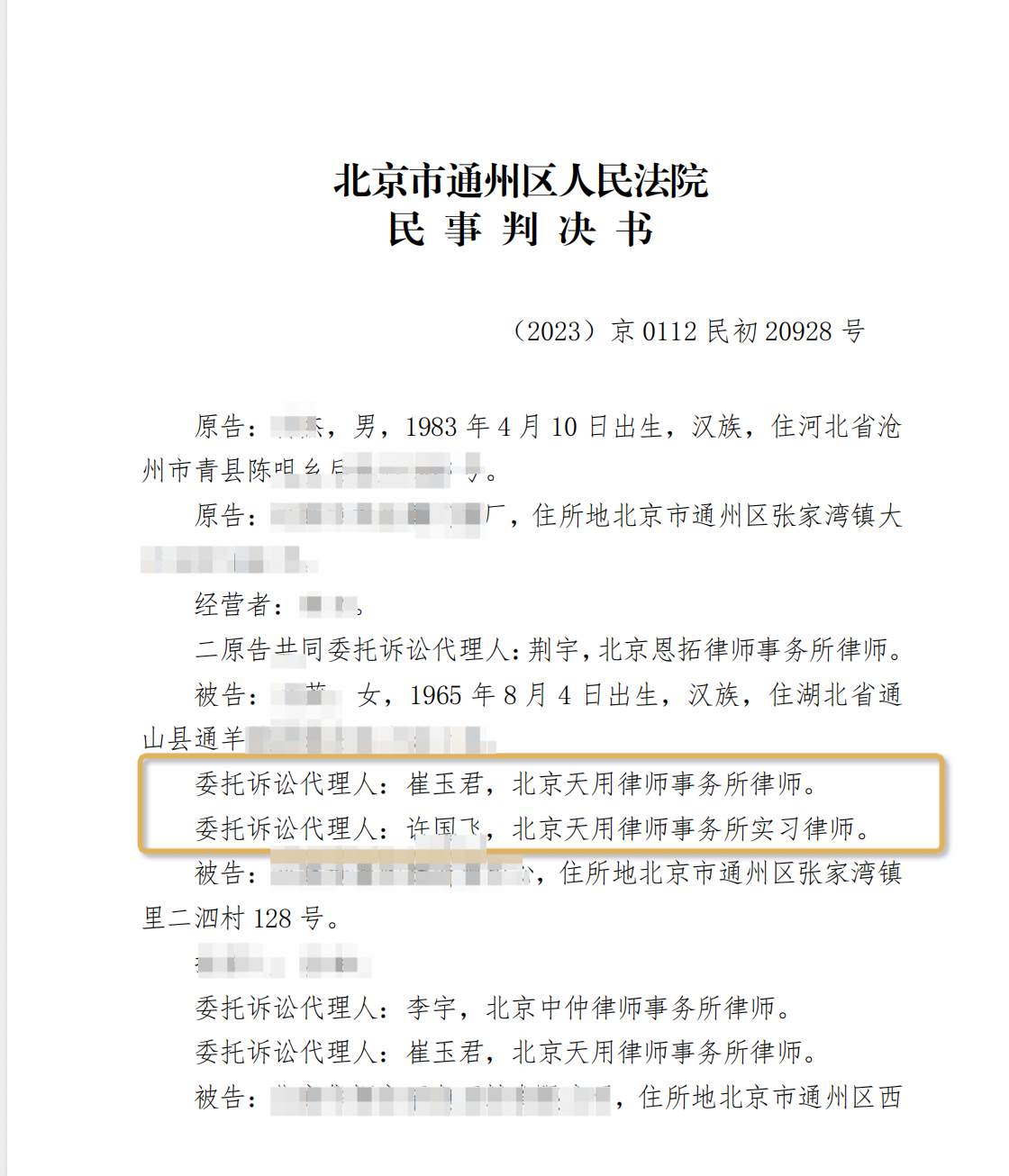保證債務與訴訟時效債務糾紛訴訟時效
 王學瑞律師2021.12.11502人閱讀
王學瑞律師2021.12.11502人閱讀
導讀:
保證債務與訴訟時效必須指出,擔保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關于在合同約定的保證期間和法定的保證期間,“債權人未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人免除保證責任;債權人已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期間適用訴訟時效中斷的規定”,這一規定存在問題。44號第一百二十五條關于“一般保證的債權人向債務人和保證人一并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將債務人和保證人列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那么保證債務與訴訟時效債務糾紛訴訟時效。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保證債務與訴訟時效必須指出,擔保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關于在合同約定的保證期間和法定的保證期間,“債權人未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人免除保證責任;債權人已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期間適用訴訟時效中斷的規定”,這一規定存在問題。44號第一百二十五條關于“一般保證的債權人向債務人和保證人一并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將債務人和保證人列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關于保證債務與訴訟時效債務糾紛訴訟時效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債權債務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保證債務與訴訟時效
必須指出,擔保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關于在合同約定的保證期間和法定的保證期間,“債權人未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人免除保證責任;債權人已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保證期間適用訴訟時效中斷的規定”,這一規定存在問題。因為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期間尚未起算,談何中斷?此其一。其二,債權人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斷,但在就債務人的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的事實出現之前,保證人有權拒絕履行保證債務,即不構成保證債務的履行遲延,也就是債權人的債權尚未遭受到來自保證人的違約行為的損害,因而,按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前段關于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受到侵害時起算的規定衡量,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期間不起算。法釋?2000?44號第一百二十五條關于“一般保證的債權人向債務人和保證人一并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將債務人和保證人列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但是,應當在判決書中明確在對債務人財產依法強制執行后仍不能履行債務時,由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規定,堅持了民法通則的這個思想。訴訟時效期間不起算,也就無所謂訴訟時效的中斷。
法釋?2000?44號意識到了擔保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不當,試圖加以修正,于其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一般保證的債權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前對債務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從判決或者仲裁裁決生效之日起,開始計算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這避免了擔保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存在的“未起算,卻中斷”的邏輯錯誤,但仍然存在問題:其一,它不符合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關于訴訟時效期間起算點的規定,因為判決或者仲裁裁決生效之日,并不清楚對主債務人的財產強制執行有無效果,只要未出現對主債務人的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的事實,保證人就有權行使先訴抗辯權,可以拒絕履行其保證債務。“在保證人得為檢索抗辯之期間,保證人不負遲延責任。”(史尚寬:《債法各論》,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1年11月版,第855-856頁)也就是債權人對保證人的債權尚未受到保證人不當行為的侵害,依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前段關于訴訟時效期間起算點規定的反面推論,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期間就仍不開始進行計算。其二,它同法釋?2000?44號第一百二十五條后段關于“應當在判決書中明確在對債務人財產依法強制執行后仍不能履行債務時,由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規定不一致,走到了另外的方向。
解決上述問題的路徑可有兩條,一是解釋論,一是立法論。為了法律適用的安全性、穩定性和統一性,在目前適宜采納前者。依據解釋論,法釋?2000?44號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不符合民法通則關于訴訟時效期間起算的規定,并無適當的理由修正民法通則的該項規定,依據下位階規范不得抵觸上位階的原則,在確定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點上,應當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的規定,而非適用法釋?2000?44號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

應當看到,由于擔保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更不合邏輯,因而僅僅固守著上述解釋論尚不能完滿地解決問題。從理想的角度出發,在制定我國民法典時,有必要采取立法論的立場,重新設計一般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的起算點,修正擔保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以及法釋?2000?44號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我們應予堅持的觀點是:一般保證期間的起算點,應為對主債務人的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之時(實際上為次日);而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點是權利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實際上為次日)。
與筆者的上述意見不同,有專家學者認為,對一般保證人只需要在實體審理和執行中肯定其作為第二順序債務人,就滿足了先訴抗辯權的要求,沒有必要處處體現“先訴抗辯權”,不能機械地認為先訴抗辯權可以對抗法院的審理,對抗訴訟時效的起算。比如《德國民法典》第202條規定,時效因給付遲延或者義務人由于其他原因暫時有權拒絕給付而中止,但不適用于……先訴抗辯權……。
由此可見,先訴抗辯權不能導致訴訟時效的中止,當然更不能阻止訴訟時效的起算。對此,筆者不能茍同。
其一,這違背了民法通則關于訴訟時效期間起算點以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為準的精神。而訴訟時效制度及其關于起算點的規定屬于強行性規范,我們個人無權修正。
其二,所謂“對一般保證人只需要在實體審理和執行中肯定其作為第二順序債務人,就滿足了先訴抗辯權的要求”之說,如果其含義是指在對主債務人的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前,保證人有權拒絕履行其保證債務,且不構成遲延履行,那么,債權人的債權就未受到侵害,依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關于訴訟時效期間起算點的規定,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期間不起算。從論者關于“在實體審理和執行中肯定其作為第二順序債務人”的表述看,是在上述意義上使用的,按理應該承認訴訟時效期間不起算的結論,但論者卻拒絕承認這一結論,一方面承認保證人作為第二順序債務人(作為第二順序債務人,他拒絕履行就未侵害債權人的債權――筆者注),另一方面又承認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期間重新開始計算,顯得不合邏輯。論者的上述觀點還不符合法釋?2000?44號第一百二十五條關于“一般保證的債權人向債務人和保證人一并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將債務人和保證人列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但是,應當在判決書中明確在對債務人財產依法強制執行后仍不能履行債務時,由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規定。
其三,起算不起算訴訟時效期間與對抗不對抗法院審理案件沒有必然關系。在訴訟時效期間進行中,法院可以審理案件,如法院審理已經構成違約的案件。在訴訟時效期間尚未開始進行的背景下,法院也可以審理案件,如法院審理合同所附的停止條件是否成就,合同義務是否已屆清償期的案件。難道在后者場合,債務人行使對抗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的抗辯權,就是在對抗法院的審理嗎?把行使先訴抗辯權以遲滯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稱為對抗法院審理,過于言重了。
其四,所謂“先訴抗辯權不能導致訴訟時效的中止,當然更不能阻止訴訟時效的起算。”欲通過舉重明輕的推理來否定先訴抗辯權的行使遲滯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的理論,實際上存在著誤解。因為在已經有保證期間發揮作用的情況下,訴訟時效期間起算點定得早,意味著提前了保證期間的開始時間,留給債權人行使債權的時間相對短,對債權人并不利;反之,確認先訴抗辯權的行使遲滯訴訟時效期間的開始,留給債權人較多的時間,同時,也順延了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時間,形成雙贏,是適當的制度設計。訴訟時效期間的中止則是有利于債權人,使債權人行使債權的時間相對延長了。這種利益不應由保證人正當地行使先訴抗辯權而獲得。因為保證人行使先訴抗辯權本是保障他自己的合法權益,若因此導致訴訟時效期間中止,使得債權人有更長的時間追究其保證責任,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一部良法不應如此設計制度。所以,《德國民法典》第202條第2款規定,時效不因先訴抗辯權的行使而中止,是適當的利益衡量。由此可知,在這里,起算、中止不是同一方向上的東西,而是非此即彼之間的關系。[page]
關于一般保證債務與訴訟時效中止的問題,法釋?2000?44號第三十六條第二款規定:“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止的,保證債務訴訟時效中止。”筆者認為,只有在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期間已經開始起算的情況下,依據主從關系原理,認定主債務訴訟時效中止的,保證債務訴訟時效才中止;在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期間尚未起算的情況下,主債務的訴訟時效中止,并不引起保證債務的訴訟時效中止。所以,從立法論的立場出發,在制定民法典時,對此規定應予修改。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