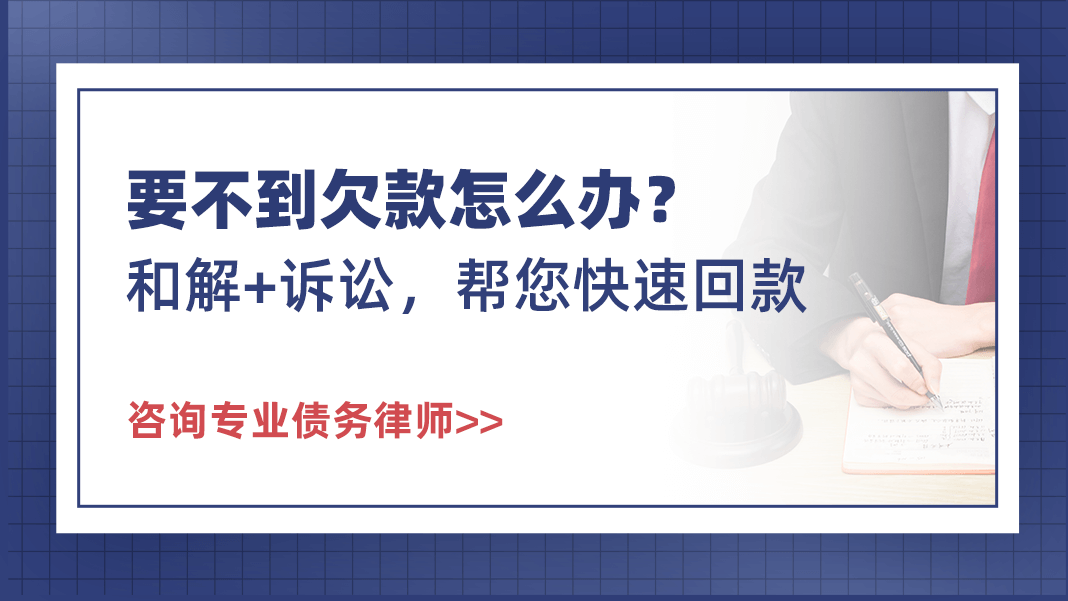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的研究債務(wù)糾紛訴訟時(shí)效
 于海明律師2021.12.09973人閱讀
于海明律師2021.12.09973人閱讀
導(dǎo)讀:
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的研究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是指訴訟時(shí)效完成后的法律后果。對(duì)于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問題,各國的立法規(guī)定得很不一致。三是訴權(quán)消滅主義,這種類型的立法主張,訴訟時(shí)效完成后,權(quán)利本身仍然存在,但訴權(quán)歸于消滅,當(dāng)事人不能請(qǐng)求法院為強(qiáng)制執(zhí)行。那么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的研究債務(wù)糾紛訴訟時(shí)效。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guān)知識(shí),希望能幫助大家。
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的研究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是指訴訟時(shí)效完成后的法律后果。對(duì)于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問題,各國的立法規(guī)定得很不一致。三是訴權(quán)消滅主義,這種類型的立法主張,訴訟時(shí)效完成后,權(quán)利本身仍然存在,但訴權(quán)歸于消滅,當(dāng)事人不能請(qǐng)求法院為強(qiáng)制執(zhí)行。關(guān)于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的研究債務(wù)糾紛訴訟時(shí)效的法律問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債權(quán)債務(wù)律師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shí),希望能幫助大家。
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的研究
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是指訴訟時(shí)效完成后的法律后果。對(duì)于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問題,各國的立法規(guī)定得很不一致。大致來說有三種類型:一是實(shí)體權(quán)消滅主義,這種類型的立法主張,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直接表現(xiàn)為實(shí)體權(quán)利的消滅。其代表是日本民法典。該法典第一百六十七條規(guī)定:債權(quán)因10年不行使而消滅,債權(quán)或所有權(quán)以外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因2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二是抗辯權(quán)發(fā)生主義,這種類型的立法主張,時(shí)效完成后,義務(wù)人取得拒絕履行的抗辯權(quán),如果義務(wù)人自動(dòng)履行的,視為拋棄其抗辯權(quán),該履行應(yīng)為有效。屬于此種主義的立法,有德國民法典和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民法。德國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二條規(guī)定:消滅時(shí)效完成后,義務(wù)人有權(quán)拒絕給付。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民法的規(guī)定與此相同。三是訴權(quán)消滅主義,這種類型的立法主張,訴訟時(shí)效完成后,權(quán)利本身仍然存在,但訴權(quán)歸于消滅,當(dāng)事人不能請(qǐng)求法院為強(qiáng)制執(zhí)行。屬于這種類型的立法有法國民法典。該法典第二千二百六十二條規(guī)定:一切物權(quán)或債權(quán)的訴權(quán),均經(jīng)30年的時(shí)效而消滅。
我國民法通則第七章用7個(gè)條款對(duì)訴訟時(shí)效做了一般性的規(guī)定。其中第一百三十五條規(guī)定:向人民法院請(qǐng)求保護(hù)民事權(quán)利的訴訟時(shí)效期間為二年,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據(jù)此,我國民法學(xué)者認(rèn)為,我國民法通則系采訴權(quán)消滅主義。而有的學(xué)者則進(jìn)一步把訴權(quán)區(qū)分為起訴權(quán)和勝訴權(quán),認(rèn)為訴訟時(shí)效的完成,僅使權(quán)利人的勝訴權(quán)消滅,而權(quán)利人的起訴權(quán)并不消滅,權(quán)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訴時(shí),只要符合民事訴訟法關(guān)于起訴條件的,人民法院還是應(yīng)當(dāng)受理。其實(shí)這種區(qū)分沒有什么實(shí)質(zhì)意義,因?yàn)闊o論訴權(quán)消滅說也好,勝訴權(quán)消滅說也好,都在一個(gè)基本問題上保持一致:罹于訴訟時(shí)效的權(quán)利,不能請(qǐng)求人民法院強(qiáng)制執(zhí)行,喪失了法律的強(qiáng)制力,淪為自然債。
無論是訴權(quán)消滅說還是勝訴權(quán)消滅說,它們都有著固有的理論缺陷與邏輯矛盾。這兩種見解一方面認(rèn)為罹于訴訟時(shí)效的“權(quán)利”本身并沒有消滅,消滅的是訴權(quán)或勝訴權(quán),另一方面認(rèn)為罹于訴訟時(shí)效的“權(quán)利”,不能請(qǐng)求人民法院強(qiáng)制執(zhí)行,喪失了法律的強(qiáng)制力,淪為自然債。那么,什么是權(quán)利?權(quán)利和法律的強(qiáng)制力之間有什么關(guān)系呢?我國民法學(xué)者認(rèn)為,權(quán)利是可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法律上之力是由法律所賦予,受法律的保障與支持的一種力量。沒有法律保障的權(quán)利為“裸體權(quán)利”,不具有實(shí)際意義。那么,所謂的自然債又意味著什么呢?我國民法學(xué)者認(rèn)為:“所謂自然債,如時(shí)效經(jīng)過之債……因不具備訴請(qǐng)法院強(qiáng)制執(zhí)行的效力,難謂為法律上的權(quán)利。”顯然,訴權(quán)消滅說或勝訴權(quán)消滅說一方面主張罹于時(shí)效的“權(quán)利”,“權(quán)利”本身并不消滅,另一方面卻又說罹于時(shí)效的“權(quán)利”,淪為不具有實(shí)際意義的,難謂法律上的權(quán)利的“自然債”,邏輯上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當(dāng)然,無論訴權(quán)消滅說還是勝訴權(quán)消滅說,都是為了對(duì)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進(jìn)行正當(dāng)性說明而解釋的結(jié)果,但解釋的結(jié)果卻使解釋者陷于兩難困境。
筆者認(rèn)為,應(yīng)該從完善我國民事立法,制定民法典的立場來檢討我國未來民事立法應(yīng)當(dāng)采取的對(duì)于訴訟時(shí)效效力的態(tài)度,而不能固守于解釋現(xiàn)行法律條文。很顯然,由于訴權(quán)消滅主義固有的理論缺陷,我國未來的民事立法應(yīng)當(dāng)拋棄這種立法主義。那么,我國是否應(yīng)當(dāng)采納實(shí)體權(quán)消滅主義呢?筆者認(rèn)為,實(shí)體權(quán)消滅主義主張罹于時(shí)效的權(quán)利本身消滅,對(duì)于權(quán)利人來說未免過于苛刻。我們社會(huì)主義國家的立法應(yīng)以保護(hù)人民的權(quán)利為根本出發(fā)點(diǎn),人民的權(quán)利神圣不可侵犯,不能輕易因?yàn)榈∮谛惺苟鴨适В虼耍瑢?shí)體權(quán)消滅主義應(yīng)為我國未來的民事立法所不取。

我國未來的民事立法應(yīng)當(dāng)采取抗辯權(quán)發(fā)生主義。首先,抗辯權(quán)發(fā)生主義既可以克服訴權(quán)消滅主義或勝訴權(quán)消滅主義的理論缺陷,也可以避免實(shí)體權(quán)消滅主義對(duì)權(quán)利保護(hù)的不周全。因?yàn)榭罐q權(quán)發(fā)生主義不涉及訴權(quán)或勝訴權(quán)問題。訴訟時(shí)效的完成僅僅產(chǎn)生義務(wù)人拒絕給付的抗辯權(quán)。而罹于時(shí)效的權(quán)利本身并不消滅,因該權(quán)利所生之請(qǐng)求權(quán)也不因時(shí)效完成而消滅,而僅僅是力量受到了減損。如果義務(wù)人行使抗辯權(quán),則請(qǐng)求權(quán)的行使受到阻止;如果義務(wù)人放棄抗辯權(quán),則請(qǐng)求權(quán)可以完全發(fā)揮其效力。其次,采納抗辯權(quán)發(fā)生主義的立法政策將對(duì)我國民事訴訟體制的改革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在發(fā)達(dá)的市場經(jīng)濟(jì)國家,民事訴訟的基本模式是當(dāng)事人主義。當(dāng)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要求當(dāng)事人在民事審判中處于積極主動(dòng)的地位,而作為裁判主體的法官則應(yīng)處于消極被動(dòng)的地位;訴訟程序由當(dāng)事人啟動(dòng),并在當(dāng)事人的積極參與下進(jìn)行;法院不能審理當(dāng)事人未主張的事項(xiàng);法院作出裁判所依據(jù)的事實(shí)只能來源于當(dāng)事人;對(duì)當(dāng)事人提供的證據(jù),只有經(jīng)過充分的辯論、質(zhì)證,法院才能認(rèn)定其真?zhèn)危⑦M(jìn)而加以取舍。就訴訟時(shí)效這一具體問題而言,除非當(dāng)事人援用時(shí)效,法院不得根據(jù)時(shí)效進(jìn)行裁判。但是,在我國,根據(jù)我國現(xiàn)行法律的有關(guān)規(guī)定,民法學(xué)者解釋說,法庭可不待當(dāng)事人主張而依職權(quán)主動(dòng)適用訴訟時(shí)效,而民法通則實(shí)行以來的審判實(shí)踐,也正是如此。很顯然,這與我國民事訴訟體制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馳。采納抗辯權(quán)發(fā)生主義能有效地杜絕法院主動(dòng)援用訴訟時(shí)效,這是因?yàn)楫?dāng)事人可以放棄抗辯權(quán)也可以不放棄抗辯權(quán),是否放棄不是法院依職權(quán)所審查的結(jié)果。
綜上所述,筆者主張,我國未來的民事立法在訴訟時(shí)效的效力上應(yīng)采納抗辯權(quán)發(fā)生主義的立法政策,并進(jìn)而設(shè)計(jì)完善我國的訴訟時(shí)效制度。武漢大學(xué)法學(xué)博士,范中超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王勇
 點(diǎn)贊
點(diǎn)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