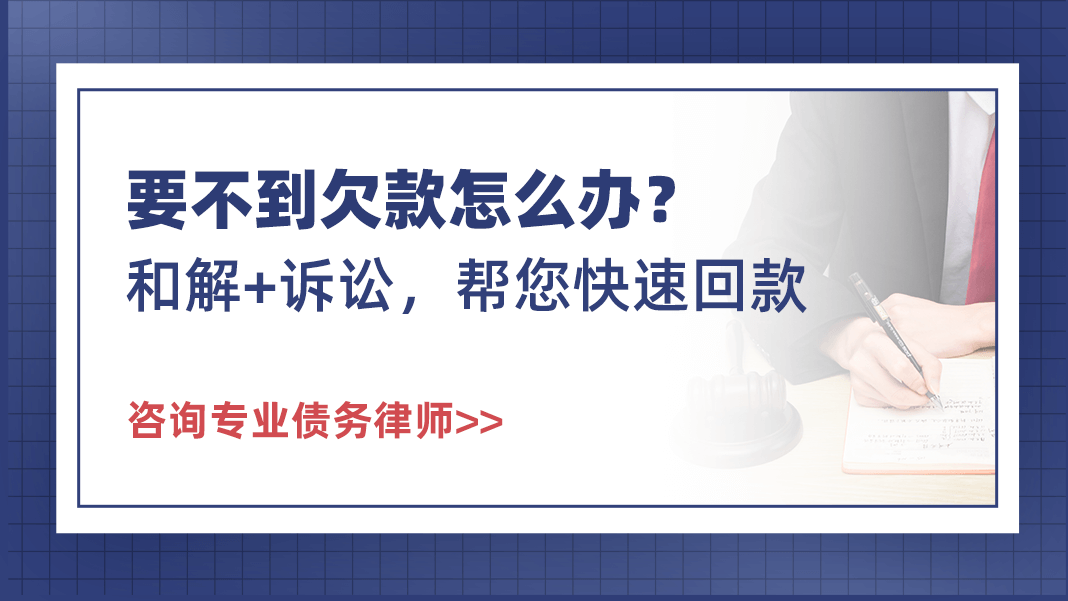論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債務(wù)糾紛訴訟時效
 李維律師2021.12.09419人閱讀
李維律師2021.12.09419人閱讀
導讀:
論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兼評《最高院關(guān)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有關(guān)內(nèi)容保證是指,保證人承諾,在債務(wù)人到期不能承擔債務(wù)清償責任時,由其替?zhèn)鶆?wù)人代為承擔清償責任。對于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我國《擔保法》沒有作出明文規(guī)定,實務(wù)中,各地司法實踐亦各不相同,較為混亂。那么論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債務(wù)糾紛訴訟時效。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guān)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論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兼評《最高院關(guān)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有關(guān)內(nèi)容保證是指,保證人承諾,在債務(wù)人到期不能承擔債務(wù)清償責任時,由其替?zhèn)鶆?wù)人代為承擔清償責任。對于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我國《擔保法》沒有作出明文規(guī)定,實務(wù)中,各地司法實踐亦各不相同,較為混亂。關(guān)于論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債務(wù)糾紛訴訟時效的法律問題,大律網(wǎng)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債權(quán)債務(wù)律師相關(guān)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論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
——兼評《最高院關(guān)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有關(guān)內(nèi)容
保證是指,保證人承諾,在債務(wù)人到期不能承擔債務(wù)清償責任時,由其替?zhèn)鶆?wù)人代為承擔清償責任。因此,在債務(wù)人不能承擔清償責任時,保證人需要向債權(quán)人承擔清償責任,我們稱之為“保證債務(wù)”。然保證人的這一保證債務(wù)不能無期限地存續(xù),其必須受到訴訟時效制度的約束。就連帶保證而言,保證人需對債權(quán)人承擔連帶責任,換言之,自債務(wù)人不履行債務(wù)清償責任時起,債權(quán)人就可以請求保證人承擔保證債務(wù)。此時的保證債務(wù)和一般的債務(wù)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故其訴訟時效亦當然應(yīng)當從保證債務(wù)發(fā)生之時,即債務(wù)人不履行債務(wù)清償責任時起計算。對此,理論界和實務(wù)界均沒有爭論。但是,就一般保證而言,保證人通常享有先訴抗辯權(quán),即在債務(wù)人不履行清償責任時,保證人并不需要立即承擔保證債務(wù),而是可以要求債權(quán)人先對債務(wù)人提起訴訟并申請強制執(zhí)行,其只在此后仍不能滿足債權(quán)人債權(quán)時,保證人方承擔剩余部分的清償責任。因而,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肯定不能同于連帶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若不考慮債權(quán)人因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quán)而耽擱的可主張權(quán)利的時間,以致認為訴訟時效期間因時間經(jīng)過而屆滿,則顯然對債權(quán)人不公。然而,就一般保證保證債務(wù)而言,其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究竟如何計算,在立法和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

對于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我國《擔保法》沒有作出明文規(guī)定,實務(wù)中,各地司法實踐亦各不相同,較為混亂。2000年《最高院關(guān)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4條規(guī)定,“一般保證的債權(quán)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前對債務(wù)人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從判決或者仲裁裁決生效之日起,開始計算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連帶責任保證的債權(quán)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前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的,從債權(quán)人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之日起,開始計算保證合同的訴訟時效。”
最高院以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統(tǒng)一了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計算方法,使各地法院的司法實踐有章可循了,但是,最高院的這一條司法解釋存在諸多矛盾之處。首先,按照一般保證中的先訴抗辯權(quán)理論,在債權(quán)人未對主債務(wù)人進行強制執(zhí)行并未能獲得清償之前,一般保證保證人均可以拒絕履行保證責任。相應(yīng)地,在此之前,債權(quán)人對保證人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也不應(yīng)當開始計算,否則,對債權(quán)人是不公正的。但是,前條司法解釋將訴訟時效的開始定位于債權(quán)人對債務(wù)人訴訟判決的取得,而非法院強制執(zhí)行后,這顯然是與先訴抗辯權(quán)的要求相違背的,對債權(quán)人利益的保護存在不足。其次,《最高院關(guān)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6條規(guī)定,“一般保證中,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連帶責任保證中,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不中斷。”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權(quán)威人士的解釋是:在一般保證中,債權(quán)人必須先向債務(wù)人提起訴訟或仲裁,此時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那么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也必須中斷,否則,債權(quán)人在經(jīng)過訴訟或仲裁后,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可能已經(jīng)完成,保證人將免責,這樣對于債權(quán)人明顯不公。而連帶保證與一般保證相比,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債權(quán)人對債務(wù)人和保證人可以不分先后行使權(quán)利,所以,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并不必然導致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中斷。[1]但是,這一規(guī)定和前述第34條相矛盾。依第34條的規(guī)定,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將從債權(quán)人對主債務(wù)人提起訴訟或仲裁的判決或仲裁裁決生效之日起才開始計算,那么,又怎么可能出現(xiàn)上述解釋中所擔心的,在債權(quán)人經(jīng)過訴訟或仲裁后,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可能已經(jīng)完成的情況?
實際上,我們考察傳統(tǒng)民法中關(guān)于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各國民法中,對于債權(quán)人向保證人主張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均沒有特殊的規(guī)定,一般都是適用普通訴訟時效計算方法,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開始計算時效期間。而非如我國現(xiàn)行司法解釋所規(guī)定的,要等到有關(guān)主債權(quán)債務(wù)的判決生效之后,方能計算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更不是像某些學者所主張的,應(yīng)當從對主債務(wù)人強制執(zhí)行仍不能清償債務(wù)時起算。如史尚寬先生言,“保證債務(wù)已屆履行期時,不問主債務(wù)人有無清償資力或第三人就主債務(wù)已設(shè)定擔保物權(quán)與否,即得請求保證債務(wù)之履行。惟債權(quán)人未就主債務(wù)人之財產(chǎn)強制執(zhí)行而無效果前而向保證人請求時,保證人有檢索之抗辯權(quán)。如保證人不提出此抗辯時,債權(quán)人得對于債務(wù)人及保證人有效地行使兩個請求權(quán),并得同時或先后請求全部或一部之履行。”[2]“德國法上,保證債務(wù)的時效,獨立于主債務(wù)的時效,為30年(第195條)”。[3]
我國學者之所以不承認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期間應(yīng)當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起算,主要是因為一般保證中先訴抗辯權(quán)的存在。依先訴抗辯權(quán),在債權(quán)人依法院判決對債務(wù)人實施強制執(zhí)行仍不能得到清償以前,保證人可以拒絕履行保證債務(wù)。因此,如果讓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期間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開始計算,則因其間存在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quán)而使債權(quán)人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證,也許當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quán)消滅時,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開始計算的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也許早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或者說已經(jīng)所剩無幾了。
但是,學者們的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存在著不足。所謂抗辯權(quán),即對抗請求權(quán),使其效力無法發(fā)生的權(quán)利。換言之,有抗辯權(quán)者,則當然存在請求權(quán),只是由于抗辯權(quán)的存在,使請求權(quán)的效力無法實現(xiàn)。照此邏輯,在一般保證責任中,既然存在保證人對債權(quán)人的先訴抗辯權(quán),即意味著債權(quán)人對保證人的履行請求權(quán)已經(jīng)發(fā)生并存在,而此種履行請求權(quán)是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即發(fā)生的。[4]正如學者所言,“先訴抗辯權(quán)的行使是以債權(quán)人的請求為前提的,無請求,則無抗辯,既有抗辯,說明請求權(quán)已經(jīng)得以行使。”[5]訴訟時效是從請求權(quán)可以行使之時起計算的,因此,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也應(yīng)當是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即開始計算,而不應(yīng)當從強制執(zhí)行債務(wù)人財產(chǎn),先訴抗辯權(quán)消滅之時起算。此時,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計算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雖然可能由于先訴抗辯權(quán)的存在而使債權(quán)人的利益不能實際實現(xiàn),但是,這是符合請求權(quán)以及抗辯權(quán)法律屬性的,是符合法律邏輯的。[6]更何況,在實踐中,還有無先訴抗辯權(quán)的連帶保證,以及一般保證人放棄先訴抗辯權(quán)的情況存在。在這些情況下,債權(quán)人行使權(quán)利不存在先訴抗辯權(quán)的限制,其對于保證人的履行債務(wù)請求權(quán)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即可以行使。所以說,在保證債務(wù)中,訴訟時效期間應(yīng)當適用普通訴訟時效期間,具體期間應(yīng)當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開始計算。[page]
正是基于上面的考慮,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德國民法典(舊版)第202條規(guī)定,“(1)時效因給付遲延或者義務(wù)人由于其他原因暫時有權(quán)拒絕給付而中止。(2)上述規(guī)定不適用于對留置權(quán)、合同不履行、擔保欠缺、先訴抗辯權(quán),以及保證人根據(jù)第770條的規(guī)定享有的抗辯權(quán)和繼承人根據(jù)第2014條、第2015條的規(guī)定享有的抗辯權(quán)。”依此規(guī)定,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當不應(yīng)因為先訴抗辯權(quán)的存在而受阻。德國民法典(2002年版)將上述條款改為第205條,規(guī)定,“在債務(wù)人依與債權(quán)人達成的協(xié)議而暫時有權(quán)拒絕給付期間,消滅時效停止進行。”修改后的德國民法典雖然沒有明確規(guī)定先訴抗辯權(quán)的存在不影響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進行,但“從該條規(guī)定清楚明確的字義可以看出:其僅適用于約定的拒絕給付權(quán),而不適用于法定的拒絕給付權(quán)。”[7]由此可見,使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停止進行的只能是當事人的約定,而不能是先訴抗辯權(quán)等法定的抗辯事由,換言之,先訴抗辯權(quán)的存在并不影響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進行。
傳統(tǒng)民法規(guī)定,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起算,先訴抗辯權(quán)的存在不影響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進行,這是符合法律內(nèi)在邏輯和秩序的。但是,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從主債權(quán)履行期屆滿時起算,其間畢竟還存在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quán),債權(quán)人向保證人主張的權(quán)利因此是不能得到滿足的,而訴訟時效又不停止計算,顯然,這對于主債權(quán)人而言是不公正的。實際上,傳統(tǒng)民法對此并非熟視無睹,各國均規(guī)定:債權(quán)人向主債務(wù)人主張權(quán)利等而使主債權(quán)訴訟時效中斷時,其效力及于保證債務(wù),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亦因此而中斷。這樣,一般保證中,債權(quán)人在因先訴抗辯權(quán)的存在而只能向債務(wù)人主張權(quán)利時,主債務(wù)訴訟時效因此中斷,而同時其效力及于保證債務(wù),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也隨之而中斷。如此,實質(zhì)上就使債權(quán)人因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quán)而停止的時間從訴訟時效中去除掉,保證了債權(quán)人有足夠的時間向保證人主張權(quán)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法國民法典第2250條規(guī)定,“向主債務(wù)人進行的傳喚,或者主債務(wù)人承認債務(wù),對保證人發(fā)生中斷時效之效力。”日本民法典第457條第1款規(guī)定,“對主債務(wù)人的履行請求或其他時效中斷,對保證人亦發(fā)生效力。”臺灣民法典第747條規(guī)定,“向主債務(wù)人請求履行,及為其它中斷時效之行為,對于保證人亦生效力。”
在我國,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亦應(yīng)當隨之中斷,以保證債權(quán)人的利益,這一點已經(jīng)為我國立法界所承認。也正因為此,《最高院關(guān)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6條規(guī)定,“一般保證中,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連帶責任保證中,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不中斷。”如前所述,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權(quán)威人士的解釋是:在一般保證中,債權(quán)人必須先向債務(wù)人提起訴訟或仲裁,此時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那么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也必須中斷,否則,債權(quán)人在經(jīng)過訴訟或仲裁后,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可能已經(jīng)完成,保證人將免責,這樣對于債權(quán)人明顯不公。而連帶保證與一般保證相比,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債權(quán)人對債務(wù)人和保證人可以不分先后行使權(quán)利,所以,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并不必然導致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的中斷。[8]但是,該司法解釋這里忽視了一個問題,國外規(guī)定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隨之中斷的前提是,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從主債務(wù)履行期屆滿時開始計算。而我國在規(guī)定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隨之中斷的同時,規(guī)定,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從主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判決書生效時起算。這樣,自然就會出現(xiàn)上文所述的矛盾:“保證債務(wù)的訴訟時效從債權(quán)人對主債務(wù)人提起訴訟或仲裁的判決或仲裁裁決生效之日起才開始計算,又怎么可能出現(xiàn)上述解釋中所擔心的,在債權(quán)人經(jīng)過訴訟或仲裁后,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可能已經(jīng)完成的情況?”如此,《最高院關(guān)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6條規(guī)定,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隨之中斷,完全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也成為學界所批評的一個詬病。因此,我們建議,正本清源,在以后修訂擔保法時,我們應(yīng)當完整沿襲傳統(tǒng)民法的既有做法,規(guī)定一般保證中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從主債務(wù)履行期屆滿時起算,同時規(guī)定,主債務(wù)訴訟時效中斷,保證債務(wù)訴訟時效隨之中斷,以平衡因保證人先訴抗辯權(quán)而給債權(quán)人帶來的不利益。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