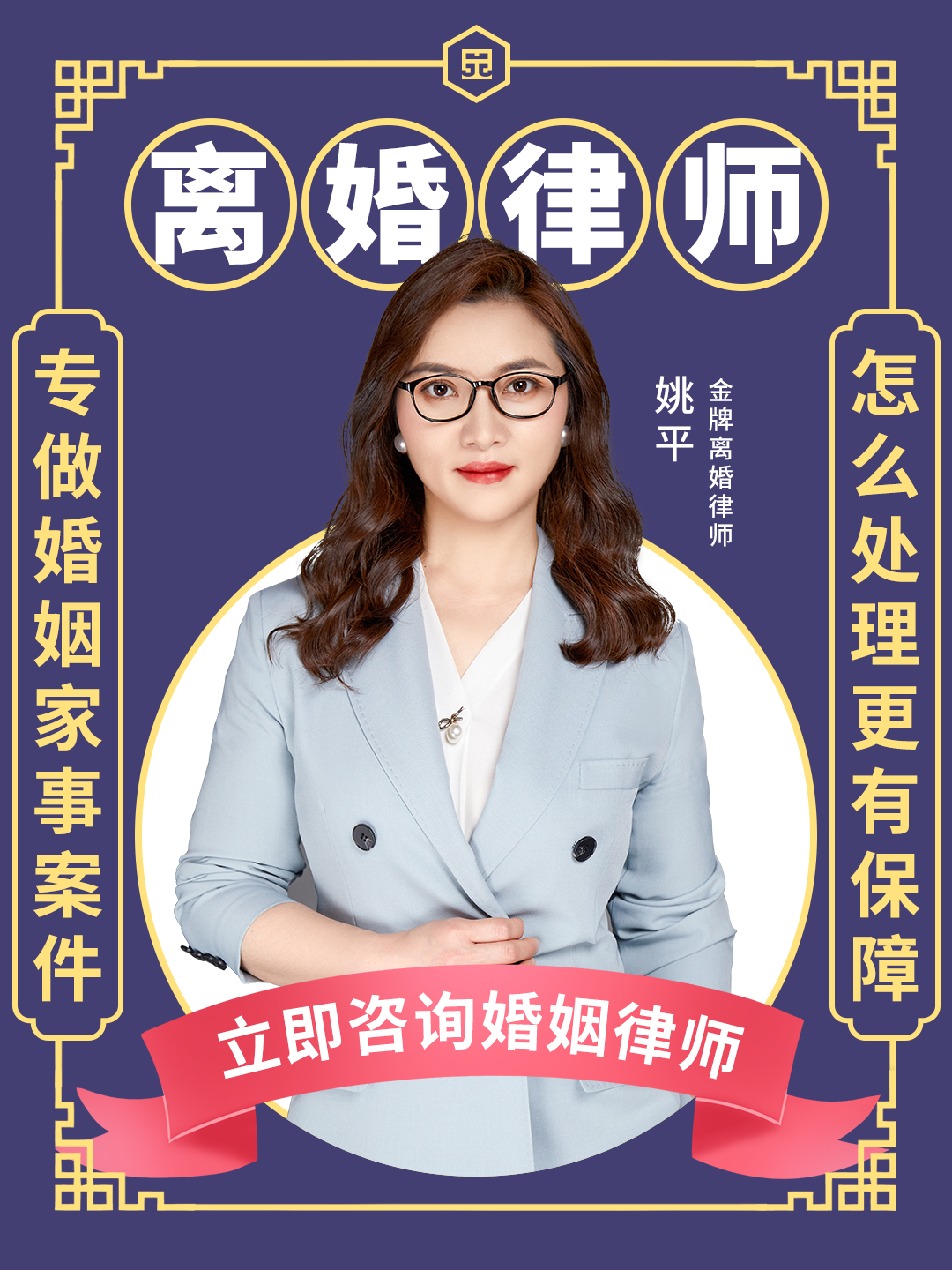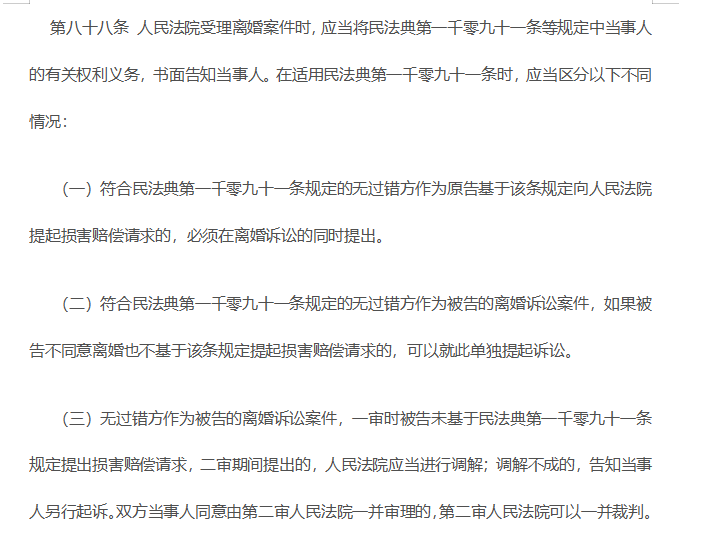離婚損害賠償過錯責任的認定及賠償標準問題
 張蕓律師2022.02.11106人閱讀
張蕓律師2022.02.11106人閱讀
導讀:
離婚損害賠償過錯責任的認定及賠償標準問題:1、關于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過錯責任之認定問題。但是否配偶對每一個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力行為,另一方即無過錯方在離婚訴訟中都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對此,法律及司法解釋并未明確。例如丈夫毆打其父母、兄弟姐妹,但并未毆打妻子而妻子卻以其理由提起離婚之訴時,能否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在丈夫毆打其父母、兄弟姐妹這一家庭暴力中,雖然丈夫存在過錯,但它并不一定給其妻子造成物質和精神上的損害。那么離婚損害賠償過錯責任的認定及賠償標準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離婚損害賠償過錯責任的認定及賠償標準問題:1、關于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過錯責任之認定問題。但是否配偶對每一個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力行為,另一方即無過錯方在離婚訴訟中都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對此,法律及司法解釋并未明確。例如丈夫毆打其父母、兄弟姐妹,但并未毆打妻子而妻子卻以其理由提起離婚之訴時,能否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在丈夫毆打其父母、兄弟姐妹這一家庭暴力中,雖然丈夫存在過錯,但它并不一定給其妻子造成物質和精神上的損害。關于離婚損害賠償過錯責任的認定及賠償標準問題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婚姻家庭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離婚損害賠償過錯責任的認定及賠償標準問題:
1、關于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過錯責任之認定問題。
《〈婚姻法〉解釋(一)》第2條界定《婚姻法》規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就是說,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主要是指同居時,既不辦理婚姻登記手續、對外也不以夫妻名義出現的具有隱蔽性和較為穩定的兩性關系之行為。其特征是同吃、同住、同性生活,也稱為姘居。筆者認為,依照上述司法解釋及學者的觀點,離婚訴訟中過錯方有許多過錯行為是無法歸責的,例如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長期發生性關系,由于雙方沒有房子居住?如固定租房也算同居,并不固定地同住一起,這種情況下同吃的機會也不多,但平時是以開賓館、旅店房間或以其他場所為主要的會面點來發生兩性關系且長期維持其兩性關系的,這種情況如果不認定為非法同居的話,顯然是有違于客觀事實并不利于保護無過錯方利益的。因此,筆者認為,認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行為存在,應以較為穩定的兩性關系作為核心點來考慮,而不必以同住、同吃作為考慮的側重點。因為,穩定的兩性關系其感情基礎比較牢固且具有持久性,這種不正常的有感情基礎的婚外情人關系,勢必損害無過錯方合法權益,并給無過錯方帶來物質與精神的損害,故以非法同居來確定其過錯責任并判令其承擔損害賠償是完全必要且符合婚姻法之本意的。由于姘居或婚外情人關系多是秘密或半公開的,而要求賠償的過錯方,特別是女方自我保護意識不強,證據意識淡薄,平時不注意收集和保全證據,因此,無過錯方在舉證時往往就比較困難。法院在審理查明非法同居事實時關鍵在于把握其兩性關系的時間及其感情的程度,只要無過錯方在離婚訴訟中舉出相關證據鎖鏈證明有合理的場景和相關的人證、物證,證明過錯方即有配偶者與他人發生兩性關系已存在一定時間如三個月以上且兩性的感情業已達到親密程度,就可以認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行為存在。這樣,其過錯責任就自然而然的明確。
2、關于實施家庭暴力的過錯責任如何認定的問題。
《〈婚姻法〉解釋(一)》第1條界定“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傷害后果的行為。”我們知道,家庭成員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孫、婆媳。因此,配偶一方實施家庭暴力侵害的對象相應地也就包括上述其成員。但是否配偶對每一個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力行為,另一方即無過錯方在離婚訴訟中都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對此,法律及司法解釋并未明確。筆者認為,對于這個問題是不能簡單地回答是或不是的。例如丈夫毆打其父母、兄弟姐妹,但并未毆打妻子而妻子卻以其理由提起離婚之訴時,能否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在丈夫毆打其父母、兄弟姐妹這一家庭暴力中,雖然丈夫存在過錯,但它并不一定給其妻子造成物質和精神上的損害。因此,如果準許其無過錯方即妻子向過錯方即丈夫提起損害賠償之請,則與客觀事實是不相符的。反過來,如果實施家庭暴力的主體是妻子,如妻子毆打丈夫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其離婚訴訟中丈夫同樣也是不能由此提起損害賠償之請的,他們如要提起損害賠償之請,可單獨以其妻子作為被告來提起,其理由同上述理由是一樣的。但如果配偶一方是對子女實施暴力的,則在其離婚訴訟中無過錯方就可以提起損害賠償之請。因為配偶一方對子女?一般是未成年子女的傷害,子女的賠償之請只能是從父母的財產中直接支付,無過錯方提起損害賠償之請實際上就是代表子女來行使其權利;同時,這種過錯方對子女的傷害對于無過錯方的精神打擊來講,也是直接與重大的。因此,在這種情形下,準許無過錯方向有過錯方提起損害賠償是完全必要的。當然,這種配偶一方傷害其子女的情形在婚姻家庭及司法實踐中都是極其罕見的。由此可見,婚姻法所規定的實施家庭暴力的主體應當只能是配偶,其侵害的對象應是配偶一方或其子女,而不應包括其他家庭成員。
當我們明確了實施家庭暴力的主體和侵害的對象后,接下來需要解決的問題自然就是如何認定施暴者的暴力行為與受害者的傷害結果之關系問題了。暴力行為的表現形式依照上述司法解釋有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及其他手段。前者即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等實際上是屬于身體暴力的范疇;后者即其他手段可包括語言暴力和性暴力。因為,后這兩種暴力形式在婚姻家庭中都是客觀存在的,它們是家庭暴力中除身體暴力外的另兩種表現形式。那么,語言暴力、性暴力在審判實踐中如何來認定﹖筆者認為,語言暴力,一般是以威脅、恐嚇、謾罵、挖苦、侮辱等方式來威嚇、虐待對方,造成受害一方長期在精神、心理方面產生壓力與痛苦;性暴力是指丈夫為滿足自己的性欲,在妻子病重、經期、產期哺乳期等特殊情況下,違背妻子意愿,經常強迫其從事性行為或用殘暴的方式傷害妻子的生殖器官,使其身心受到極大損害的行為。家庭暴力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非是一切家庭暴力行為都能提起損害賠償的,只有那些施暴行為足以導致夫妻感情破裂并造成一定的傷害后果時,過錯方才應承擔起賠償責任。但“一定的傷害后果”其標準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對此未做出明文規定。筆者認為,由于婚姻損害賠償包括物質與精神賠償兩個方面,因此,其傷害后果的標準也應當以這兩方面的損害事實作為參考指數即包括肉體損害和精神損害的事實。而肉體損害事實筆者認為可依照刑事法律標準分為重傷、輕傷、輕微傷來認定。因為刑事法律這種區分肉體傷害程度不僅是比較科學的,而且依照其標準來作為確認離婚損害賠償中家庭暴力之傷害結果并無不妥;同時,在審判實踐中民事損害的賠償依據也往往是借鑒或參照刑事傷害這一標準的。因此,只有依照刑事傷害的法律標準,才能在審判實踐中對“一定的傷害后果”作出科學且公正的界定。精神損害事實筆者認為,可依照醫學上的標準分為精神衰弱、精神失常、精神錯亂等。但要明確肉體上的損害結果如輕傷并不一定就給受害者造成精神衰弱、精神失常等后果即肉體上的損害與精神的損害并不都是一致且并不都是具有因果關系。只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受害者的精神損害是同過錯方實施家庭暴力的行為具有因果關系的,人民法院才可以認定。由于家庭暴力有法定性及權威性的損害結果作為參照依據,這樣,在司法實踐上,認定實施家庭暴力者的過錯責任就比較容易掌握,其所造成的傷害結果及程度就易于明了,從而不會陷入盲目及主觀臆斷的誤區。
3、關于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過錯責任如何認定的問題。

《〈婚姻法〉解釋(一)》第1條在界定家庭暴力行為的同時,認為“持續性、經常性的家庭暴力構成虐待”。這說明,虐待是家庭暴力的經常性表現形式,也是家庭暴力的最高表現形態。但“持續性、經常性”的標準又是如何確認的﹖筆者認為,其時間標準應以一年以上為宜,即只要行為人實施的家庭暴力行為連續達一年以上的就可以認定為虐待。因為整年都對無過錯方實施家庭暴力,說明行為人主觀惡性大及情節較為嚴重,對這種不分四季的惡劣行為,宜于重罰。但必須明確,如果以虐待的過錯責任論處后,就不能也不應該再以實施家庭暴力的過錯責任來論處了,因為一種過錯行為不能受兩次處罰。
認定待如此,那么,對遺棄家庭成員的過錯責任又如何認定﹖這就需要明確遺棄這一概念,所謂遺棄,就是指對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撫養義務者拒絕撫養、贍養、照顧,情節較為嚴重的行為。首先,從其概念來看,遺棄的主體只能是有撫養能力的配偶,其他家庭成員即使有遺棄行為,但都不是離婚損害賠償制度中所規定的遺棄主體;其次,被遺棄的對象既包括年老、患病的父母、未成年的子女,也包括患病或沒有生活經濟來源的配偶。再次,這種遺棄行為已造成了較為嚴重的后果,如造成年老、年幼或患病者饑餓、挨凍、流浪、病重及死亡等。此外,遺棄在時間上顯然是要達到一定的期限,否則不會出現嚴重的后果。從此我們可能看出,遺棄相對于實施家庭暴力來講,它所侵害的對象與范圍比實施家庭暴力行為所侵害的對象與范圍要廣泛,理由是實施遺棄者往往是離家外出或不共同生活在一起,無過錯方的賠償請求是基于撫養子女、贍養年老或生病的父母的需要而提出的,負有撫養義務一方不能逃避此責任;同時,撫養、贍養既是一種法定義務,也是傳統的孝德,有撫養能力的配偶喪失了這種孝德,則不僅要受道德的譴責,而且要受法律的制裁。因此,認定遺棄家庭成員的過錯責任,應從遺棄行為所造成的后果、被遺棄成員的人數及遺棄行為的起始時間來綜合考慮和分析。
二、關于離婚損害賠償的賠償標準如何確定的問題
離婚訴訟中對過錯責任的認定就為我們確定其損害賠償額提供了法律和事實的依據,但如何準確、公平地確定每一種過錯責任所應承擔的賠償額,并能體現出過錯行為與損害賠償額相一致的原則,則是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的問題。在法律及司法解釋未對損害賠償數額做具體規定的條件下,我們只能從相關的法律及司法解釋中尋找其依據與理由;同時,在民事損害賠償的法律關系中如何把握錯責自負原則,也需要我們對之進行認真研究,因為這不僅是司法實踐面臨的問題,而且也是法律的公平與正義的問題。筆者認為,確定離婚損害賠償額,不論是哪一種類型的損害賠償,都應當堅持如下四個考慮原則:1、適當考慮經濟補償的原則,就經濟補償是必須的,但它并非是無限量的。2、適當考慮以精神撫慰為主、物質補償為輔的原則,就這種損害賠償主要是基于撫慰無過錯方的精神受傷害、受打擊而設立的,因此,物質賠償只是起一種輔助的作用。3、適當考慮精神賠償數額有所限制的原則,即使是以精神撫慰為主,但其精神賠償也不是沒有限量的,應當有所限制。4、適當賦予法官對精神賠償額裁決的自由裁量權的原則,就每一件離婚損害賠償的案例來講,都會因人因地區及因傷害程度的不同而迥異,因此,賦予法官在此方面的自由裁量權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每一種婚姻其過錯行為引起的離婚損害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其承擔的損害賠償額自然也就不盡相同。下面就四種婚姻過錯責任所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分析如下:
1、關于因重婚的過錯責任所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的確定問題。
重婚是指已結婚男女又與他人結婚或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的行為,它是以一種公開化的夫妻形式對原有的合法性的婚姻關系的疊加。重婚既是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挑戰與否定,也是對自身已有婚姻的挑戰與否定。因此,無過錯方因重婚者重婚行為提起離婚損害賠償時,法院依法對其進行救助與支持是必然的,這也是維護弱者合法權益之要求,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復雜的一面,重婚行為一樣也存在著復雜的情形。重婚者之所以采取公開化的重婚方式,其原因無外有下列兩種:1、原配偶(無過錯方)不愿意與其離婚,第三者強烈要求組成家庭,有過錯方愿意或堅持與第三者組成家庭。2、原配偶因年紀大沒有子女或沒有兒子,為了傳宗接代,允許甚至幫助過錯方實施重婚行為。對于上述這兩種重婚行為,人民法院在審理無過錯方提起損害賠償之請時,應當區別對待。對第一種因重婚行為提起離婚請求損害賠償的,因導致離婚的責任完全在于過錯方,因此不論是在物質損害賠償還是精神損害賠償方面都應當給予無過錯方充分的救濟與支持。但究竟確定多少損害賠償額才合理,才符合錯責一致的原則﹖筆者認為,確定其損害賠償額,首先,應以夫妻共有財產總額作為參考系數,并根據上述確定損害賠償額的原則來確定賠償額的份額或比例才能恰當與公平。其次,如果夫妻共有財產如金錢等不足于賠償無過錯方損失或者其共有財產分割時,過錯方所分得的財產如房屋等無法通過折價或抵償的方式賠償對方損失的,則人民法院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解釋》來確定其賠償數額。再次,物質損害賠償額在分割夫妻共有財產時應優先考慮和照顧,并根據無過錯方所受的損害程度、過錯方的主觀過錯責任之大小及其經濟負擔能力等因素來確定其在夫妻共有財產中的份額或比例。其理由是,離婚時,有過錯方即重婚者無論怎樣的過錯他?她都應取得一定的共有財產;同時,今后生存的需要也應給予過錯方一定的共有財產。另外,以夫妻共有財產總額作為損害賠償系數并優先確定物質損害賠償額,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解釋》第10條即根據侵權人?過錯方承擔經濟能力和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精神,又符合各個家庭的實際情況并便于法院的執行及無過錯方權利之實現,使過錯方和無過錯方都切實感受到法律的功能與作用,從而對各個婚姻家庭產生制約及規范性影響。當然,如果過錯方給無過錯方造成的損害是巨大,其所分得的共有財產無法再賠償其損失,則另行確定其賠償額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因第二種重婚行為提起離婚損害賠償的,因無過錯方在重婚者實施重婚行為開始時是給予支持的,感情傷害不明顯、不劇烈,因此,在精神損害賠償額方面可酌情減少,但可在物質損害賠償額方面給予一定的照顧。
2、關于因配偶與他人非法同居的過錯責任所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的確定問題。
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雖然不象重婚者那樣采取直接公開的形式,但它對無過錯方的傷害往往也是巨大的。因此,在確定其損害賠償額時也應以其夫妻共有財產總額作為參考系數,明確無過錯方在其財產總額中應占有的份額。其損害賠償額的確定方法同重婚責任所承擔的賠償額之確定方法一樣。但如果物質損害賠償額確定之后,過錯方從夫妻共有財產分割中所得到的財產不足賠償無過錯方的精神損害,則應考慮過錯方與他人同居時的主觀過錯程度及經濟負擔能力等因素,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解釋》來另行確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但對于因與他人同居所承擔的過錯責任的賠償數額,筆者認為,無論是物質損害賠償份額還是精神損害賠償份額都不應低于重婚行為所造成的損害賠償額。因為重婚行為和非法同居行為都是屬于同一性質即因一方同其他人產生兩性關系導致雙方的感情破裂與傷害。因此,法院在確定其賠償額時不應有輕重之分,除非有其他法定例外的情形與事實。
3、關于因實施家庭暴力行為的過錯責任所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確定的問題。
如前所述,實施家庭暴力行為給無過錯方的傷害,在肉體上的損害有重傷、輕傷、輕微傷之分;在精神上的損害有精神衰弱、精神失常、精神錯亂之分等。相應地,人民法院在確定其損害賠償額時就應根據其傷害結果與程度,以夫妻共有財產總額作為參考系數來確定無過錯方所應取得的賠償份額,如夫妻共有財產總額不足于賠償的,在精神損害賠償方面,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解釋》確定方法另行確定。但應當注意,肉體上的損害結果并非都能導致精神上的損害結果之發生。如無過錯方把過錯方打成輕傷或重傷,其肉體上的所遭到的致害并非就能導致無過錯方出現精神衰弱、精神失常、精神錯亂等情形,因此,法院在確定其精神損害賠償額時可根據肉體上的損害程度與結果,參照精神損害的賠償因素確定方法來確定其應得的數額。但如果兩者的損害是同時發生,如無過錯方被打傷重并導致精神失常的,則就應根據上述賠償額比例的方法來確定其整個損害賠償額。
4、關于因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過錯責任所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確定的問題。
上面談到,依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釋,虐待是家庭暴力的持續性、經常性的表現形式。因此,因虐待家庭成員的過錯責任所應承擔的損害賠償總額就不應低于一般性的家庭暴力所造成的損害賠償總額,這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否則就不能體現出兩者的本質之區別。但對于特殊性的家庭暴力如一次就毆打無過錯方致重傷,造成無過錯方精神失常等,這種例外的情形,其一般性虐待的損害賠償總額就并不一定比這種特殊性的家庭暴力所應承擔的損害賠償額高。理由很簡單,因為一次的傷害就已遠遠超出其長期性傷害程度。因此,確定虐待損害賠償額時不能機械確定和適用。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