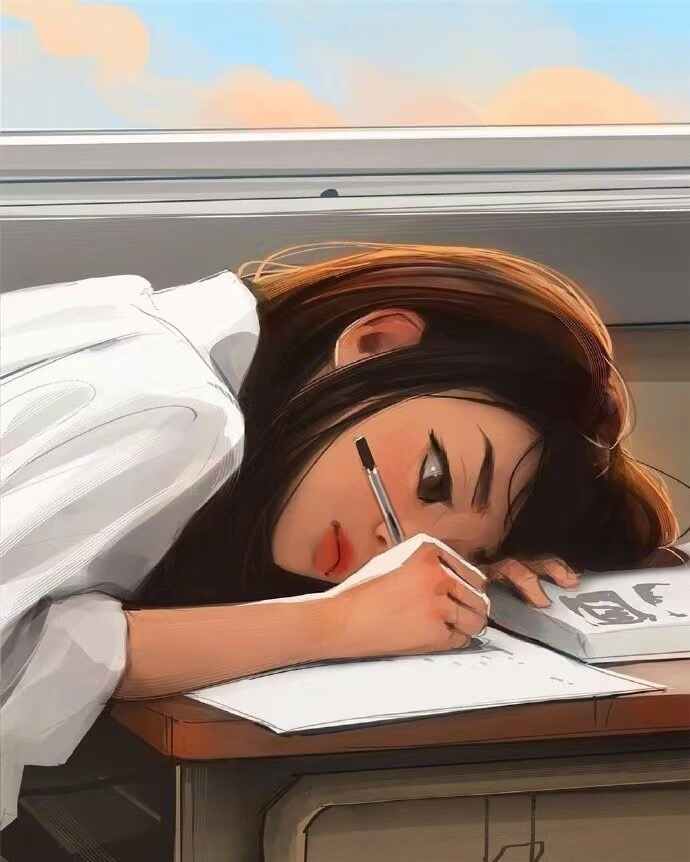掛名法人危險有多大
 郭銘芝律師2023.06.08453人閱讀
郭銘芝律師2023.06.08453人閱讀
導讀:
《企業破產法》第128條規定,破產企業在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一年內,存在對未到期的債務提前清償、以明顯不合理的價格交易資產、放棄債權、無償轉讓財產等行為的,該行為應予以撤銷,如對債權人利益造成損害的,破產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掛名法定代表人&rdquo,在確需掛名的情況下,掛名法定代表人有必要與實際控制人簽訂書面協議,約定掛名期限、各方權利義務以及解除掛名的事由等,員工擔任掛名法定代表人的,應在離職時與公司協商并書面約定辦理變更登記的時間。
實踐中公司實際控制人為了逃避司法制裁,不愿意以自己的名義擔任公司的股東和法定代表人,存在很多“員工”法定代表人、股東,而“掛名法定代表人”因為各種原因承擔與之不相符的法律風險。
如果“掛名”,風險有哪些?
實際上,“掛名”法定代表人的風險遠不止上述的民事風險,甚至還有行政、刑事方面的風險。例如,公司運營過程中出現火災,法定代表人可能成為直接的責任人;公司涉嫌詐騙、非法集資等情況時,法定代表人也可能成為犯罪嫌疑人。
掛名法定代表人應謹慎對待此身份的法律風險,應提前了解掛名的風險。
在確需掛名的情況下,掛名法定代表人有必要與實際控制人簽訂書面協議,約定掛名期限、各方權利義務以及解除掛名的事由等,員工擔任掛名法定代表人的,應在離職時與公司協商并書面約定辦理變更登記的時間。這樣雖然不可能完全免責,但至少可以一定程度降低掛名法定代表人的風險。
當擔任一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時,應關注公司來往賬目,印鑒使用規范,遇到公司資不抵債的情況,及時與公司協商辦理法定代表人工商變更登記,保護自身利益。
掛名法定代表人的主要法律責任
1.民事責任
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法定代表人需要對自身行為及所屬企業行為對外承擔民事責任。
《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第21條規定“法定代表人的越權擔保行為給公司造成損失,公司請求法定代表人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沒有提起訴訟,股東依據《公司法》第151條的規定請求法定代表人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企業破產法》第128條規定,破產企業在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前一年內,存在對未到期的債務提前清償、以明顯不合理的價格交易資產、放棄債權、無償轉讓財產等行為的,該行為應予以撤銷,如對債權人利益造成損害的,破產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另外,如果被債權人告上法庭,并被申請強制執行時,根據《民事訴訟法》以及《最高院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掛名法定代表人會被限制高消費和限制出行。
社保入稅后,根據2018年11月22日國家發改委等28個部門印發《關于對社會保險領域嚴重失信企業及其有關人員實施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通知》,一旦公司在員工的社保繳費上出問題,掛名法定代表人會面臨列入黑名單的嚴重后果。
2.行政責任
根據《民法通則》《公司法》等相關法律之規定,企業法人存在以下情形的,對法定代表人可以給予行政處分、罰款。
1、企業法人超出登記機關核準登記的經營范圍從事非法經營的;2、向登記機關、稅務機關隱瞞真實情況、弄虛作假的;3、抽逃資金、隱匿財產逃避債務的;
4、解散、被撤銷、被宣告破產后,擅自處理財產的;5、變更、終止時不及時申請辦理登記和公告,使利害關系人遭受重大損失的;6、從事法律禁止的其他活動,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
而且,法定代表人需要承擔的行政責任往往還與所屬行業有較大關系。比如在醫藥行業,藥品生產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應對本企業的藥品生產活動全面負責,《藥品管理法》第118條規定“生產、銷售假藥,或者生產、銷售劣藥且情節嚴重的,對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沒收違法行為發生期間自本單位所獲收入,并處所獲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終身禁止從事藥品生產經營活動,并可以由公安機關處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再比如針對項目建設過程中的環評問題,《環境影響評價法》第32條明確規定“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環境影響報告表存在基礎資料明顯不實,內容存在重大缺陷、遺漏或者虛假,環境影響評價結論不正確或者不合理等嚴重質量問題的,由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對建設單位處五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的罰款,并對建設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3.刑事責任
在我國《刑法》規定的某些罪名中,除了對單位進行處罰外,還可能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的刑事責任。例如,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逃稅罪、非法經營罪等,而對于上述“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具體范圍,雖然我國法律法規等未明確規定,但是司法實踐通常將法定代表人認定屬于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公司法定代表人作為公司的主要負責人,一旦參與公司具體行為的決策或在相關決策文件上簽字,在單位犯罪情形下,法定代表人被認定對單位的犯罪行為承擔相應刑事責任的風險極大。2015年的天津港爆炸案中,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掛名法定代表人李亮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近年來,隨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套路貸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增多,如何在《刑法》體系內界定“掛名法定代表人”與“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之間的關系逐漸引發人們的關注,如《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檢察院、河南省公安廳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豫檢會2015第11號)第6條第3項提出了如下處理意見“對于沒有與單位實際控制人進行非法集資預謀,沒有實際出資,沒有參與經營的掛名股東,掛名法定代表人,是否構成共同犯罪,要按照主客觀一致原則嚴格掌握。構成犯罪的,如能配合司法機關查清事實挽回損失,可以從寬處理。”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