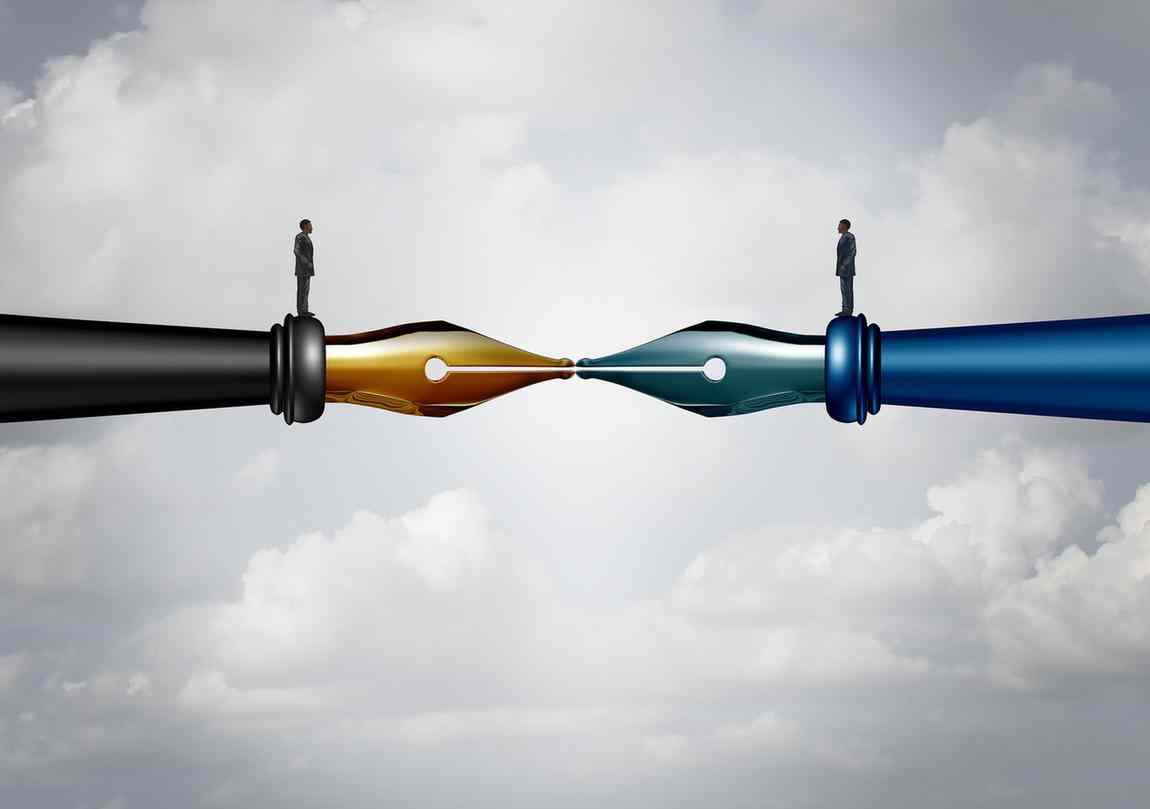后車撞死追尾事故中人員誰來承擔賠償責任
 張蕓律師2021.12.05613人閱讀
張蕓律師2021.12.05613人閱讀
導讀:
后車撞死追尾事故中人員誰來承擔賠償責任王永亮董永強[案情]原告鄭克鋒,系死者鄭大喜的父親。原告認為交警部門未正確劃分事故責任。第三被告辯稱,其不應承擔責任。法院并未采納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提出的“由張中亮、鄭大喜與李子明各自承擔三分之一責任”的主張,而是判決張中亮承擔50%的賠償責任。那么后車撞死追尾事故中人員誰來承擔賠償責任。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后車撞死追尾事故中人員誰來承擔賠償責任王永亮董永強[案情]原告鄭克鋒,系死者鄭大喜的父親。原告認為交警部門未正確劃分事故責任。第三被告辯稱,其不應承擔責任。法院并未采納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提出的“由張中亮、鄭大喜與李子明各自承擔三分之一責任”的主張,而是判決張中亮承擔50%的賠償責任。關于后車撞死追尾事故中人員誰來承擔賠償責任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交通事故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后車撞死追尾事故中人員誰來承擔賠償責任
王永亮董永強
[案情]
原告鄭克鋒,系死者鄭大喜的父親。
第一被告張中亮。
第二被告周口市遠大運輸集團潤發運輸有限公司。
第三被告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五○四廠。
第三人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
2005年9月30日,原告主子鄭大喜搭乘胡德于駕駛的車輛行駛至上海市A4高速公路時,被李子明駕駛的車輛(第三被告為該車登記車主)從后面撞擊。事發后,鄭大喜、胡德于與李子明下車查看損失情況時,鄭大喜與李子明被張中亮駕駛的車輛(第二被告為該車登記車主)撞擊致死。2005年10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交警支隊認定,張中亮所駕駛車輛的制動性能不符合安全要求,不能確保駕駛安全,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簡稱《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之規定;鄭大喜和李子明在高速公路發生交通事故時,均未轉移到右側應急車道內,違反了《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之規定。故張中亮、鄭大喜、李子明負事故的同等責任。
原告提起訴訟,請求判令三被告連帶賠償各項損失共計2500000元。訴訟中,依照張中亮的申請,法院追加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審判]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在第二起事故中,對于鄭大喜的死亡,如何確定三方當事人責任?
原告認為交警部門未正確劃分事故責任。《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機動車駕駛人已經采取必要處置措施的,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鄭大喜下車后,其身份即由乘車人轉變為行人,在過錯相當的情況下,鄭大喜所承擔的事故責任應當低于張中亮,因此交警部門認定三方負同等責任是不正確的。
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辯稱,交警部門認定三方負同等責任意味著張中亮、李子明與鄭大喜應當各承擔三分之一的責任。
第三被告辯稱,其不應承擔責任。
第三人未到庭參加訴訟,也未提出答辯意見。
法院認為:李子明在第二起事故中的過錯與鄭大喜的死亡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和必然的因果關系,故對原告要求第三被告承擔賠償責任的主張不予支持;第二起事故中,鄭大喜并非行人,故對原告要求按行人與機動車發生事故的原則劃分責任的主張不予支持;對于鄭大喜的死亡,張中亮和鄭大喜本人均有過錯,因此應當由他們各負50%的責任,第二被告作為張中亮所駕駛車輛的登記車主,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由于張中亮未提供第三人的工商主體資料,法院對第三人是否負有保險賠付責任未作認定與處理。
[評析]
本案中,要正確確定賠償責任必須澄清兩個問題:第一,交警部門作出的責任認定書載明,“張中亮負事故的同等責任、鄭大喜負事故的同等責任、李子明負事故的同等責任”,能否解讀為張中亮作為肇事方僅需承擔三分之一的賠償責任?第二,鄭大喜離開機動車后,其身份是否從乘車人轉變為行人?
1、事故同等責任是否意味著同等賠償責任?
法院并未采納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提出的“由張中亮、鄭大喜與李子明各自承擔三分之一責任”的主張,而是判決張中亮承擔50%的賠償責任。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責任認定書是對交通事故中所涉及的各種過錯與責任的總體評判,并不針對具體的損害結果,而民事賠償責任則必須針對事故中每個具體的損害結果予以確定。本案中,第二起交通事故造成了鄭大喜和車子明死亡兩個損害結果,責任認定書是針對兩個損害結果統一作出的。“張中亮負事故的同等責任、鄭大喜負事故的同等責任、李子明負事故的同等責任”,只能說明張中亮、鄭大喜與李子明在第二起事故當中均負有責任,而不能說明他們針對每個單一的損害結果負有責任。在訴訟當中,法院必須根據每個受害人的受損情況分別進行認定,而標準依然應當是侵權行為、損害結果、過錯與因果聯系等四個侵權行為構成要件。本案中,鄭大喜家屬提起訴訟,則人民法院就必須圍繞鄭大喜死亡這一損害結果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在第一起追尾事故發生后,鄭大喜、胡德于和李子明為了查清損失情況,一起下車查看。對于鄭大喜的死亡,李子明主觀上不具有過錯,客觀上未實施侵權行為,因此李子明不應承擔民事侵權責任。鄭大喜的死亡是由于其自身的過錯和張中亮的侵權行為共同造成的,鄭大喜與張中亮因此應當各負50%的責任,而李子明不承擔責任。基于同樣的分析,對于李子明的死亡,李子明和張中亮應當各負50%的責任,而鄭大喜則不承擔責任。綜上,對于交警部門責任認定書的正確解讀是:對于鄭大喜的死亡,鄭大喜與張中亮應當各負50%的責任;對于李子明的死亡,李子明和張中亮應當各負50%的責任;鄭大喜與李子明互不承擔賠償責任。
另一方面,各自承擔三分之一的賠償責任將會不當地減輕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應當承擔的責任。如果采納了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的答辯意見,將出現侵權責任因受害人數量遞增而不斷遞減的不合理現象。假設本案當中受害人不是兩人而是五人,則按照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的邏輯,其對于包括鄭大喜在內的每個死者只需承擔六分之一的責任。受害人人數越多,損害后果越嚴重,侵權行為人針對每個受害人的責任比例反而越低,這顯然是極不正常的。侵權行為人的過錯只應在其與受害人之間作出評價,而不應當將與損害結果不具有因果關系的第三方(本案中為李子明)納入其中。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的答辯意見是對交警部門責任認定書的一種誤讀,不當地將本應針對每個受害人分別作出的責任認定進行了“打包”處理。
2、鄭大喜是否屬于行人?
《交通安全法》分別就車輛駕駛人、乘車人與行人的通行作出了規定,卻并未就車輛駕駛人、乘車人與行人作出明確的定義。在大多數情況下,車輛駕駛人、乘車人與行人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車輛駕駛人指操縱車輛行駛的人;乘車人指搭乘車輛的人;行人指“在路上走的人”。但在本案的特定法律語境中,行人與乘車人的界限就變得模糊了。鄭大喜在離開所乘坐的車輛之前,無疑屬于乘車人,而在為了查看損失而離開機動車近距離行走的情況下,鄭大喜是否已經轉變為行人?[page]
筆者認為,鄭大喜并未因近距離行走而轉變為行人。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是否在道路上行走不應被作為判斷行為人是否是行人的決定性標準。機動車駕駛人和乘車人在特定情況下也必須近距離行走,但在行走期間卻并不適用有關行人的規定。《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機動車在道路上發生故障,需要停車排除故障時,駕駛人應當立即開啟危險報警閃光燈,將機動車移至不妨礙交通的地方停放;難以移動的,應當持續開啟危險報警閃光燈,并在來車方向設置警告標志等措施擴大示警距離,必要時迅速報警”。第六十八條第一款規定,“機動車在高速公路上發生故障時,應當依照本法第五十二條的有關規定辦理;但是,警告標志應當設置在故障車來車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車上人員應當迅速轉移到右側路肩上或者應急車道內,并且迅速報警”。上述兩個條文分別規定在第四章第二節“機動車通行規定”和第四章第五節“高速公路的特別規定”中,與第四章第四節“行人和乘車人通行規定”為并列關系。由此可以看出,第五十二條與第六十八條第一款并不適用行人通行的規定。但是,車輛駕駛人和乘車人要實施第五十二條和第六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的某些行為,卻又必須離開車輛近距離行走,如“在來車方向設置警告標志”與“迅速轉移到右側路肩上或者應急車道內”。因此,并非所有事故發生時在道路上行走的人均屬于《交通安全法》意義上的行人。
其次,將鄭大喜作為行人對待有悖于立法意圖。《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條與第六十八條第一款均包含了機動車駕駛人和乘車人下車行走的行為,卻分別被規定在“機動車通行規定”與“高速公路的特別規定”中。這充分表明了《交通安全法》的立法意圖:事故發生后,機動車駕駛人或者乘車人下車、行走直至轉移到安全地帶應當被作為一個完整的過程來看待,行走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并不改變機動車駕駛人或者乘車人的既定身份。雖然鄭大喜違反了《交通安全法》的規定,在事故發生后未及時轉移,但對其身份仍然應當結合事發經過作出評判。將鄭大喜作為行人對待,實質上是對《交通安全法》的一種斷章取義的理解。
最后,鄭大喜并不符合行人的特征。盡管《交通安全法》未對行人作出明確定義,但從《交通安全法》有關行人的規定中,卻可以歸納出行人最基本的特征,即主觀上無意正常搭乘或駕駛機動車行進,客觀上對于機動車的行駛或使用不具有支配力。本案中,鄭大喜雖然暫時離開了所乘坐的機動車,但主觀意圖是在交涉完畢后返回機動車繼續行進,他不是為了行走而行走,而是為了解決機動車出現的問題而行走;在客觀方面,鄭大喜與胡德于下車察看的行為與乘坐和駕駛行為一樣,都體現了對機動車的支配。因此,無論從主觀方面還是客觀方面來看,鄭大喜與《交通安全法》中所規定的行人均有所不同。
綜上,法院判決認為,鄭大喜并非行人,本案中的第二起事故不應按照行人與機動車發生事故的原則劃分責任。
作者單位: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
[專家點評]
交通肇事案中的間接責任人應否為事故擔責?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陳現杰
本案中,法院根據交警部門對事故責任的認定,確認肇事機動車一方應分別對兩位受害人的死亡結果各承擔50%的責任,死者本人亦應對自身被撞致死承擔50%的責任,其對交警所作三方當事人負事故的同等責任的解讀是正確的。
加害人所駕駛車輛的制動性能不符合要求,且駕駛員駕駛車輛未確保安全,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之規定;而受害人一方在高速公路上發生交通事故時,未轉移到右側應急車道內,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個八條第一款之規定,故對受害人死亡結果,機動車一方和受害人自身負同等責任。作為事故責任主體的加害人一方認為同等責任意味著兩位死者與其各應承擔三分之一的責任的觀點,是一種誤解。但應當注意的是,就第一起事故而言,李子明所駕車輛追尾撞擊鄭大喜所搭乘的車輛造成交通事故,案例未說明兩者之間的責任劃分,依交通常識應是追尾車輛負全責。兩人下車查看事故情況時,被第二次事故的肇事車輛撞擊致死,則第一次事故的發生,客觀上不能不說是導致第二起事故的一個條件或者因素,故受害人死亡后果雖與第一次事故的發生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但仍存在間接的因果關系。僅據李子明在第二起事故中的過錯與鄭大喜的死亡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和必然的因果關系而否認第三被告的可歸責性,是值得商榷的。法律上的因果關系,與自然科學領域的因果關系有所不同,不能以是否存在固有的內在的必然聯系作為判斷標準,而須加入價值判斷,從而以所謂相當因果關系理論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標準。所謂相當因果關系,通常認為包含兩個層次:其一是事實上的因果關系,其判斷標準是“無此原因必無此結果”;其二是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即原因和結果具有“相當性”,其判斷標準是“有此行為通常即有此結果”,這其中就包含有價值判斷的因素。車輛相撞,雙方下車查看,乃事物當然之理——這就是一種價值判斷;匆遽之間,未能及時轉移到安全區域,致釀成第二起車禍——亦是下車查看之隨機結果,在高速公路上,更具有高度之蓋然性,從而建立起第一起車禍的發生與第二起車禍之損害結果間具有相當性之評價。但由于發生死亡結果的直接原因力來自第二起車禍,故第一起車鍋的發生乃是一個間接原因,是介入因素。故第一起車禍的肇事責任人在其對第二起車禍的原因力比例和過錯大小的范圍內仍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由于第一起車禍只是發生死亡結果的間接原因,其原因力比例較低;又由于受害人自身的過失也是發生死亡后果的主觀因素之一,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后,即使李子明在第一起車禍中應負全責,其所承擔的責任比例亦不宜過高,而應予適量斟酌。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