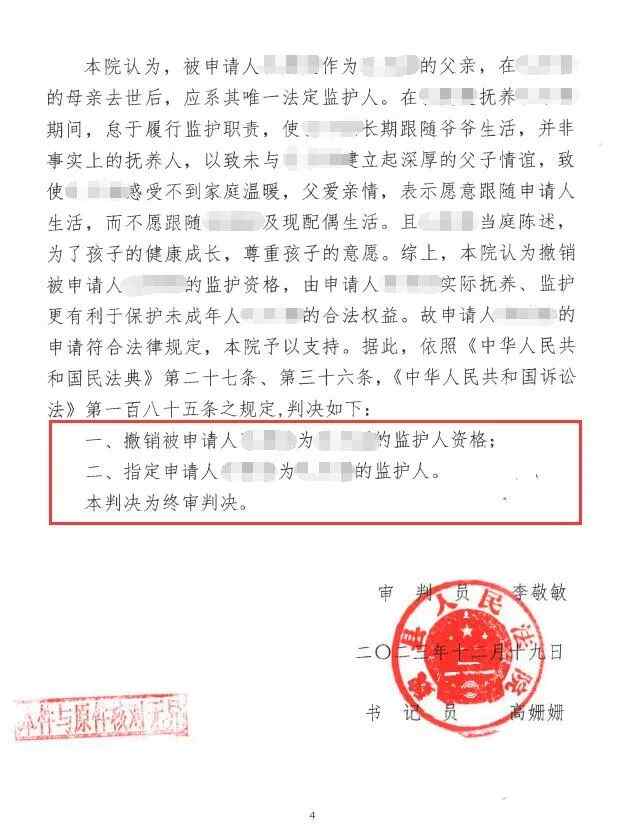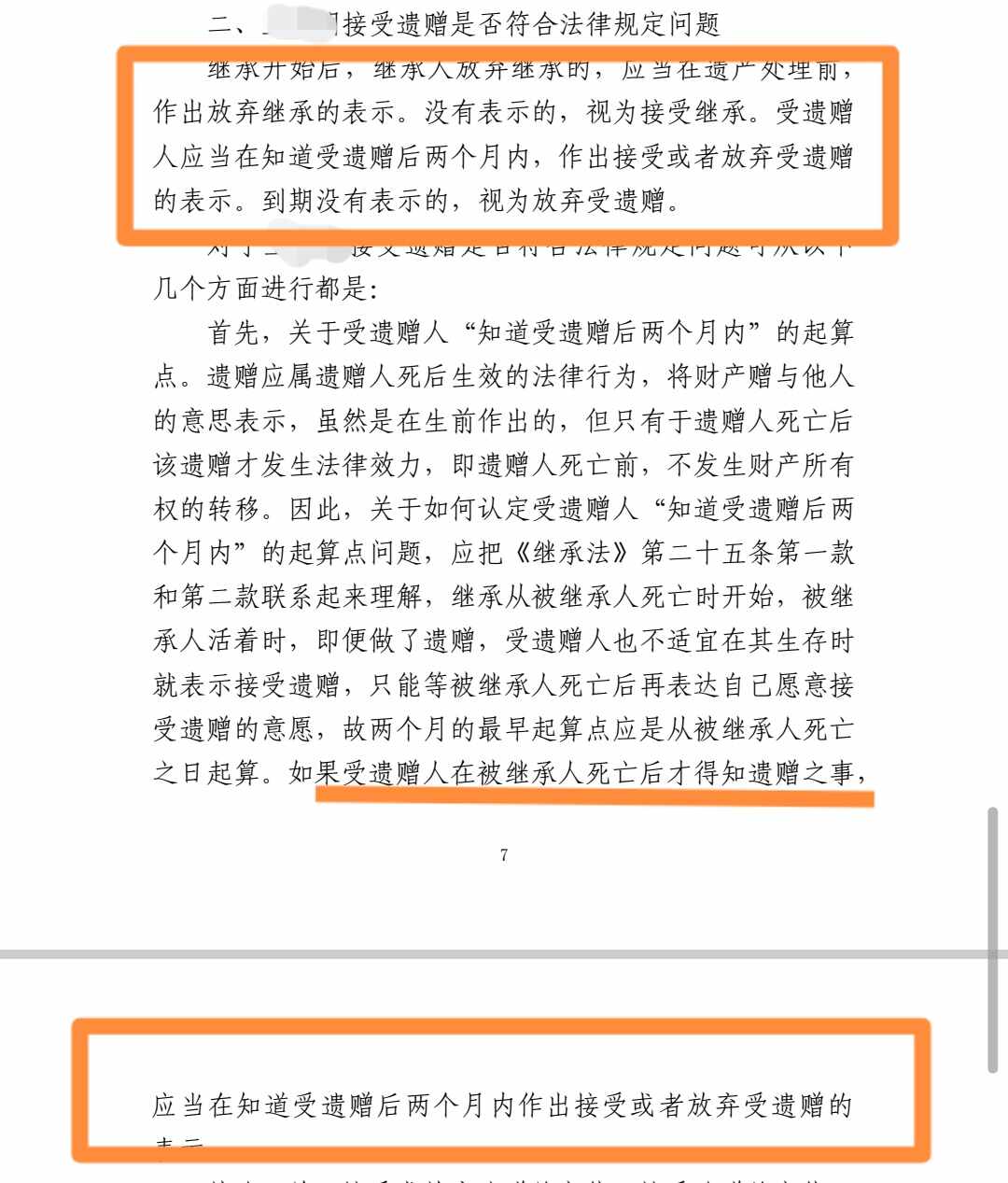民事債權人和刑事被害人對財產權利的放棄有什么影響
 李維律師2022.02.07720人閱讀
李維律師2022.02.07720人閱讀
導讀:
案發前,其中兩名被害人池某和何某分別通過書面和口頭形式,表示對余某未償還的共4140.89萬元本金予以放棄。第二種意見認為,民事債權人與刑事被害人對財產權利的放棄對于民事和刑事法律關系中的對方當事人責任承擔存在不同影響。同時,案發前被害人放棄財產權利的社會危害性遠大于被告人案發前歸還贓物。因此,余某仍需承擔相應的懲罰性和財產性刑事責任,池某和何某放棄財產權利的行為對余某刑事責任的承擔不產生影響。本案中,池某和何某雖放棄其對余某的財產權利,但余某在案發前客觀上并未歸還該筆款項,因此該4140.89萬元仍屬余某的犯罪所得,不能剔除,其集資詐騙數額應為12994.78萬元。那么民事債權人和刑事被害人對財產權利的放棄有什么影響。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如下相關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案發前,其中兩名被害人池某和何某分別通過書面和口頭形式,表示對余某未償還的共4140.89萬元本金予以放棄。第二種意見認為,民事債權人與刑事被害人對財產權利的放棄對于民事和刑事法律關系中的對方當事人責任承擔存在不同影響。同時,案發前被害人放棄財產權利的社會危害性遠大于被告人案發前歸還贓物。因此,余某仍需承擔相應的懲罰性和財產性刑事責任,池某和何某放棄財產權利的行為對余某刑事責任的承擔不產生影響。本案中,池某和何某雖放棄其對余某的財產權利,但余某在案發前客觀上并未歸還該筆款項,因此該4140.89萬元仍屬余某的犯罪所得,不能剔除,其集資詐騙數額應為12994.78萬元。關于民事債權人和刑事被害人對財產權利的放棄有什么影響的法律問題,大律網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債權債務律師相關的法律知識,希望能幫助大家。
2003年4月至2013年9月期間,被告人余某以經營醫療器械需要資金為名,以30%至60%的高額年利率為誘餌向16人非法集資16152.8萬元,案發時除歸還部分本金和支付部分利息外,仍有12994.78萬元未歸還。余某將大部分集資款用于賭博、購買房產、高檔汽車、奢侈品及個人揮霍。案發前,其中兩名被害人池某和何某分別通過書面和口頭形式,表示對余某未償還的共4140.89萬元本金予以放棄。
兩名被害人放棄財產權利對余某集資詐騙數額是否產生影響?
第一種意見認為,池某和何某放棄權利,應視為余某已經歸還該筆款項,還表明余某無需承擔包括刑事責任在內的所有對應的法律責任,故4140.89萬元不應視為余某的集資詐騙數額。
第二種意見認為,民事債權人與刑事被害人對財產權利的放棄對于民事和刑事法律關系中的對方當事人責任承擔存在不同影響。同時,案發前被害人放棄財產權利的社會危害性遠大于被告人案發前歸還贓物。因此,池某和何某所放棄的4140.89萬元不能從犯罪數額中剔除,仍應認定為余某的犯罪數額。
【評析】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
1.民事債權人和刑事被害人對財產權利的放棄對對方當事人民事與刑事責任產生不同影響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十八條的規定,債權人可以在不侵害國家、集體和他人合法權利的基礎上放棄自己的實體權利。同時又因民事權利和民事責任屬于私法領域的法律關系,民事立法的價值追求是保護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對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賦予法律效力,體現的是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因此,當債權人放棄其權利時,債務人就當然免除對應的民事責任。而刑事權利和刑事責任屬于公法領域的法律關系,法律強調的是強制性而非意思自治,主要體現的是國家與被告人之間的單向服從的不平等法律關系。因此,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對其權利的放棄雖然可以影響其自身權利的實現,但并不能影響國家對被告人所要追究的強制性刑事責任,包括判處自由刑和財產刑等懲罰性刑事責任和追繳或責令退賠贓物等財產性刑事責任。本案中,池某和何某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而非民事債權人,其放棄的是刑事權利而非民事權利。因此,余某仍需承擔相應的懲罰性和財產性刑事責任,池某和何某放棄財產權利的行為對余某刑事責任的承擔不產生影響。
2.案發前被害人放棄財產權利與被告人已歸還贓物體現不同社會危害性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第三款的規定,集資詐騙數額應是指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即指案發前實際未歸還的數額。而所謂實際未歸還的部分,是指客觀上沒有歸還,不應包括被害人放棄的部分。這是因為,詐騙罪所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所有權,正是因為被告人實際未歸還財產導致侵害了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從而造成了較大的社會危害性,此時刑法才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而案發前被害人雖然放棄對被告人的財產權利,但客觀上被告人仍然沒有歸還被害人財產,被告人依然侵犯了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被告人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并不因此而發生變化。本案中,池某和何某雖放棄其對余某的財產權利,但余某在案發前客觀上并未歸還該筆款項,因此該4140.89萬元仍屬余某的犯罪所得,不能剔除,其集資詐騙數額應為12994.78萬元。
3.被害人放棄的財產應當上繳國庫
如前所述,被害人對財產權利的放棄對被告人刑事責任不產生實質性影響。因此,法院在刑事判決主文部分,除要列明懲罰性刑事責任外,同時仍應列明被告人的財產性刑事責任,法院對該財產性刑事責任仍要予以執行。與此同時,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對于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于被害人的財物,應當及時返還。上述規定雖未明確被害人放棄的財產性權利在執行到位后歸誰所有,但筆者認為,被害人放棄的財產與民法上的無主物類似,應當對該財產收歸國有,上繳國庫。
 點贊
點贊
 收藏
收藏